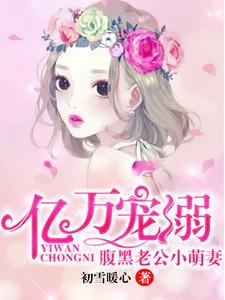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50章 不瘋魔不成活
來探班的“夏令營”回到家裏後,将他們探班成果制作成一組照片,發到了連夏的貼吧上。
“啞母”劇組不知道,這組照片從貼吧轉到了天涯貓撲等公共平臺,引起了不少網友的圍觀和贊嘆。
無論是連夏的粉絲,還僅僅是知道有連夏這麽一個演員的普通網友,都對連夏的新造型極為贊嘆,尤其是當連夏村姑打扮的照片和《靖康變》中李師師美輪美奂的劇照放在一起對比的時候,那效果簡直是嘆為觀止。
一些網友紛紛跟帖發表自己的意見——
“不知道誰能看出來她們是一個人!”
“氣質完全變了,不告訴我這是連夏完全認不出來,好牛逼的化妝師啊!”
“根本不是化妝好不好,據說連夏臉頰上的紅色是過敏,但是為了拍戲效果沒有去醫院。”
“真是好大的犧牲,真是好敬業啊,突然路人轉粉了啊。”
李青這種純文藝片導演,沉寂五年,記住他的人并不多,“啞母”開機儀式吸引來的媒體也不是特別多,沒有濺起特別大的水花,基本上除了連夏的粉絲,沒有人會關注這部電影,但是随着連夏在片中劇照的曝光,不少網友百度連夏在拍什麽片子時,執導這部戲的導演李青也開始走進大家視線。
兩次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二十七歲執導的影片捧得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獎,因“社交恐懼症”一直在國外治療,五年未有新作……
縱觀導演的履歷,網友不禁感慨,真的好牛啊。
有人關注,媒體自然就會報道,無人問津的“啞母”劇組,在開機半個多月後,迎來了第一批來探班的記者。
可惜記者并沒有得到多少采訪的機會,李青生活裏話都說不出來,但是在工作中卻是一個“獨-裁者”,他認為記者的到來引發村民的圍觀,不僅影響影片的拍攝質量還影響拍攝進度,實在是讨厭,他拒絕記者采訪,并且希望工作人員不要接受記者采訪。
當然,李青的原話不是這樣說的,連夏親耳聽見李青對助理不耐煩地吼,“讓他們滾——”
記者沒有拍到他們想拍到的內容當然不肯罷休,他們改采訪村裏的村民。
村民見到記者和攝像機,圍上去七嘴八舌地用河北話說,可惜村民沒太有文化,沒參與拍攝的也不知道導演拍攝的是什麽,記者從他們嘴裏也得不到太多的信息。
Advertisement
記者随後找到了連夏借住的那戶人家,那戶人家因為收了劇組的錢,加上連夏對他們态度也不錯,采訪時都說的劇組的好話:“那閨女,可倔了,導演嫌她長得俊,她自己用冰水洗手,水裏都是冰塊,那麽冷的天,臉上手上都皴了,跟老樹皮似得,以前那手可滑了,還要挖土,指甲裏都是血,遭死罪了。”
記者聽了也是驚訝不已,對随行攝像師感嘆,“以後誰說她是潛規則上位,甭管說得再像我都不信了,這勁頭兒,當年的蕭文軒都不一定比得上她,太拼了。”
回到電視臺後,結合連夏過往奮鬥史,該記者用《連夏:十年磨一劍》作為标題,對“啞母”做了一篇獨家追蹤報道,在媒體的宣傳下,觀衆對這部戲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導演才華橫溢年輕有為,連夏演得很拼命,至于影片的最終質量,還需要時間去驗證。
*******
和許多文藝片導演一樣,李青也喜歡用長鏡頭,固定長鏡頭、景深長鏡頭、運動長鏡頭,他在作品中對長鏡頭的鐘愛程度,在連夏接觸過的導演中,絕對拍得上前三。
但是這樣對演員也造成了許多壓力,尤其是連夏這個主演,因為長鏡頭需要長時間将鏡頭固定在一點,完全靠演員表演去诠釋,演員稍微出一點錯,整組鏡頭就要重拍。
演員表現得好,長鏡頭可以省下許多成本,若是表現的不好,就是燒錢。
鑒于導演李青絕對控制欲,遇到長鏡頭,劇組往往需要一個白天或者一天一夜去準備。
好在導演也不是沒有菜鳥,雖然他夠年輕,但是經驗絕對算得上豐富,對于一個導演來說,三部影片就脫離新人導演的行列了。
作為主人公秀梅的扮演者,連夏幾乎包攬了影片所有的長鏡頭,這對于她來說已經不能算是挑戰,而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
挖凍土,啃草根,吃樹皮……
被農村的小孩子用石頭和泥巴丢,被村民指指點點,肆意的辱罵和嘲諷。
村裏不少有些中年村民都是經歷過長征的,他們有時候根本不是演戲,而是回憶,回憶他們經歷過的那些艱難地歲月,在拍攝的過程中,連夏越來越分不清楚戲裏戲外的區別,她仿若穿到了四十多年前,她不是連夏,而是秀梅。
她像個普通農村姑娘一樣,揮動着鐮刀和鋤頭,最初這些農活她做得不好,後來越做越好,得心應手。
如今她已經不需要醞釀關于秀梅的情緒,就連導演李青也認為現在的連夏就是他腦子裏那個秀梅。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連夏這樣的狀态很好,連夏越來越沉默,這種沉默不是屬于連夏平時的拍攝狀态,而是屬于啞女秀梅,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她越來越喜歡和飾演麥子的小演員王聰在一起,王聰的父母不在身邊,連夏就是王聰的監護人,兩個人形影不離,劇組工作人員經常看到兩個人用手語對話。
因為導演要求,連夏在劇組外面也是秀梅的打扮,吃和住都住在當地村民家裏,戲裏戲外,小演員并不能很好分開連夏與秀梅的區別,時間一長他連“連夏媽媽”都省去了,直接叫連夏“媽媽”,連夏會護着小王聰,會給王聰洗頭喂飯,他們像一對真正的母子。
一個髒兮兮的啞女,帶着她髒兮兮的孩子,就這麽從電影裏走到了現實。
這一幕落到徐妙珍眼裏,未免有些膽顫心驚的感覺,她感覺連夏入戲太深,已經到了不正常的地步,這種事情徐妙珍以前只是聽說過,“XX演員入戲太深,得了抑郁症,需要心理醫生輔助治療”,沒有想到如今,這種事情竟然在連夏身上發生了。
當然正常人在這種環境下,很難保持正常,就是徐妙珍這個圍觀者,在看連夏吃草根的時候,都會捂着嘴哭,以至于差點沖進拍攝現場,将啞女秀梅和她的兒子麥子救出水火之中,更何況戲裏的連夏。
徐妙珍越想越不對勁,她看着連夏欲言又止,想了想,最終打電話到公司,彙報情況,希望公司那邊幫忙聯系一個心理醫生,她懷疑戲拍完,連夏心理就出問題了。
******
連夏曾經對“啞母”演員構造提出過質疑,“啞母”時間段橫跨那麽長時間,為什麽從“三年-自然-災害”到“長征”近六年的時間,導演卻沒有換“麥子”的演員。
要知道對于一個孩子來說,六年的時間,足以讓她從一個小小人兒長成一個小少年,哪有從六歲到十二歲都是一個人去演,難道“麥子”不長大了嗎?
但是導演李青卻告訴連夏,在這段時間裏的麥子是不會長的特別高大的,因為他吃不飽穿不暖,每天餓着肚子,惡劣的生存環境注定讓這個孩子瘦小,所以導演會借助燈光、化妝、道具、拍攝角度等手段讓“麥子”看起來大一些,而不是換演員。
連夏最初覺得導演這個理由很牽強,直到她來到農村,接觸了很多家裏特別窮的孩子時,她才知道導演說的不錯的。
在這個極度困難的特困村,很多十幾歲的孩子,看起來還不如城市八-九歲的孩子看起來壯實。
在特別窮的,特麽沒有營養,溫飽都成問題的年代,長高真的是一種奢侈。
秀梅一生最悲哀的年份,李青導演全都留給了連夏。
當連夏拍完“啞母”秋篇中三-年自然-災害後,影片的拍攝終于迎來了最高-潮的部分,這也是連夏在“啞母”劇組最後的幾場戲,小村莊最難熬的冬天來了,“文-革”的風吹到了小山村。
此時的麥子已經稍稍長大了一些,因為吃不飽飯,他看上去比同齡的孩子瘦小不少。
麥子和啞巴母親相依為命,這個時候的他已經學會不去問“我為什麽沒有爸爸”、“你為什麽不會說話”這種蠢問題。
小山村到處刷的都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要鬥私批修”、“興無滅資”、“批陳整-風”這樣的口號,很多帶着紅袖章的紅衛兵。
在小山村風風雨雨數百年的山神廟被推了,村民砸了山神像,推到了廟裏石碑,一把火燒了香火旺盛的山神廟。
秀梅看到了,回到家秀梅抱着麥子又哭又笑,麥子很害怕,他不知道母親為什麽會這樣。
他不懂,秀梅生下來就被村裏人說,是山神給她的懲罰,如今山神沒有了,她脊背上的枷鎖沒有了,山神是假的,村民一張嘴山神就不作數了,她這麽些年受的苦,誰來承擔?
山神廟被砸似乎是一切的起點,麥子覺得村裏的人都瘋了,學校裏教麥子的老先生挂上“臭老九”的牌子被拉出去批-鬥,他們砸了老師的家,村長讓老師跪下當着全村人的面承認自己是“資産階級反革-命”,并讓他指出來同夥。
麥子吓得在秀梅懷裏瑟瑟發抖,因為前一天老師還誇他功課有進步。
學校裏不再上課,小村莊唯一的老師被鬥倒了,老先生借給麥子的書,秀梅全燒了,并且不讓麥子和老先生家來往,麥子不理解為什麽媽媽要燒他的書,他覺得老師是好人,他又哭又鬧,跑了出去。
麥子沒想到,等他回來的時候,自己家已經被砸了,啞母秀梅也不在家中。
麥子瘋狂地找媽媽,在村口,批-鬥老先生的臺子上,他看到跪在地上的母親,他們說自己的母親和“資産階級的走狗搞破鞋”。
自己的母親跪在地上,磚頭拴在母親的脖子上,母親像狗一樣匍匐在地上,頭耷拉着。
他們不讓母親吃飯,不讓母親喝水,就讓母親承認自己是“破鞋”。
秀梅被折磨了五天五夜,村民不讓她睡覺,睡了就潑她冷水,冬天,水在秀梅的臉上頭發上結了冰,只剩下半口氣,麥子被村裏人拖出去,村裏的小孩暴打麥子,說他是“資産階級的野-種”,秀梅看到被欺負的麥子,發瘋一樣沖下臺去,和小孩子厮打在一起,她用身體護着麥子,村裏人圍着秀梅打,秀梅身上,嘴裏都是血。
漫漫嚴寒,誰也不知道這冬天什麽時候是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