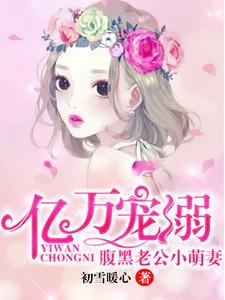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18章
餘之遇确定自己和肖子校不是那種好朋友, 可她又不拒絕這所謂的好朋友。這個細想起來十分危險的念頭蹦出來,餘之遇自己都吓了一跳, 一時忘了回答。
猶如為她解圍, 肖子校在這時把苗苗叫了過去, 說是要檢查她的作業。
小姑娘平時很努力學習,等的就是肖子校來了向他彙報,于是颠颠地跑過去, 老老實實地拿出作業本, 邊翻邊小聲小氣地說自己得了幾朵小紅花。
從窗戶投射進來的陽光恰好落在肖子校身上,他胳膊肘拄在桌案上,手掌托着下巴, 側顏被勾勒得清晰而深刻, 和小姑娘說話時,卸掉了眼尾的鋒芒, 聲音低而柔,迷人的不像話。餘之遇不動聲色地欣賞了小片刻,搶在他發現前跑去幫苗奶奶的忙。
她看到滿滿幾大箱子生活用品,才知道是肖子校送來的。大G再大,能拉過來的物資也有限,所以他其實早在出發前幾天便把東西通過物流發出來了,大部分是給學校的,也有給苗家的。
無論她是否跟來,摩托車一次性也帶不過來這麽多,是李校長提前安排了一輛三輪摩托。也正是因為收到了這些, 苗奶奶才确定,孫女說在學校裏看到校長爸爸的大車了,是真的。
苗奶奶滿懷感激地說:“多虧了小肖,要不然苗苗就得跟着我挨餓了,哪還能上得了學。”
臨水四面環山,可用耕地不如平原地帶多,沿途餘之遇也觀察到莊稼确實很少,可想而知,糧食産量必然不高,但她以為保證溫飽是沒有問題的。
顯然事實并非如此。
苗奶奶說:“周圍都是大山,能保證有水吃就不錯了,根本種不了水稻。村裏的青壯年越來越少,被開墾出來的地都沒人種,即便種上麥子和玉米,雨水少了旱,多了又澇,收成無法保證,全憑老天作主。再趕上個災年,顆粒無收也是有的。”
餘之遇皺眉:“這邊沒什麽特産嗎?”
苗奶奶想了想:“野菜算嗎?以前到時節了我也挖點拿到鎮上賣,但我一個老婆子都能挖到的東西,自然不是什麽稀罕物,都是怎麽拎過去的,再怎麽拎回來。”
對于城市而言,野菜屬于綠色有機食品,貴着呢。可山裏遍地都是,當地人又過着恨不得把一塊錢掰成兩半花的日子,誰會花錢去買?要把這些野菜運到城市去……交通又成一大難題。
征得苗奶奶的同意,餘之遇拍了一些照片。低矮的房屋,黃泥砌的竈臺,用紙糊的牆壁,雞毛撣子,長木凳,裝針線的笸籮,哄小孩兒用的“悠車”,以及破舊的老式桌椅,都是農村的真實寫照。窗上貼的剪紙和小院中那片綠油油的菜地,成了這個貧瘠家庭唯一的生機。
餘之遇眼睛泛潮,有點能體會肖子校初到苗家來時的心情了。
肖子校還要去趟村裏的杜家。杜家有一對年齡相差兩歲的兒女,姐姐去年秋天就到了适學的年齡,可杜家夫婦不肯讓她上學。村長和李校長相繼來勸過,都是無功而返。
Advertisement
作為貧困村,沒錢上學幾乎是家家戶戶共同的難題。除此之外,杜家女主人的腿腳還不利索。把女兒留在家裏照顧母親,在夫妻倆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杜青山作為一家之主,實在蠻不講理,肖子校才開了個頭他便就火了:“窮成這樣上什麽學?上學不用錢嗎?我們又沒人資助。不如再大點去外面打工,掙得是不多,也不至于餓肚子。我不也一天書沒念過,還不照樣過生活。一個丫頭片子,不趁她沒嫁人前伺候伺候媽,還有盡孝的機會嗎?我讓她上學,學啥不得帶去婆家啊。老話不也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嗎?”
因為做記者,餘之遇有幸記錄過很多樸實動人的故事,也見證過太多凄慘沉痛的魔幻現實。但她始終相信,再多的惡,都抵消不了生命原初的本能的善。
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也不僅僅只有杜青山有。和愚孝啃老一樣,這種原生家庭的悲哀依然存在于這個新時代,徹底消除掉或許還需要很長時間,很多人的努力。
杜青山的理直氣壯,卻讓餘之遇忍無可忍,她沒給肖子校講道理的機會,語帶機鋒地說:“你把生活過成什麽樣,自己心裏沒數嗎?打工?她才多大?國家有禁止使用童工的規定,你沒讀過書不懂法,當所有人都和你一樣無知嗎?還女子無才便是德,別在那斷章取義了!那句俗語出自清朝張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原文是: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殊為未确。知道什麽是‘此語殊為未确’嗎?所謂‘此語殊為未确’是說,‘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話語的說法是不正确的!以後別拿這話說事,丢人現眼。”
無論是口條,還是知識儲備,杜青山遠比不了餘之遇,想截斷她都不能。他被一個小姑娘教訓,氣得臉紅脖子粗。
肖子校第一次見餘之遇和人吵架,那麽長一大段話,她草稿沒打,語速還快得連标點符號都省略了,也是讓人佩服。尤其杜家他來過不止一次,道理統統講過,卻全都對牛彈了琴,現下有個人能當頭罵杜青山一頓,倒挺解氣。
卻不能讓她在自己眼前吃虧。
見杜青山紅着眼要上前,肖子校一手将餘之遇拉到身側,原本拿手機的右手倏地一擡,手機直接抵上杜青山額頭。
他甚至連話都沒說,只是用那雙沉湛犀利的眼盯着杜青山,杜青山便沒敢再上前。
杜青山對肖子校有些了解,知道他是城裏來的文化人。起初他沒瞧得起,直到聽說小學校蓋新樓的錢是肖子校找來的,而見到肖子校時,他發現這位孩子們口長的“校長”一點不文弱,不說話的時候,眼神冷得能把人凍死,一笑又俨然換了一個人。他沒文化,形容不出肖子校的氣質和氣場,直覺認為這人挺厲害的,不好惹。
他胸口起伏醞釀半晌,終究沒敢動餘之遇一指頭,又實在氣不過,便抄起掃把趕人,同時胡攪蠻纏道:“我是她老子,她上不上學我說了算。你們想讓她上學,行啊,你們出錢,再找人照顧她媽,否則想都別想。”
餘之遇也不知哪來的力氣,差點把掃把搶下來,要不是肖子校攔着,她怕是要反打杜青山一頓了。
肖子校到底對村裏的人和事有所了解,比較沉得住氣,為了給她消氣,還給她講了個故事。
他曾去過一個比臨水更窮的村子,村長好不容易搞了個項目,給每家每戶發了兩頭小毛驢,本意是讓村民把毛驢養大,通過繁殖或是育肥出售來獲得收益。結果沒兩天,就有村民把毛驢殺了吃肉。他們有的說,人都餓着,哪兒還有東西喂驢?有的說,反正國家在搞扶貧,用得着自己辛苦養驢?
餘之遇聽得火起:“國家花那麽大力氣扶貧,到頭來扶出些懶漢啊?”
肖子校示意她稍安勿躁:“沒有幫扶之前,貧困戶們為了生存還自己幹點農活,有了扶貧政策和扶貧款後,有些人因沒受過教育,思想出現偏差,居然只想等救濟。要扭轉他們這一思想,就得教育先行。扶貧先扶智,治貧先治愚。”
他意在告訴她,和杜青山難以溝通,是文化素質差異導致的。要改變這一現狀,唯有教育。
肖子校屈指敲她額頭一下:“要知道你會真動氣,絕不帶你來。”
“誰讓我是汽水做的,易怒呢。”餘之遇被敲疼了,邊揉邊嘀咕:“職業病,随時随地都能給人上一課。”
她沒說和杜青山吵架也有他的因素在。杜青山應該是知道肖子校資助了苗苗,話裏話外都透露出嫉妒,餘之遇其實擔心肖子校會把杜家姑娘上學的事也攬上身。資助貧困學生是善事,可做善事的人不該被道德綁架,況且肖子校一個人也不可能把全國貧困的學生都資助了。尤其杜家的情況也與苗家有所不同……
思及引,餘之遇恍然大悟:“對于選擇資助誰,你肯定是有考量的,對吧?”
肖子校笑:“我又不是傻大款。”
餘之遇被他的用詞逗笑,她說:“你說扶貧先扶智我認同,但要是二者同步進行不是更好?懶漢畢竟是少數人,只要有人先富起來,自然會有人跟。”可想到苗奶奶的話,她又犯難:“政·府對臨水有幫扶政策嗎?
“一直有。否則就靠那麽點農用耕地,村民們怎麽生活?”聽到身後有拖拉機的聲音,肖子校不動聲色地走到外側,把她護在裏面:“可解決不了導致貧困的根本原因,找不到地域性的潛在資源優勢,也是年年扶貧年年貧。”
這個道理餘之遇懂。扶貧并非只是給錢給物,而是以貧困地區自力更生為主,外部力量幫扶為輔。否則那不是扶貧,而是“我養你”。那些個別沒志氣的人,也是因此成為懶漢的。
幫扶不難,自力更生卻要有産業,這個産業就是肖子校說的地域性的資源優勢。
餘之遇看看被山巒包圍的小村落,一時間找不到産業的方向。
她的沮喪那麽明顯,肖子校想忽略都難,他沉默了幾秒,說,“除了山上那些藥用植物,這裏确實什麽都沒有。但藥用植物能否成為這裏的特色生态資源,還需要驗證。”
餘之遇一點就通,她眼睛倏地一亮,抓住他的手,聲音是壓不住的激動:“你的意思是要做一個中醫藥扶貧項目?”
肖子校注視她隐隐發光的眼睛,眉梢微揚:“我的興趣和本職工作只在于道地藥材研究,能否成為扶貧項目,不是我能決定的。”在沒有絕對的把握前,他從不會把話說滿。
餘之遇晃了他手腕一下,微微嗔道:“過份謙虛等于驕傲,小肖教授你能真誠點嗎?”
肖子校發現她心情好,或是有求于他時,便喜歡稱呼他“小肖教授”。他笑得無聲,稍一垂眸,目光落在她手上:“我真誠地提醒餘記者,村民思想保守,我們這樣拉拉扯扯,放在從前是要結婚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唇邊的笑意還沒散,餘之遇甩開他手時回敬道:“放在從前,三十歲還沒結婚,你就是重點扶貧對象。”
肖子校有點好笑地看着她炸毛的樣子,感慨了一句:“也不知道國家分配的,什麽時候到位。”
作者有話要說: 餘之遇:“我怎麽覺得進山像是羊入虎口?”
肖子校:“……我還什麽都沒做。”
作者:“人家的小手你摸了,你的小腰也讓人家摟了,你還想做什麽?”
肖子校:“你天天在哪琢磨給我使絆子,我還能做什麽?”
--------
我以前一直不懂為什麽扶貧先扶智。直到去年《漁火已歸》完結後去內蒙采風,到了興安盟科右中旗的一個扶貧村,聽村書記講了那個關于毛驢的故事,我才知道有人因生于貧困,因沒有受過教育,而甘于貧困,且不願自力更生,只等着國家救濟。
而在那個貧困村,也有一個養老院,因為有一些政策上的扶持,能夠給予村裏的老年人集中的照顧,為年輕人解決了一部分後顧之憂。當時我就在想,也許有一天,我在《漁火已歸》中設想的康養小鎮,真的會有。
--------
大家別錯過上章的雙倍紅包哈,金額不大,留着看文呗。
這章依然2分留言送紅包,明天十點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