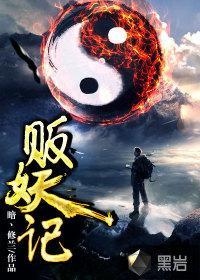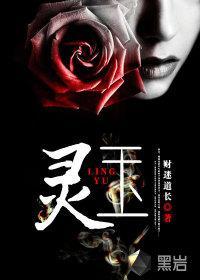第5章
風和日麗,鳥語花香,天下太平,普天同慶。
唔……
三年窩在這鄉下地方,天下太不太平他其實不太清楚,不過既然衆人都這麽說,那就當是這麽回事吧。畢竟,福平縣以及幾個臨縣的确長年和樂無憂,對于他們這些偏鄉芝麻官,一個縣也确實是他們的天下。
「呵呵呵呵……」順應着那些難令人上心的話題,江蘭舟配合地笑着。
類似的對話已經持續了将近三個月,也莫怪他要當成耳邊風了。一開始,永鹿縣的林大人發了請帖,說是家中孫子擺滿月酒,邀這附近幾個縣的縣令過府一聚;衆人相談甚歡,接着去了齊玉縣赴黃大人的壽宴;隔沒幾日換石成縣的吳大人辦賞鳥宴。
數日過去了,沒再聽聞任何消息,以為告一段落,不想山城縣的李大人竟來了封信,說非得邀他過府一躺。去了方知是為年初傳喚仵作的誤會致意,大張旗鼓請來了客滿樓的名廚與人稱肅州第一的舞伎,留宿的三日裏便這麽夜夜笙歌到天明……
眼下,輪到被趕鴨子上架的江蘭舟了。福平從前産玉,早年開采過度,近年蕭條許多;辦不成賞花玩玉宴,只有把壓在箱底的茶拿了出來,邀了幾位大人過府論棋品茗。
「江大人,」林大人啜了口嬌小杯中冒着香氣的茶,問道:「這可是招國采州産的水金龜?」
「林大人舌頭好靈。」江蘭舟點頭應着。從前在京中學人附庸風雅,當時只為融入同僚,增添話題;買一次茶,可耍同樣把戲兩回,也算值得。他轉頭對鷹語說道:「吩咐備好茶盒,晚些讓各位大人提了回去。」
「是。」在諸位鄉下縣令無趣的對話中,早已白眼翻透的魏鷹語領命退下,樂得耳根清淨。「在下這就去準備。」
「有勞魏師爺了。」
京城來的人果然是有些不同的,說起話來就是斯文許多,一舉一動也賞心悅目,不只魏師爺如此,江大人也是。衆縣令微笑目送魏師爺離開,再轉回茶盤前。
江蘭舟将滾水稍稍放涼,才沖入壺中,接過幾位大人的空杯,又再添茶。
「方才聽魏師爺說,平日江大人在府裏若無事,便是下棋,今日一見,果真棋藝高超哪。」發話的是黃大人,一笑,那福态臉上的橫肉便歪了歪。「本官的老丈人送過本官一副好棋,黑子白子都是上等石子磨的,改明兒個就讓人送來給江大人吧。」
……分明方才他與鷹語對弈又是滿盤皆輸,不知黃大人從哪兒看出他棋藝高超?若鷹語在,肯定又是一番白眼相對。望着那笑臉一陣,江蘭舟語帶為難應道:「那怎麽行,是您老丈人送的,理當好好收着。」
「哎,本官不谙棋,收了也是浪費。」黃大人很堅持。「放在書房角落都蒙塵了,江大人就莫要推辭了吧。」
Advertisement
「是呀,江大人,您就收了吧。」另一頭的林大人幫腔道:「不過……有了棋子,沒好的棋盤怎麽成。本官那兒正巧有張雲紋棋盤,湊成一組送來給江大人吧。」
「呵呵呵呵……」江蘭舟不置可否笑着。來到偏到不能再偏的偏鄉了,官還是官,官場依然是官場。
「啊呀,那本官可沒什麽能給江大人的哪。」聽着另兩人的話,這回換李大人很煩惱地啧了聲。「不如本官就當江大人的棋友吧,山城離福平最近,本官也可月月來此與江大人切磋切磋。」
「李大人真是的……」黃大人笑容裏有些惱意,沒想到自己的棋子成了李大人的墊腳石。
「江大人屆時一定會邀我等一同前來的,是吧?光兩人下棋多悶哪!」林大人順勢接道:「今日江大人、魏師爺開啓我等對棋的興趣了,可一定得教教黃大人與本官,否則長日漫漫真不知作何排遣了。」
「可不是。」眼見話題被林大人圓了回來,黃大人趕緊又道:「其實李大人也無需勉強的,誰不知李大人您風流多情,閑來便上府城春滿樓,這一來一回,可得花上三日有餘呢……話說回來,上月您悄悄邀了江大人與吳大人,不就是安排了紅牌舞伎過府?」
「是哪,李大人真不夠意思,」與黃大人交換了眼神,林大人繼續與他一搭一唱。「也不邀黃大人與本官同來一睹其風采,是存心排擠我等嘛……」
幾次聚首,隐約感覺黃、林兩位大人連成一氣排擠李大人,好在今日吳大人身體不适,未能一聚,否則情勢成了二對二,要是當場鬧開了要他
選邊站,那他就頭大了。江蘭舟繼續裝傻。「呵呵呵呵……」
眼見矛頭全往自己身上指來,李大人摸摸鼻子,轉道:「其實……春滿樓自然是好,可幾位大人可曾聽聞,原來這福平縣碧落閣的姑娘也是個個如花似玉,比起府城那些個給人捧慣了的紅牌,絕對是聽話溫順許多。」
語落,黃、林兩人交換了眼神,不說話。
文人、官僚上青樓聽琴、吟詩、議事,是自古以來便有的事;江蘭舟沒想到的是,言語間沖突不斷的幾人,提及了溫柔鄉,嘴皮也就軟了。
李大人見衆人沉默,心下冷笑,道:「江大人可否為我等安排安排?」
「自是可以。」他也沒理由在這節骨眼上拂了李大人的臺階,表明自己偏向了黃、林兩位大人的黨派。轉頭,江蘭舟招來一旁的賈立,道:
「你到碧落閣見日陽姑娘,請她張羅晚宴,甘鸨母那兒我回頭再打聲招
便成。」
賈立聽着大人的話,暫時沒有回應。
在京裏時,大人只在府中設宴,推不掉帖子去了青樓,也從不留夜。
來到福平後,每月總有幾日在日陽姑娘那兒流連忘返,他與鷹語只當大人悶得發慌所以找個心細的姑娘談天說話,男人最失意寂寞時,身邊有個女人安撫着總是好的;可如今,如此張揚地帶上幾位大人到碧落閣尋歡作樂,是轉了心性?
江蘭舟對上了賈立遲疑的眼,令道:「即刻去辦。」
「是。」賈立抱拳領了命,退出庭園。
手邊新添的水燒開,江蘭舟又為幾位大人加了茶。
「話說回來……」繞了大半圈,黃大人終是忍不住說到了重點:「前些日子那個殺人案子,江大人真是審得好呀!」
「讓幾位大人見笑了。」語氣謙遜中帶點無奈,江蘭舟應道:「延宕多時,幸而能破。」
「江大人謙虛了。」林大人搖搖手,說道:「一個人自京城來此經商,遇上所愛,最終卻死在愛人之弟的手裏,想來也是造化弄人……若不是江大人明察秋毫,又怎能還死者一個公道?州牧大人對江大人是贊賞有加,還要我等向您多多學習、多多讨教哪。」
「是呀、是呀。」黃大人連忙點頭如搗蒜,搶在李大人開口之前補充道:「江大人曾在京中任官,見識、人脈都廣……最重要的是,本官聽州牧大人說,大理寺的寺臺陳大人很是關心此案,欲請您上京一趟,當面問問一個稚童如何能下此毒手,您又是如何抽絲剝繭,好作為往後同僚辦案的參考--」
「是呀!畢竟那實在太可怕了,不過是個十歲的孩子呀……」李大人見縫插針道,搖頭嘆氣再嘆氣。「真是太駭人聽聞了哪!」
黃大人瞥了他一眼,冷哼一聲。「倘若當初江大人上本官那兒傳仵作,也不會傳了一月仍傳喚不來,為破此案還不惜跋山涉水到日江,自個兒掏腰包聘仵作為己用,此案便能更早了結。」
「可不是?」林大人也跟着哼了聲。「那麽此刻江大人已在京中與昔日上司的寺臺陳大人飲茶賞花了哪。」
「咳咳……」反駁不了,李大人臉紅了紅,半晌,道:「總之……若是江大人上京那時,若是這個……那個……寺臺大人問起,可得請江大人為本官……呃,本官是說為我等美言幾句呀。」
三年從來無所交集的數人,這轉眼間的轉變,全是為了京商被殺的案子送呈了州牧,又轉送大理寺協助運屍回京交還家屬的事宜,才會弄得衆所周知;換句話說,若今日死的是個本地人,無需勞師動衆運屍回京,沒有層層知會,此刻大約還是悠閑院中下棋。
趨炎附勢是人之常情,江蘭舟自是明白幾位大人的心思,微微一笑,回道:「江某已修書一封,上呈陳大人。當中詳述辦案過程,陳大人讀過之後,會當允許我不必上京了。」
語落,三人呆滞地望着他。
「當中詳述辦案過程,自也不會漏了平日幾位大人對江某的照應。」
江蘭舟補充着。所謂的辦案過程便是将開堂審案所錄下的案帳、屍帳重抄一份,加上陳大人問及是否見過臨縣同僚,他便照實回說見過了;至于是案發前抑或是案發後見過,就無需詳述。陳大人身居廟堂,位高權重,成日在朝中想着如何扳倒擋在身前之人,是何等的老狐貍,眼下這等的班門弄斧,還是別提了吧,省得弄巧成拙,給衆人招禍。
「原來是這樣……」
「不上京了,是有點可惜……」
「是哪,但……将來總有機會的……」
三人未免有些失落,可聽聞江大人已在信中提及自己,已是夠好的了。京中大官,每日要見多少人,每年又有多少新人争相投入門下效命,若沒信任之人提及,轉眼便忘。
近來聽聞江大人從前得寺臺陳大人重用,是為人陷害才遭貶;陳大人暗中相助,先将其安于福平縣令一職,待找到适當時機,自然是會将之調回京中的。如此想來,與江大人打好關系只有好處。
若是早點收到這重要消息,他們也不會遲了三年才與江大人交好。要怪就怪當年江大人上任時他們打聽到的消息有誤;那時的版本,分明是江大人犯了過錯被眨,又得罪上頭,永世別想翻身,旁人最好也避遠些,否則難保不遭池魚之殃。
唉……将幾位大人的表情盡收眼底,江蘭舟暗自搖了搖頭。
若要跟風,就得要先學看風向;可風呀,哪裏是人抓得住、摸得透的?哪日上頭的人轉了念頭,便是風雲變色,教人措手不及。
不如閑下心吧。
在福平縣平靜了三年,遠離京中是非,是不差的,如今見到眼前幾位大人老來還懷抱升官夢,也是頗有趣;京裏,多少人争了一世,到頭來才發覺一場空,卻已深陷泥沼難以抽身,偏偏在外頭看着的人是霧裏看花,硬是要往這渾水裏跳……
反正,三位大人的這般野心、這等手段傷不了人;再者京中已無他落腳之處,若要在福平待着,沒必要再為自己樹敵。這是為何他答應了李大人的要求,于碧落閣設宴款待;這段日子受了幾位大人的招待與好處,禮尚往來,免去人情積欠方是長久之計。
為官的,最上手的技能之一便是話題的轉換。沉默只持續了短短片刻,三人便又聊起了一日來嘗過的幾款茶,個中滋味是多麽多麽苦澀、又或甘甜、又或清新……
江蘭舟靜靜聽着,但笑不語。
又過一陣,鷹語與賈立一同歸來,衆人見天色不早,便要動身前往碧落閣。
命了鷹語領在前,招呼幾位大人出了庭圜,江蘭舟壓後走在回廊。
前方還能聽見李大人訴說當年勇,另兩位大人冷聲諷刺,轉頭,瞥見的是一幅寧靜畫面。
回廊尾處的屋檐下,少年趴在雕花窗前,手中一根長長的草,輕輕穿過窗,在外頭的水盆中畫圓。
草尖劃過水無痕,但少年仍一圈一圈又一圈。
瞅着那自殺人案子結束後便空白至今的眼神、臉容,江蘭舟整日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柔和了,薄唇彎出弧度。
相安無事,天下太平;同時,也無聊透頂呀……
望了許久,他垂下眼,再擡起時,喚來了一旁的小仆端來筆硯,寫下幾字,交代了幾句話。那時,鷹語久等不到人,回頭來尋,小仆已然退去。
鷹語睨着小仆背影,江蘭舟笑着解釋道:「見知行閑得慌,允他至我書房翻翻書。」
魏鷹語也笑。「大人那些棋譜只怕陶仵作見了更無趣吧。」
「怎麽這麽說嘛,裏頭還有別的書呀。」
「大人說的是那些比棋譜更無趣的陳年案帳?陶仵作連前幾個月的案子都不感興趣了,更何況是那些舊案……幾位大人已等得不耐煩,賈護衛領路先行,我等也快快跟上吧。」
「……好好好,真沒見過哪個師爺這麽對縣令說話的……」
水面的圓,很飽滿。
可這圓,無論畫得再快,怎麽就是畫不全呢?
陶知行手裏一根草,穿出石花窗,輕點窗臺上淺盆裏積滿的雨水,每畫一圈,就自問一回。
來到福平四個月了。最初的兩日進出惠堂,為了案子的事忙碌,接着……接着就閑下了。
離開日江時大哥交代得匆促,只說從前在京裏的故友需要幫助,他分不了身,所以讓她跟着來到福平縣衙待着兩年,還說讓她以男裝身分見人,較能方便行事;三哥則說大哥早已看穿她的不安分、不認分,這兩年就讓她出去闖闖,切記莫要給大哥添亂。
兩位兄長的話陶知行謹記在心。縣衙不比自家,房裏她不敢堆放自制的藥粉草藥、檢驗書籍、各式器具;院裏更沒有小木屋任她擺弄肉塊、骨頭、髒器……能離開香到鼻子發癢的香行,她很知足的,真的。
大哥放她出日江,已是天大的恩惠了,不可再奢求更多。
她觀察過,這府裏的人不多,個個都頗閑,院中時常日上三竿才見得到人影,或下下棋,或說說話,過午似乎還有午睡習慣,睡醒了又是下下棋、喝喝茶,看完日落便各自回房歇下。
原以為是這福平民情,入境理當随俗,她也跟着躺到近午才下床,繞着庭園散步,偶爾被叫去觀棋飮茶,一日過一日,直到有日出門寄平安信給大哥,方知原來福平無異于其它地方,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閑的,只有縣衙。
這……合該是好事吧?
縣衙閑着,意味着管區內和樂平安。一個仵作無用武之地,那麽,大哥送她到此,當真只是為了将個麻煩鬼支開?
将手中的草換到另一只手,陶知行撐着臉頰。
她試過從這庭院中的每個角落看同一處風景,樓宇、小亭、回廊,數着會在府裏出現的人們,小仆、衙役、賈護衛、魏師爺、大人……同樣的景、同樣的人,變化的只有愈發盛開的花、萌芽的樹,與越來越綠意盎然的庭院。
真是令人……提不起勁。
對于生意盎然的事物,她提不起勁。
畫圓的手微停,瞅着一只小麻雀飛到了水盆邊上,蹦跳兩步又展翅高飛。陶知行目光随之放遠,落到了回廊另一頭的小亭中。
臨縣的幾位大人一早來到了府裏,在小亭石桌上擺了棋盤、棋子,石階上架了炭盆鐵壺煮茶,看似十分專注地研究棋藝。衆人有時大笑出聲,有時争執不下,模樣非常地投入;若不是他們圍着一張棋盤,她會以為幾位大人談論的是國家大事。
陶知行黑眸落在一張白淨帶笑的側臉。魏師爺說大人纏了他三年,日日在亭中下棋對弈,夜夜在書房鑽研棋譜,如今又邀人過府下棋,說大人愛棋成癡應當不假。
……望着那總帶着淺淺笑意的臉龐,陶知行想起那個她在小亭中大口吃肉卻老被打斷、順帶聽到了很多她并不想知道的事的午後。
不想知道的事……好比說,她的驗屍結果讓一個十歲的孩童定罪;好比說,魏師爺在外人看來是大人的左右手,實則是被派來監視大人的一舉一動;好比說,大人手中握有某樣重要的東西。
她并不想知道這些。
一旦聽見了,該想的,是如何消去、忘卻。
遠方忽而轉大的談話聲打斷了思緒,陶知行皺了皺眉,移開視線,又專心地拿着草在水面畫圓。
她的世界約莫就是這副石盆裝水的模樣吧?裝不滿,也倒不幹,風再如何吹皲,草再如何劃過,也只是在表面,烙不下痕跡……
手中的草有一下沒一下地輕點水面,陶知行又趴低了身子。
「--阿九……阿九!」
意識過來時,幾聲叫喚由遠而近,陶知行循聲看去,是一府中小仆。
就見他快步來到自己面前,遞出手中一張對折的紙條。
「大人交代要交給阿九,請阿九即刻過目。」小仆說着。
将長長的草銜在嘴邊,陶知行依言接過,卻未打開,直覺望向回廊另一頭。
小仆也跟着瞥了眼無人的廊下,道:「大人帶着三位大人與魏師爺、賈護衛上碧落閣去了。」
上青樓呀……還以為他與其他當官的有多麽不同呢。應了聲,見小仆退下,陶知行低頭打開手中紙條。
沉穩的字跡寫着:其一,麻香。其二,書房,西二。
「……」打啞謎?陶知行嘴角抽了下。
麻香指的應是大人贈與她的麻香堂麻油……是了,那日大人似乎提及有兩件事要同她說,不過那時她沉迷于純正金标牧童戲水瓶身,沒留意大人後來說了些什麽。
書房、西二……指的又是什麽?
府裏有書房的,就只有大人和魏師爺……轉轉眼,陶知行吐掉口中的草,回身邁步。
推開門,一股淡淡松墨香。
陶知行立在敞開的門邊,環顧陰暗窄小的書房內。
本就不甚寬敞的房內被書架圍起,遮了窗,只留了一點隙縫,于是顯得昏暗。四面靠牆擺放書架,相隔一人能通過的距離,再擺了第二圍書架。陶知行來到狹小的走道中擡頭,書籍一層疊一層,令她頓時有些頭暈。
書房中央一張長案,案上是文房四寶、棋盤棋子,幾本棋譜攤開,一本壓一本,細看最上頭那本,朱色的字跡圈了幾圈。
「西、二?」按着棋譜經緯讀出,陶知行弓起纖指,撓撓頭頂。她再一次攤開了手中紙條,盯着西二兩字。
不是巧合?
可是真的太難懂了……陶知行斜靠在案上,雙手環胸;那刻,日落西山,些許光線穿過窗、穿過書間隙縫,染了書房一束暖意。
呃,該不會……這也不是巧合?
陶知行緩緩轉向書房西面,看了老半天,看到天都黑了,她點上燈,來到書架間翻着一本又一本的棋譜,忽地發覺靠牆的書架下層,最陰暗處有幾口蒙塵的箱子,她蹲下身将之一一拉出。
抹開了塵,手中的燈照在箱上的字。寧武七年、寧武八年、寧武九年、明永一年、明永二年……
直覺地解了箱封,打開。
手抄的陳年案帳數本相疊,幾捆布包攤開後是各式檢驗器具,當中一包令她手中一頓,只因上頭繡着大哥的名字。
這捆器具她自是識得,是陶氏檢驗用具,由家族中領後輩入門的長輩傳下,她也有一副;只是她的多加改造,與眼前大哥從前用過的傳統器具相比,已有多處相異。
仵作各派有各自手法,檢驗器具向來不外借,此物曾是大哥的,又怎麽會到了大人手上?大哥在京中的最後幾年已是無心仵作工作,但能讓他将器具相贈,想必深得大哥信任。
信任?
……這是為何大哥連代代相傳的陶氏檢驗錄也能奉送?甚至連百勸不聽、恨不得鎖在自家地窖中直至醒悟的小妹,也能放心相托兩年之久……
陶家人一向相信證據多于其它,至少,她難以将信任投注在一個活人身上;能得大哥完全信任之人,是怎麽樣的一個人呢?
只一瞬,陶知行甩甩頭,甩掉這陌生又莫名的念頭。研究一個活人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理解了他的當下,并不代表能永久理解,更無法判斷其行徑;沒有意義,自然不該多花心思。
握着手中的布包,考慮了片刻,陶知行又往箱中深處挖着。這箱東西不是活物,在福平的日子也還有許久,既然如此,就……打發打發也好。
這麽想着,陶知行翻出了整箱的陳舊物品後,箱底一張雪白新紙寫道--
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