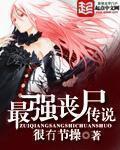第5章
姐弟倆肚皮吃得圓滾滾後,便分別窩在對應的量角落鋪得厚厚的稻草堆裏一夜安睡到天明。
起床後,姐弟倆先是生篝火,用了一竹筒的溪水燒成熱水、用粗布以及咬去皮兒的柳條簡單的洗漱一番,這才不慌不忙的做起了早餐。
姐弟倆的早餐與往日一樣,不一樣的不過是在一鍋野菜湯裏丢了一小把雜糧。快速地吃完早餐,姐弟倆便出了破廟,開始新一輪采摘山珍。
這一次采摘的山珍,楊令月依然準備拿去賣,所賣的銅板沒有拿去買糧,而是存着,等數量足夠多時,拿去買可以用來做種的種糧以及蔬菜種子。
如此一來,便又是一月過去。等可耕種的糧食種子和蔬菜種子買了回來後,楊令月抽空去了山腳底下的小村落,找村裏正家的借了一把鋤頭,一把斧頭,又用一些珍換了一把菜刀,這才回到破廟,領着楊明達一道在破廟的庭院中,開荒種菜。
所買的糧食種子,姐弟兩人是在距離破廟不遠處、地勢較為平坦的地段,這兒靠近小溪,來往倒也方便,所有便種在了這兒。
當然,由于女孩子的力氣着實不大,所以開荒種植需要的力氣活都是小三歲的楊明達做的,至于楊令月則用楊明達用斧頭砍的灌木,做了一個外形粗糙、卻實用的織布機。
楊令月之所以會做這玩意兒,完全是因為她在鄉下的外婆家也有木架結構的古織布機,小時候待在外婆家外婆織土棉布時,還給乖乖待在一旁看織布的楊令月講解過這玩意兒該怎麽使用,再加之後來接觸電腦,曾搜索過古織布機的詳細資料,所以這次楊令月才能像模像樣的做了織布機出來。
楊令月做好織布機後,便将曬幹的荨麻莖皮撚成比細毛線一樣大小的線條,再用這些線條小心翼翼的鋪到木質織布機上,除了剛織時有些不順暢、織得亂七八糟的,後面倒也織得像模像樣,幾日忙活倒也織出了幾尺荨麻布來。
只不過楊令月雖說織出了布,但卻不會做衣裳,無奈只得撿了半籃子的山珍,與楊明達一起去村裏正家還鋤頭、斧頭時,央求大娘教自己做衣裳。
“你這是麻布吧!”大娘仔細翻看着手中草木顏色的荨麻布,贊嘆的道:“你這姐兒的手算巧,這布織得不錯,摸着也不怎麽粗糙,倒是可以用來做衣裳。”
“大娘,我也是這麽覺得的,只不過娘親去得早沒怎麽教我做衣裳,就算如今我織出了布,卻有心而無力。”
楊令月笑得甜甜地說道:“我知大娘是個心善的人,大娘如果不覺得麻煩的話,就簡單的教教月兒怎麽剪裁、縫制衣裳吧。”
“哎喲,你這姐兒的嘴可真甜。得,大娘就好好的教教你怎麽剪裁、縫制衣裳好了。”
大娘笑眯眯地打算領着姐弟倆進門,只是姐弟倆還來不及進門,就見村裏正家的大兒媳婦,面露鄙夷的道。
“娘,你怎麽香的臭的都往家裏領,污了地兒不說,別到時丢了東西就不好了。”
此言一出,大娘當即變了臉色,喝罵自家這看不懂人臉色的兒媳婦。“你在這兒胡咧咧的亂說啥,沒眼力見的東西,別逼我這個做婆婆的将你攆回娘家去。”
自家老大娶的這個媳婦,大娘一開始是不願的。人懶不說,還眼皮子淺不會說話,可以說除了那張長得俏麗的臉,沒有一點的優點。可誰讓她家和自家是從小定的娃娃親,雖說看不上這個大兒媳婦,但為了避免被人說不講信用、無仁義,怕會影響自家老頭子在村裏的地位,所以大娘只得咬牙的認了。而老大家的自從進門後,也低眉恭順的一段時間,沒曾想,今兒卻一不小心又裝不住、原形畢露了。
其實這也怪不了村裏正老大家的,畢竟就楊令月姐弟倆的形象,雖說所穿衣物都采了皂角漿洗得幹幹淨淨,可破破爛爛、大洞套小洞、顏色慘白、看不出原色的衣衫,也別怪眼皮淺的村裏正大兒媳婦一見他們就面露鄙夷,認為他們是利用大娘的同情、準備上門打秋風的乞丐兒。
楊令月滿心憤怒、有些想罵上幾句,但他們如今情況如此、怪不得別人鄙夷,所以楊令月只得忍了憤怒,先是安撫同樣憤怒得眼眶兒都紅了的楊明達,沖着大娘露出怯生生的微笑,故作局促不安地說道:
“大娘,我和明哥兒就不進屋了,就在這屋檐底下學就行。”
大娘可有可無的點點頭,說聲‘丫頭等着’,就進她和村裏正所住得正房,拿出放有針線的籮筐,就在屋檐底下的臺階上坐下,耐心而又細心地教楊令月怎麽剪裁布料、縫制衣裳。
楊明達是男孩子,對這些拿針撚線的女兒夥計是十分不耐煩聽的。不過卻還是跟着楊令月,百般無聊的撿了一根細木棍,在那兒捅着螞蟻洞玩…
楊令月本是個聰慧的家夥,加之她的實際年齡不是如今的十歲,再加之大娘講的細心而又耐心,楊令月學了一上午,倒也像模像樣地剪裁出适合楊明達身材的布料,只得回家時、再耐心的将各部分縫上就成,要知道大娘問明了楊令月如今所住的那個破廟家什麽都沒,不止讓他們将鋤頭、斧頭拎回家,還送了楊令月一卷棉線、幾根根繡花針,一把半舊卻還是很鋒利的剪刀。
“謝謝大娘。”楊令月眉開眼笑的對大娘道謝道:“等明兒我讓明哥兒給大娘送些曬幹的山貨。大娘別說拒絕地話,你對我們姐弟倆的好,我們姐弟倆都記得心裏呢。送些不值幾個錢的山貨只是聊表心意罷了。”
“你這丫頭就是會說話。”被一通好話恭維得歡喜地大娘更加喜歡楊令月的知情識趣。在此時輕飄飄地大娘心中做她的兒媳婦也是夠格的。不過鑒于楊令月是個沒爹沒媽的孤兒,又有年齡比她小的弟弟拖累,所以這個想法只是在大娘心中過了一遍便随之抛于腦後,只笑呵呵、如同彌勒佛一般目送姐弟倆各自拎着東西、相攜往山上走去。
春去秋來,女真兵克撫順的消息傳開後,京師附近的城鎮的物價再一次飛漲。原本幾個銅板就可以買一升的大米變成如今五十個銅板一升,就連平時用來做畜生口糧的麥麸、豆渣都變成了雜糧一樣的價。
“幸好姐姐夠聰明,早早地買了種糧自己種植,不然咱們到了寒冬臘月只得上街乞讨去了。”
楊令月站在收拾幹淨地破廟門口,一邊收拾翻曬的菜幹、鹹菜,一邊慶幸地對正在用斧頭劈柴的楊明達道:“等明兒姐姐再去耿家村用山貨換些雞鴨鵝毛,這樣咱們姐弟倆今年除了羽絨服,還有羽絨被蓋了。”
耿家村便是山腳底下的小村落,因為村子裏大部分都姓耿而得名。将山上大部分生長的野生荨麻收割後,楊令月加班加點、紡織了很多的荨麻布。雖說布料稍顯粗糙、有些割皮膚,但因為姐弟倆根本就沒有那個錢買細棉布,便用原色的荨麻布做了幾套适合春夏穿的衣裳,換着穿。
至于楊令月口中的羽絨服和羽絨被,則還是因為姐弟倆沒有那個錢買棉花做棉衣、棉被,所以只得用采集、曬幹的山貨換取村民們殺雞廢棄不要的雞鴨鵝羽毛…楊令月算了算,她換取的雞鴨鵝羽毛再加之楊明達好運抓到的野雞羽毛,剛好能做一床羽絨被和兩套鑲嵌有羽絨的衣裳,她再花時間攢攢,再多做一床,免得姐弟倆為了取暖而擠在一起睡。
楊令月心知,依她的織布技術要想将布織成後世衣服那樣細密、厚實,那是完全布可能的。要只得羽絨服這種玩意兒,即使布料再細密、厚實,也無法阻擋羽絨鑽出來,所以楊令月只得采取将羽絨壓縫進織得密密的荨麻布裏,然後再在外套一個同樣大小的被面。這樣做應該能減少羽絨鑽出來的問題吧。
作者有話要說: 更新o(* ̄︶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