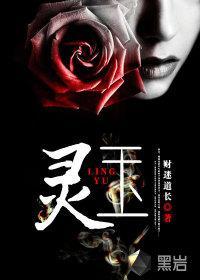第24章 二十四、原來要這麽多時間
二十四、原來要這麽多時間
張萱琳對醫學專業的選擇是被動的,那是由父母幫她做的選擇,或者說,那個選擇是在她全家都糊裏糊塗的情況下做出的。
只是因為醫學生的身份說出去比較好聽,且好一些的大學的醫學專業錄取分數高,不會浪費了張萱琳考出來的分數。
家裏誰都不知道醫學生是怎麽回事,要經歷怎樣的過程,要付出什麽得到什麽才能成為醫生,也都不知道如何成為醫生,之後要面臨怎樣的困境,要克服怎樣的難題,要在怎樣的環境中工作,要過了多少關卡才能成為他們日常在醫院裏見到的醫生模樣。
一家子都是對醫學之路極度陌生的糊塗蛋,從老的到小的。他們卻在讨論了十五分鐘之後,就渾渾噩噩地決定了張萱琳的未來。
張萱琳念大學之初,覺得和念中學時沒有太多差別,除了不用穿校服和不用每天滿課之外。
張萱琳也和從前一樣,盡量當一名好學生,該學習的時候毫不含糊地學,該玩的時候略顯拘謹地玩,經常獨自泡在圖書館的自習室裏看書,平日又勉強稱得上合群。
大一的一二學期,張萱琳都是年級前三名,連沒人在意的毛概課的開卷考、全部人都随便應付的醫學史課的期末小論文,她都用心對待,争取拿了滿分。
同學們都認為她是鐵了心要當醫生的那類人。
只有張萱琳自己心裏知道,她對醫學沒有一點興趣和雄心壯志。
且張萱琳很倒黴,本科的醫學生要念五年,前四年在校學習,第五年到醫院實習。她念大學的前三年還好好的,第四年開始風聲不對了,到第五年實習期間,事情差不多成型了,等到快要畢業時,改革的通知下來了。
每個醫學生都必須參加三年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簡稱規培。
強制要求,沒有規培合格證書,不能在醫院裏工作。
張萱琳在S市的第二人民醫院實習了一年,也在醫院出了招聘公告時去應聘。
她那時的目标就是留在呼吸內科。內科的績效是絕對比不過外科的,亦即是說醫生能夠拿到手的獎金比較少,整個科室的醫生都比較窮。但張萱琳喜歡不那麽忙碌的工作,外科那種日夜颠倒連軸轉的工作強度,會将她艱難維系住的對當醫生一事的堅持打碎。
早在輪科時,張萱琳就和呼吸內科的主任陳康仁提前說了自己的想法,在應聘過程得到了陳康仁的一點幫助,離實習結束還有兩個來月的時候醫務科就敲定了張萱琳畢業後的工作問題。
Advertisement
因此規培的通知下來後,雙方都很被動。
醫務科的各位主任商量了好幾回,最終決定和張萱琳簽協議,承認張萱琳是醫院的員工,用醫院的名義送張萱琳去規培,而張萱琳在規培結束後必須回到醫院裏來工作,否則就要賠償醫院支付給她的基本工資。
張萱琳報名了市裏唯一的三甲醫院,即醫大附院的規培,并通過了附院設定的前期考試,獲得了規培名額,在附院開始了為期三年的規培。
張萱琳當初選擇不考研的原因,就是為了早點參加工作,早點掙錢,早點獨立。
可規培的規定一下來,她掙錢的道路上就多了三年的攔路虎,和讀研要花費的時間一樣。
拿着人民醫院每個月發給她的一千二百塊基本工資,張萱琳心都涼了。
且人民醫院給她發工資還發得不情不願,醫務科時不時就要聯系她詢問近況。
新規定剛開始實行,誰都沒有經驗,誰都慌,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實際問題要解決,就是不曉得哪天問題會爆出來,會爆在誰的面前。
張萱琳怕小醫院有了更好的人選而不要她,小醫院怕張萱琳在大醫院待得好了,毀了約,拍拍屁股走掉。
誰都不信誰。
張萱琳已經和醫務科的劉科長談心好幾次:她沒地方去,人家大醫院不要她這種本科生,只有人民醫院肯看在陳康仁主任的面子上勉強要了她。
劉科長也和張萱琳坦白:醫院無緣無故要付三年的工資給一個不在醫院工作的醫生,壓力也很大,請張萱琳一定要諒解他們的緊張。且張萱琳規培順利結束後,她就是第一批參加過規培的醫學生,指不定有什麽別的醫院要挖她過去,他們肯定是要确保多幾次張萱琳的意願。
至于附院那邊,從來沒有和張萱琳提過要在規培期間付給她任何的補助費用。
張萱琳也不可能去問。
附院是慌裏慌張地就作為規培定點出現了,估計也沒搞明白怎麽回事,更不會願意給注定要離開的一個醫學生掏錢。
社會需要醫生,需要高學歷的人才,可這樣的角色變得了不起之前的菜鳥時期怎麽活,大家能不能安然挺過培訓時期,似乎不在考慮範圍內。
張萱琳沒錢在外租房子,附院的宿舍又不向規培生開放,她只能在父母家住,每天坐差不多一個半小時的公交車去上班,差不多就是從起點站坐到終點站了。輪科輪到非常忙碌的科室,張萱琳可能幾天回不了家,因為抽不出近三個小時來回家與附院。
張萱琳的父親還在工作,母親到了退休年紀,因早年買斷工齡,故此時可以開始領退休金,暫時不需要她來養。每個月她拿到一千兩百塊的薪水之後,給家裏八百塊當夥食費,留四百塊自己用。
但她的父母偶爾也會感嘆一下:原來讀這個專業要花這麽多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她一天無法獨立養活自己,父母就要幫扶她一天,家裏的負擔就無法真正減輕。
這與一畢業就能夠出去正常找工作領薪水的別人家的孩子相比,她的父母難免要産生疑慮。
何況張萱琳家裏還有一個妹妹要念書,要花錢。
一旦要支出的錢超出負荷,就要往回去查是哪裏多花了錢。家裏最大的支出,是兩個女兒的學費和生活費。而盼望多年的大女兒學業有成後回饋家庭一事,卻暫時成了空,這是一目了然的。
張萱琳在這個事實面前,擡不起頭,壓力極大。
張萱琳沒辦法在父母面前抱怨醫學之路難走。
當初父母建議她讀醫,只是建議。傻乎乎地點頭答應的人是她。
且已經熬過了五年,還剩三年就要熬到頭了,她不可能現在才來抱怨,除了硬着頭皮繼續熬下去,她別無他法。
張萱琳也不是多麽熱愛醫學事業,更不是因為對治病救人有無上的信念才讀醫的,她只不過是聽從了家人的建議,而家人,只不過是對醫生一職有着強烈的誤解。
當時誰都沒有想過現在當醫生要經歷這麽多坎坷。
而後來一直在這一條道上走,也只不過是因為張萱琳不會幹別的事,沒有掙錢的腦袋。
她的家人和她很相像,都是不會掙錢的人。所以她的家境一般,無法給她提供任何經濟上的幫助,無法讓她去學點別的東西或是做點小生意。
在所讀的專業裏,在所擁有的一技之長裏,悶頭往前走,對上了賊船的張萱琳而言,是眼下最好的選擇,最不會讓前期支出的成本沉沒的選擇。
張萱琳斷斷續續地和向珩說了這些話。
關于她和向珩在見了第一面之後、見第二面之前,将近十年的時間裏,她的經歷如何。
向珩終于能夠明白張萱琳面對工作時為什麽總是那樣疲倦。
她的內心深處并不認同自己為醫學工作付出的一切。
向珩想起他和張萱琳在市圖書館的閱覽室裏度過的時光,張萱琳總是很專注,工作也好,學習也好,她盯着電腦屏幕或是書本看的眼神,偶爾會讓向珩羨慕,羨慕被她看的對象,也羨慕擁有這種專注眼神的她。
完全沉浸在某件事的表現,很多時候就意味着某種程度的沉迷。
他有點覺得張萱琳對自己的職業會有抗拒的想法,是因為她被過去的非自主選擇一事束縛住了,也是因為對過于艱難的道路和過長的戰線産生了幻滅感。
她以為自己是被動的、是被迫的。
向珩輕聲同張萱琳說:“其實對某種職業的興趣和熱愛,是在工作的過程中培養出來的。像我,一開始也不喜歡做咖啡,只是尋常地去打工而已。我是後來才慢慢愛上了做咖啡。或許你會在工作過程中,逐漸愛上醫生這一職業。成為一種職業裏的佼佼者,肯定極其困難,甚至成為專業性極強的職業裏的普通從業人員,也是極其困難的,這由職業本身決定,但是過了這個階段,事情就會慢慢變好,在這些職業中奮鬥的人們,也可以慢慢地感受職業的魅力。”
張萱琳只喃喃地說:“是嗎……”沒有正面回應向珩的話。
“現在你已經度過了培訓階段,可以正常在醫院工作了,也算是熬出頭了吧?”向珩問。
張萱琳卻搖搖頭,明确地反對道:“不算。在我能夠穩定給父母家用并且存到錢之前,以及在我從醫學之路上獲得歸屬感之前,都不算熬出頭。”
“歸屬感?”
“嗯,我希望可以真正感受到我是屬于那個地方、那個身份的。”
向珩問:“你覺得現在的你不屬于嗎?為什麽?就是因為你不曾主動選擇過嗎?其實加上實習和規培階段,你現在快要在醫院裏待五年了,這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再怎麽樣,也該産生一些感情的。”
張萱琳沉默了一會兒,說:“一是像剛才跟你說的,我并不喜歡。還有一點是,我不太理解作為醫生應該要有的面貌。我連它的樣子都看不透,都不了解,談何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