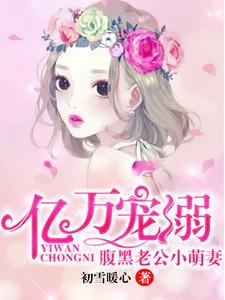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73章 《》第二部分(31)
《遙遠的救世主》第二部分(31)
門口只剩下丁元英和韓楚風兩人。韓楚風不解地問:“什麽招兒?”
丁元英說:“我謅的一首詞,不是招兒的招兒,随緣吧。”
這次守門僧人進去的時間比較長,好一會兒空着手回來了,手裏的信封已不見,這似乎是一個有希望的信息。果然,守門僧人走過來說:“兩位施主請随我來。”
守門僧人前面帶路領着二人進入寺院,穿過大佛殿時,見到大殿中央臺面上端坐一尊金身大佛,周圍是一些佛教法器,佛前燃着香火。出了大佛殿拐了幾道彎來到明心閣,屋內青磚鋪地,陳設簡單,木制桌椅呈現出古舊的色澤,臨門站着一位60多歲身穿灰色僧袍的老者,他個子不高,身材消瘦,下颌的胡須已經花白了。
守門僧人恭敬地介紹道:“這位就是智玄大師。”接着對智玄大師雙手合十躬身行禮低聲道:“弟子告退。”又對客人合十行禮,這才退下。
智玄大師說:“兩位施主,請坐下說話。”
明心閣的房子不是很大,四周牆壁上有一些佛教字畫,屋內正中擺着一張老式方桌和4把木椅,3人圍桌而坐,桌上放着丁元英的一首詞和壓在紙上的信封。智玄大師把信紙和信封輕輕往前推了一下,說:“敢問施主什麽是真經?修行不取真經又修什麽呢?”
韓楚風不知道這首詞的內容,就勢拿過看了一遍,上面寫道——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經。
一悲一喜一枯榮,
哪個前生注定?
袈裟本無清淨,
紅塵不染性空。
幽幽古剎千年鐘,
都是癡人說夢。
韓楚風馬上明白了智玄大師為什麽要提這樣的問題,所不同的是,大師心裏有解,而他心裏無解,他在心裏是真正的提問:什麽是真經?修行不取真經還修什麽?他覺得詞中諸如“休言”、“勿取”、“癡人說夢”之類的用詞過于激烈了,不太妥當。但此時他更關心的是丁元英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或者說他更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丁元英回答道:“大師考問晚輩自在情理之中,晚輩就鬥膽妄言了。所謂真經,就是能夠達到寂空涅碦的究竟法門,可悟不可修。修為成佛,在求。悟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覺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惡果者有信無證,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滅。不昧因果者無住而住,無欲無不欲,無戒無不戒,如是涅碦。”
智玄大師含笑而問:“不為成佛,那什麽是佛教呢?”
丁元英說:“佛乃覺性,非人,人人都有覺性不等于覺性就是人。人相可壞,覺性無生無滅,即覺即顯,即障即塵蔽,無障不顯,了障涅碦。覺行圓滿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圓滿即止,即非無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彌陀佛。佛法無量即覺行無量,無圓無不圓,無滿無不滿,亦無是名究竟圓滿。晚輩個人以為,佛教以次第而分,從精深處說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來不可思議,即非文化。從淺義處說是導人向善的教義,善惡本有人相、我相、衆生相,即是文化。從衆生處說是以貪制貪、以幻制幻的善巧,雖不滅敗壞下流,卻無礙撫慰靈魂的慈悲。”
智玄大師說:“以施主之文筆言辭斷不是佛門中人,施主參意不拘經文,自悟能達到這種境界已屬難能可貴。以貧僧看來,施主已經踩到得道的門檻了,離得道只差一步,進則淨土,退則凡塵,只是這一步難如登天。”
丁元英說:“承蒙大師開示,慚愧!慚愧!佛門講一個‘緣’字,我與佛的緣站到門檻就算緣盡了,不進不出,亦邪亦正。與基督而言我進不得窄門,與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幾等的貨色大師已從那首詞裏看得明白,裝了斯文,露了痞性,滿紙一個‘嗔’字。今天來到佛門淨地拜見大師,只為讨得一個心安。”
這時,一個小僧人走進來恭敬地對智玄大師合十行禮,說:“師父,都準備好了。”說完轉身退了出去。
智玄大師站起來說:“兩位施主,請到茗香閣一敘。”
丁元英和韓楚風跟着智玄大師出了明心閣,向左轉穿過一道長廊,來到一間題名為“茗香閣”的房舍。茗香閣比剛才的明心閣大得多,進門迎面就看見牆上挂着一副橫幅,上面寫着“清淨自在”四個潇灑飄逸的大字。橫幅下面整齊地擺放着筆墨紙硯和一個紫檀木制成的圍棋棋盤,棋盤上是兩盒棋子。房間北牆的位置是一塊由天然怪石當成的茶幾,石面上擺着蓋碗茶具、茶葉罐,茶幾四周是幾個樹根凳子,主座位旁邊是一個木炭爐子和一個裝水的木桶,爐子上架着銅壺,壺裏的水已經快開了,聽得見嗡嗡的響聲。
智玄大師伸手示意說:“兩位施主請坐。”待客人落座後智玄大師問道:“施主以錢敲門,若是貧僧收下了錢呢?”
韓楚風答道:“我們就走。如果是錢能買到的東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師豁然一笑,分別往蓋碗裏放入茶葉,提起冒着蒸氣的銅壺逐一将開水沖進3只蓋碗,蓋上碗蓋說:“這是寺裏自制的茶,水是山上的泉水,請兩位施主品嘗。”
丁元英揭開碗蓋,一股帶着山野氣息的清香撲鼻而來,只見碗中的茶湯呈淡綠色,碗底的茶葉根根形态秀美。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小口,禁不住地說了聲:“好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