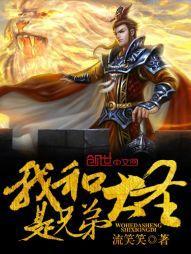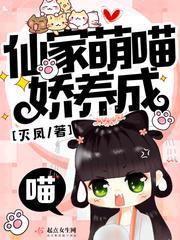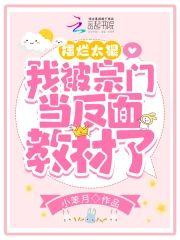第42章 章節
岳陽城郊文家老宅,臨近洞庭湖。漲潮季節,湖水已經淹到了文宅所在的小山坡的山腳下。迎接他們的家人說大水時湖水會淹到文宅的外牆,所以文宅的牆腳都特別用青石加固。雖有大水之患,風水師說此地風水極好,文運昌盛,分得老宅的長房兩兄弟文端與文方,都以文名入仕,分別官居禮部尚書與湖州知府;年輕一代的五個兄弟,也大都以國子監監生的身份得以入仕,前途正好。所以文家從未想過要遷居岳陽城中,只是不斷加固此處堤防與院牆。只是文儒海這一房的老少兩輩,除他之外,都有官職在身,不得回來,是以偌大宅院中只留下他與兩房看守家人。
文儒海不但設下盛宴,還請了幾位岳陽知名的文人作陪,并召了當地最有名的戲班來助興。
孟劍卿微笑着低聲向文儒海說道:“皇爺最嫌惡大小官員們喝酒聽戲,李先生又在喪期之中,這樣做是否不太妥當呢?”
文儒海笑道:“孟校尉不提醒,我還當真忘了這回事了。下不為例,下不為例。今天難得李兄遠道而來,就不要掃了大家的興了。來,來,孟校尉,你也點一出戲吧,這個班子很是不錯,到岳陽一趟,不看看他們的戲,便枉此一行了。”
孟劍卿既不能撕下面子,當此之際,也只能随着大家一起入席點戲了。
李克己看望過萬安與抱硯之後方才入席,與文儒海并肩而坐。
文儒海頻頻勸酒,到後來孟劍卿都看不過去了,攔住李克己舉杯的手道:“別喝醉了。”
文儒海一笑:“我知道李兄心裏難過,所以才勸他喝酒。一醉解千愁,醉了豈不更好?”
李克己只一怔,便大笑起來:“對,對,一醉解千愁!來,咱們大家一起喝個痛快!”
他一仰頭,又飲盡一杯,心中卻是百感茫茫。
他已永遠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算他此後能夠青雲直上,能夠揚名天下,沒有他們在一旁,又有何意味?他今後的路,要為了誰一步步走下去?
雷聲隆隆地滾過湖面,飲酒聽戲的人們不覺都轉過頭望望大廳外。
閃電撕開了黑沉沉的夜幕,不多時,暴雨傾瀉而下。
洞庭湖上風起濤湧,巨浪拍打着堤岸,小山坡之上的文宅也似乎在微微震顫,大廳中的人們身不由己都感到了腳下的抖動。隔了天井,對面小戲臺上正在上演全武行的長阪坡,鑼鼓喧天,與電閃雷鳴相呼應,令得庭院之中彌漫起一種奇異的氣氛,仿佛不是在岸上,而是在巨舟之中,與洞庭湖上的驚濤駭浪只有咫尺之隔。
李克己心神恍惚,過了一會才聽到文儒海在對自己說話。文儒海笑道:“李兄,上一回在京中你送我的幾幅畫,全都被錦衣衛衙門要去做辦案的證物了,看樣子是休想再要回來。今晚你該再為我畫一幅吧?”
孟劍卿微微一怔。文儒海是在說謊,還是的确有人瞞着他這個主辦案子的人沒收了那幾幅畫?什麽人有這個膽子?就幾幅畫而已,就值得來開罪他?
Advertisement
李克己不覺一笑,文儒海愛在盛宴之上索畫的習慣絲毫未改,令他仿佛又回到了洞庭湖一案案發之前與文儒海飲酒作畫的時候。
文儒海不待他回答,已命兩名家人在大廳當中清出一塊空地來,又在空地的邊緣放上一張長案,準備好筆墨紙硯。
洞庭湖上的風濤之聲與雷聲鼓聲相雜,文儒海忽地拍着桌面高唱起一首元人小令來:
“詩情放,劍氣豪,英雄不把窮通較。江中斬蛟,雲間射雕,席上揮毫。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孟劍卿打量着文儒海,心念忽地一動。
文儒海此刻的神氣,倒比李克己還要像鐵笛秋一些。
難怪得這兩個人會如此投契。
李克己的目光投向長案上的宣紙,略一停留,又轉向了大廳兩側雪白的牆壁。
長案上的紙張,不足以容納他此時心中的種種感觸。
他驀地抓起案上一盒滿滿的濃墨,一揚臂,淩空揮灑向右面的粉牆。
文儒海的眼中閃起了異樣的亮光,招手令家人趕緊再磨墨。
李克己抓起古玩架上的一幅繡絹蓋巾,揉成一團,以絹為筆,将粉牆上的墨跡鋪展開來,墨跡高處伸手難及,他縱身躍上房梁,以雙足勾住橫梁,倒挂下來将墨跡渲染開去。
繡絹所到之處,墨跡濃淡立分,或漫如雲煙,或重如濁浪。
此時另一盒墨也已磨好,李克己縱身躍下,扔了繡絹,抓起頭號狼毫,飽醮墨汁,揮灑勾勒之間,八百裏洞庭躍然牆上,水波蕩蕩,風急雲低,孤舟栖于湖心,宛如正被巨浪抛擲向半空;而最震撼人心的,還是那海吸百川的張拔氣勢與浪湧連天孤舟自靜的奇特意境。
最終他揮毫寫下“八百裏洞庭孤舟縱橫誰人識”一行字,擲筆案上,自橫梁上頹然落下,望着牆上的洞庭湖,不知不覺之間已淚流滿面。
孟劍卿驀然一驚,不由得像廳中衆人一樣,屏息靜氣地仰着牆上白浪滔天的洞庭湖。
他開始想到,也許真的有人會利令智昏、如此大膽地假公濟私拿走李克己從前送給文儒海的那幾幅畫。也許對那個人來說,那幾幅畫的确值得他去冒這個險。
【十一、】
李克己還沒有離開岳陽,旨意已經下來,著他回青城守喪,期間由地方官嚴加看管。至于喪期滿後如何,卻沒有下文了。
他再一次被挂了起來。
孟劍卿押解護送的任務已經完成,兼程回京複命。
沈光禮聽完他的彙報,淡然一笑:“我沒想到鐵笛秋居然會這般軟硬不吃,連李克己都丢下不管了。皇爺手頭要是略緊一緊,李克己就得去鳳陽服苦役了。”
孟劍卿躊躇了一下才道:“卑職覺得鐵先生的情形不太對頭。看他臨走時的身法,似乎并沒有人們傳說中那麽超凡入聖、驚世駭俗。我懷疑他拍李克己那一下,其實是在借力。他要丢開李克己獨自隐居起來,會不會也有這個緣故?”
沈光禮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除了李克己和老嚴,最後一個見到他的人就是你了。若情形當真如此,若他那些對頭們就此膽氣壯了找上門去,誰都不會認為老嚴會幹這麽沒品的事,只怕所有人都會将這筆帳記在你的頭上。”
孟劍卿擡起頭答道:“若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大人不妨看作是對卑職的又一次磨練。”
沈光禮笑而不語,轉而提起案上一紙公文遞給他。
原來是禮部派了一名國子監生去泉州祭祀媽祖,要求錦衣衛派人護送。
孟劍卿暗自詫異。朝中士大夫們,向來以為媽祖之神,不見于典籍,不可褒揚;開國以來,這還是朝廷第一次正式祭祀媽祖。
不過即便如此,似乎也用不着派他去吧?
但是他沒有問,沈光禮也沒有解釋,待他雙手奉還公文,慢慢說道:“你現在對鐵笛秋、李克己,哦,還有文儒海,有什麽看法?你以為他們是什麽樣的人?”
孟劍卿怔了一下才道:“他們都是與卑職不一樣的人。”
想到他們,尤其是李克己,孟劍卿的心中總會生出種種迷霧般的感觸。
沈光禮注視着他,等着他的解釋。
孟劍卿接着說道:“李克己的畫之所以會有一種撼動人心的力量,卑職以為與他跟随鐵笛秋修習了十餘年有着直接關系,十年磨一劍,他将他的精氣神都用到這上頭來了。卑職也仔細觀察過他的武功路數,覺得他與人過招時遠遠沒有他自己單獨練功時揮灑自如,并且有着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樂與愉悅。”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李克己卻将寒窗十年的文武兼修,鋪了一條這樣只求心中愉悅安寧的路。
就如那本應長成棟梁之材的一棵樹,卻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一朵自在開謝的花,真不知叫旁人說什麽好。
泛若不系之舟……
孟劍卿的心中忽地冒出這麽一句。
人生在世,本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他這個逆水行舟人,望着那一條不知要飄向何方的不系之舟,究竟是應該為它焦急,還是應該暗生羨慕?
沈光禮微笑道:“看來你現在已經懂得如何看人了。”
停一停,他又說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人來做的,都是為了人而做的。你懂得了人,也就懂得了事。”
孟劍卿霍然驚悟。
沈光禮從來沒有這樣教過他。他向來都是将他們這些人一把丢到狼窩裏,冷眼看他們自生自滅,再從中選出最能幹的幸存者去闖下一個狼窩。
沈光禮已經站起身:“給你三天時間準備。”
孟劍卿領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