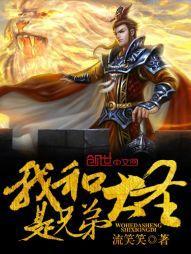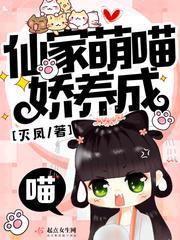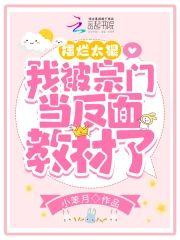第74章 章節
他的态度可想而知,自是毫不猶豫地追随李克己。
最後是明遠。他兼程趕往此地,為的就是插手此事,理由與玉衡大同小異,不過換了一個說法,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能浪費他們的能力與才華,以免暴殄天物有違天意。
孟劍卿不得不佩服這些人,能夠将“天意”二字解釋得面面俱到,誰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五對二,海上仙山的介入已成定局。
孟劍卿不知怎的,暗自松了一口氣;意識到這一點之後,不由得一怔。
難道自己也同樣希望海上仙山插手進來、好讓這場戰事快點結束?
【十一、】
既然決定介入,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介入;或者說,站在哪一邊?
首先表态的李克己,徑直說他對朱家叔侄誰輸誰贏都沒有意見,只要盡快打完就行。聯想到鐵笛秋當年對群雄争霸的鄙視态度,孟劍卿暗自感嘆,果然是一脈相承的師徒啊。
明遠則道:“李師侄若真地希望這場戰争盡快結束,就不可保持中立。眼前的局勢,各位都看得很清楚,南軍與燕師,各有長短,勢均力敵,若任何一方無出奇制勝之術,無意料之外的援兵,必成久戰。所以,李師侄,你最好還是好仔細考慮清楚,要選擇哪一方。”
李克己默然不答,很顯然是難以抉擇。
孟劍卿的心中大是震動。李克己似乎根本沒想到他還算是朝廷命官,如果要做出選擇,本應該毫不猶豫地站在建文帝的這一邊。
也許在他們這些人的心目中,所謂帝王,無非是遙遠故鄉的一幅畫面;即使是生長在蜀中的李克己,對寶座上的人,也沒有尋常士人那種發自內心的敬畏;在他們看來,這楓林之中,別無外人,是以他們平日裏的面紗都已揭下,袒露出心中那浩瀚恣肆的一片汪洋。
他們在孟劍卿面前展現的,是一個如此奇特的世界。
出乎孟劍卿意料,打破這一片沉寂的,是廉貞星君玉衡。
玉衡仍是那般慢條斯理地說道:“國家自有制度,燕王與今上孰優孰劣,無須反複權衡。但今日若讓燕王成功,他日必會出現無數個燕王。因人而壞制,日後沿以為習,只怕國無寧日。”
Advertisement
這是楓林中諸人都明白的道理。
明遠呵呵一笑:“洪武帝定下的這個制度,有無數漏洞,既擁有重兵又有靖難之權的藩王,就是其中最大的漏洞。有能力問鼎寶座的藩王,不可能抵擋得住那個位置的誘惑。既然這個制度本非善制,又何必抱殘守缺?”
玉衡道:“今上正在做的,不就是在彌補明師兄所說的這個最大的漏洞嗎?”
明遠反問:“寧師弟以為,今上有這個彌補漏洞的能力嗎?若今上真有這個從容削藩的能力,也不至于有靖難之役。”
原來玉衡姓寧。
孟劍卿已猜到他是誰。兵部左侍郎遇襲失蹤的三名下屬中,就有一名屬官姓寧名衡,字守廉。寧衡是紹興人,入仕已久,歷任六部,升遷雖慢,至今不過正六品,卻以熟知六部條律法令而聞名,各部堂官,雖然不會将獨來獨往、頗有清高之嫌的寧衡視為心腹,但是每有事關律令案例的疑難,總不忘問一問寧衡,是以寧衡之名,在六部之中,頗為傳頌。也正因為此,孟劍卿才會記住這麽一個人。
大隐隐于朝。寧衡倒真是會找地方藏。
也難怪得當日襲擊寧衡一行的亂兵不知所蹤。那根本就是寧衡玩的金蟬脫殼的障眼法。
寧衡道:“所以今上才需要我們助他一臂之力。”
明遠尚未駁斥寧衡的話,雷公輔已經不無鄙視地大笑起來:“需要我們助他一臂之力!真是笑話!洪武帝已經給了他天下至大的權柄,還會弄成今天這種局面;就算我們再借他一柄無堅不摧的寶刀,一個根本不知道怎麽用刀的黃毛小兒,拿着這柄刀又有什麽用處?”
雷公輔長年征戰海上,自然不大看得起建文帝這種深宮裏長大的君王,對鎮守邊塞能征善戰的燕王倒頗有幾分好感。
明遠頗感興趣地道:“這麽說雷師兄是要選燕王了?”
雷公輔卻道:“我看得起燕王,不等于要選他。老實說我手下的兒郎們寧可跟建文玩官兵抓賊的把戲,可不希望對手是燕王。”
楚碧天笑了起來:“雷師伯,看來小侄倒與你老人家所見略同。我不喜歡燕王,但是南洋華商同業公會的意思是,我們更需要的是燕王而非今上。”
立意要偃武修文的建文帝,與他那些書生氣甚重的肱股大臣們,只怕絕不會贊同組建一支規模空前的水師、遠航南洋與西洋那樣一個耗資巨大、收益難期、有窮兵黩武之嫌的宏偉計劃。
寧衡道:“今上不會做的事情,燕王不一定就會去做。”
明遠嗬嗬笑道:“道衍和尚對燕王的評價是,內多欲而外飾以仁義。道衍這賊和尚看人向來又準又狠,這句話可絕不是無中生有。各位想一想,這樣一位君主,對那個能讓他名利雙收的計劃,會不動心?更何況楚師侄一定不會空手去見燕王的吧?南洋華商同業公會今日投之以桃,燕王将來無論如何也會報之以李。”
孟劍卿即使沒有側過頭去看,也可以想象得到雲燕嬌此刻的神态與心情。
不管南軍與燕師的在北方的戰事何等激烈,雲燕然始終巋然不動地守在福建、專心訓練那支預定要揚帆南下的水師。
雲家是否也與楚碧天抱着同樣的心思,将希望寄托在滿懷雄心壯志的燕王身上?
明遠轉向另外兩人:“範師兄,石師侄,你們兩位的意見如何?”
範福長嘆:“我的産業,都在江南,明師弟你說我還能怎麽選?無論如何,至少在禮節上,我還是得對應天府的那位效忠。”
範福如此明确地表态,倒令大家都有些詫異;及至他說出後一句話,個中乾坤才顯露無遺,其中奧妙,大有推敲回旋的餘地。
石敢峰相形之下就痛快得多:“我不喜歡應天府裏的那一位。生于深宮,長于婦人之手,登基至今,一直被一幫酸腐文臣包圍,以為天下事都可以在紙面上解決,這樣的君主,能有什麽作為?所以我寧可選燕王。哪怕有朝一日成為對手,有這樣一個強大的對手,也足以高歌痛飲一番。”
他話中鋒芒,直指避強就弱的雷公輔。
雷公輔大笑:“石師侄你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哪裏像我這樣,要為手下幾萬兒郎讨生活?自然是不能有你這等痛快淋漓的決心了。李師侄,現在你的選擇可是至關重要了,你想好了沒有?”
寧衡道:“不但李師侄要想清楚,我看大家也都應該考慮清楚。在我看來,雖然還有不少漏洞,但是國家制度已經非常完備,一應事務皆有各級官員處理,只需要按部就班,不需要君王心血來潮、精力過人的非常之舉;所以,在上位者,循規蹈矩是最重要的。一個勇武善戰的君王,與一個文雅仁厚的君王,哪一個更合适?我想這自是不言而喻。”
明遠反唇相譏:“循規蹈矩?對六部來說,恐怕一個木偶擺在那個寶座上,才是你們最理想的選擇吧?”
寧衡答道:“明師兄有些誇大了。很多時候,六部還是需要在上位者來仲裁各種争議的。況且,六部官員若不能尊敬在上位者,庶民又怎麽會尊敬各級官吏?孔子言,冠雖敝而必戴于頂,履雖新而必着于足,其道理便在于此。”
明遠道:“寧師弟以為,建文比燕王更适合成為這樣一個足夠明智的仲裁者?建文‘仁’則‘仁’矣,只可惜流于婦人之仁,能賞不能罰,你确定你們需要這樣一個仲裁者?”
寧衡道:“建文固然有種種弱點,但燕王若是逆取而得寶座,誰又能保證他會遵守國家制度?”
明遠道:“玄武門之變,也并不妨礙太宗皇帝成為一代明君。或許正因為問心有愧,才會讓太宗皇帝面對朝臣和天下時,時時警惕,如履薄冰,務必要證明自己才是上天的真正選擇。”
寧衡道:“這只是明師兄的推測罷了。何況,就算太宗皇帝會如此想如此做,并不等于燕王将來也會如此想如此做。我不以為有必要冒這個風險。”
明遠與寧衡,針鋒相對,你來我往,一時間争執不下。
範福在一旁低聲提醒李克己快做選擇。他若做出選擇,明遠與寧衡,自然是争無可争。
李克己仍是躊躇不決,良久方才說道:“我無法在他們之中選擇任何一個。”
範福點頭附和:“那倒也是。各有短長,魚與熊掌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