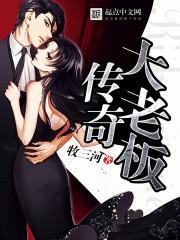第16章 七月流火(六)
六、
全村的田都插完秧之後,要賣稻谷的人家,趕緊騰出手來,挑了稻谷往八橋鎮去,大姑姑家裏也在套籮筐裝稻谷,顧岳低聲問李長庚為何大家不用牛車,大姑姑在一旁早聽見了,不覺失笑:“這鄉裏哪有牛車能走的路?也就是清江河邊上的路寬一點,容得了兩個人挑着擔子還能對面錯個身。要走大路,得到了縣城才有。”
顧岳有些臉紅。他又想當然了。
八橋鎮在李家橋下游,沿着蜿蜒的清江河走,得走二十裏;若不挑重擔,抄小路走,也就十裏不到。當地人将那鎮子叫“八橋鎮”,起初是因為這鎮子周圍,大大小小共有八座有名號的橋。現在當然不止八座橋了,不過這名字一路叫下來也沒改。
清早出發,從李家橋往清江河下游走不到一裏路,河邊就有一個磨房,夏季河水高漲,水磨正好用,不少人家趕着現在來碾米,顧韶韓家也在其中。
顧岳忍着沒有問,為什麽大姑姑家裏沒有來碾米,将稻谷碾成米後再挑到八橋鎮去賣,至少一次能夠多挑十幾斤吧?
不過李長庚不待他問,已經熱心地和他講,八橋鎮這幾天收的新谷,是要運到縣城和衡州城去賣,但是稻米遠路運送不便,容易髒污,為免被人嫌棄,所以八橋鎮這邊只收稻谷,到了衡州再碾出來賣;現在來碾米的,多是自家要吃,早稻粗硬,不如晚稻香糯賣得上價錢,但是易飽又耐饑,所以一般人家大多是留些早稻自家吃,晚稻往往是舍不得吃、要挑出去賣的;就算是顧韶韓家裏,也就逢年過節時吃幾回晚稻米。末了又補充道:“別的村子裏,除了農忙季,一般人家向來都是一半紅薯一半糙米搭着吃的。咱們村的田多,在外頭投軍當差的人也多,年年都有銀錢寄回來,所以不少人家都供得起家裏人吃白米飯。”
顧岳感慨地道:“難怪得說窮文富武,要是飯都吃不飽,哪有力氣習武?”
李長庚點頭稱是:“咱們村子習武的人多,有力氣種田當兵,賺得錢多,吃得飽飯,然後又更有力氣練武。”
顧岳:“這麽說來,還是得多謝當初教李家拳法的明山和尚?”
李長庚:“可不是?李家祠堂裏還供着明山和尚的神位來着,每年祭祖時都要祭明山和尚。咱們村子的後山上還有一個小廟,供的就是明山和尚。”
一路上李長庚說了不少關于明山和尚的傳說。據說明山和尚原本是前明時一個大官,滿人入關之後,這人不肯留辮子降清,幹脆剃了光頭出家做了和尚,不過因為原本是個大官,名氣挺大的,出了家也不得清淨,于是一路逃到這三縣交界之地的大明山,覺得這地界好安身,就住了下來――顧岳聽到這兒時不免在心裏嘀咕,大明山這地界群山綿延,道路艱險,行軍不易,三縣交界之地實際上往往是“三不管”之地,偏又氣候溫暖,土産豐富,便是被困在山裏一年半載的也不至于餓死,因此自古以來就沒斷過占山為王的強盜土匪,哪朝哪代也沒能奈何得了,頂多是鬧得厲害了剿個匪招個安,可惜的是,這塊風水寶地太過宜于盜匪安身,故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前腳收拾了一窩,後腳立刻又會生出一窩來,剿不勝剿,招不勝招,所以州縣平日裏往往睜只眼閉只眼的不肯多事去管,明山和尚選這麽個地方安身,眼光還真不錯。
李長庚又道,李家先祖也是清兵入關後逃難到大明山下的,靠着給當地人種地做工過活,為人十分淳樸厚道,入山砍柴時見這和尚孤單可憐,便常常給他送點米糧鹹菜之類的,如此送了三年,明山和尚覺得李家先祖是個誠心人,便傳了那套拳法下來。
顧岳看看李長庚,再看看前面悶頭挑擔走路的大姑父,覺得“李家先祖淳樸厚道”這個說法,應該是有點道理的,換了他是明山和尚,遇着李長庚這麽憨直熱心、送米送菜一送三年的農家子弟,說不定也會另眼相看。
等聽到李長庚說,明山和尚收拾了一窩不識趣來找他麻煩的土匪,因為出家人視錢財如糞土,便将匪窩裏的銀錢財物都送給了李家先祖,又指點李家先祖在如今李家橋這個地方買田起屋;顧岳心裏突地一跳,覺得有些不對頭啊?衡州商會那個蔡老板和他講古時,只說李家是世代居于大明山下,可沒說是和明山和尚差不多同時從外面逃過來的?是李姓人從一開始就有意讓人誤會他們比明山和尚早得多來到這大明山下?
還有,李家祠堂裏供着明山和尚的神位……
顧岳覺得自己似乎猜到了一些什麽。
此時日頭漸高,顧岳一行人遇見不少沿河村子裏挑了稻谷往八橋鎮去的,三五成群,倒也熱鬧。聽得李長庚在講明山和尚如何如何,立時有人興奮地插話附和。這些人雖然沒有李長庚的本事挑着重擔走路時也能長篇大論地說下來,不過你一言我一語,倒是将明山和尚的種種傳聞說得活靈活現,諸如能降南山猛虎能捉水中蛟龍、常常将大明山上的土匪強盜當成仆從使喚、擺了個八卦陣騙得進山的一支清兵繞暈在山裏也沒摸到廟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呼風喚雨還能看相算命……顧岳聽得簡直以為這是諸葛亮再世劉伯溫重生。
說的人一個個眉飛色舞,仿佛自己便是那得到奇遇的李家先祖,明山和尚的本事越大、傳聞越離奇,自己越是臉上有光。
顧岳聽到後來,倒不再在心裏嘲笑這些太過誇大其辭的傳聞了。
昆明城的街巷之中,他也時常會聽到當地的老人講古,将曾經世鎮雲南的沐王爺說得神乎其神,仿佛那就是自家祖先,一提起來便滿面紅光、口沫飛濺。
喜歡吹捧自己家鄉的傳奇人物,這也是人之常情吧。
二十裏路,又挑着重擔,即使同行人多,一路說說笑笑,也并不輕松,路上歇了數次,直到近午時,才望見清江河邊岳巒起伏的盡處那個人煙稠密的鎮子。清江河在此處拐了一個大彎,河道變得開闊,水流變緩變深,開始宜于行船,船只沿河而下,可以經過縣城,駛入湘江,直通衡州;加之此地背臨群山,一遇盜寇匪害便可退入山中躲避,因此随着附近村落的增加與擴大,此地慢慢便有了碼頭、貨棧、客棧、雜貨店、糧店米鋪和住家,漸成大鎮。
時當夏收過後,挑着稻谷或新米來賣的農人絡繹不絕,各有相熟的米鋪糧店,徑直挑了去排隊等候。各家店鋪早已商量過,挂出來的牌價并無二致,意料之中,遠遠不如三四月份,不如收割之前,自然也不如去年歉收時的價格。那些農人抱怨歸抱怨,稻米照舊還是得賣。
李家橋這邊的稻米,往年多是賣給鎮子東頭的張家米鋪,這家米鋪的老板雖然姓張,土生土長的八橋鎮人,不過他家老娘是從李家橋嫁過來的,姓李,自己娶的又是李家橋顧姓的媳婦,大兒子也就是将來的少東家娶的是李家橋何姓的媳婦。因着這份香火情,張老板做生意也算公道,李家橋挑出來的稻谷和新米,往往就直接送到張家米鋪裏了。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賣稻米的多,大姑父他們等了半個多時辰才輪到。
稻谷直接挑到店鋪後頭。店鋪後頭臨河的空地上,起了三個足有兩人多高的圓柱形谷倉,谷倉上部,緊挨着二樓走廊,開口只比欄杆矮個半尺。谷倉底部中空,用木柱架空了一尺多高,以便隔絕濕氣,臨河那面貼近倉底的地方,開了個尺許見方的孔,用抽板擋住,要裝船時,将木滑道靠緊方孔下端擺好,擋板向上抽起來,稻谷便可沿着滑道傾瀉入船艙裏,餘下的稻谷不多,自可裝在籮筐裏吊出來。
三個谷倉已經裝滿了一個,封好了等待裝船啓運。第二個谷倉裝了一半。稻谷挑上二樓,挨着谷倉擺好,張老板在一旁記帳,兩名夥計将量鬥插入籮筐中,裝滿了稻谷之後,搖一搖讓量鬥裏的稻谷更密實、裝得更多一些,眼見得賣稻谷的農人要嘀咕抱怨了,又用木板将量鬥上方堆出一個尖來的稻谷抹平,見堆出來的谷粒重又落入籮筐中,賣家心裏好受多了――這也是張老板厚道處,一量鬥就是平平實實一量鬥,沒有非要堆出個尖來。
輪到大姑父一行時,張老板将手插進八個籮筐裏稍稍翻了一翻,便笑呵呵地道:“李家橋的水土好,谷子算上等,水生老弟又是個厚道人,咱們向來信得過,不用量了,一擔一百六十斤,三擔一百五十斤,總共六百一十斤,倒進去就行了!”
話雖如此,大姑父還是謙讓了幾句,才提起籮筐向谷倉裏傾倒稻谷,有意放慢了速度,好讓張老板能夠看得清楚,這一整籮稻谷,都揀選得十分幹淨,谷粒幹燥飽滿,并無以次充好偷工減料之處。大姑父這麽一做,張老板臉上的笑紋顯然更深了。兩個夥計站在一旁歇息,也松了口氣。
因着不須量鬥,大姑父這四擔稻谷,很快賣完,張老板将錢一一數給大姑父,除了銀元、銅幣之外還搭了幾張軍票,大姑父和大姑姑都極不樂意,張老板苦着臉解釋道,軍票是省裏頭直接攤下來的,各家店鋪不敢不認,但是認得多了又要虧血本,因此八橋鎮的米鋪公議,今年收稻米,都要搭一成的軍票,各家都是如此,不獨他這一家。
顧岳在旁邊聽着,忽然問道:“攤派軍票,是要準備打大仗了嗎?”
其時地方不靖,中樞不振,各省督軍将軍等實力派劃地為王,為搜掘財源,自發錢票,號稱“軍票”,強行攤派,在本省內與銀元銅角雜用,卻不許用來繳納賦稅,民衆深受其害,苦無抵擋之法,往往有小本經營者因此而破産,顧岳的同學之中就有受害者,當日談及此事,同舍諸人,都義憤填膺,宣稱将來必要革除這等弊政。然而這“将來”一詞,就顧岳這半年多來的所見所聞,只怕還遙遠得很,令人沮喪之餘,心中又更為激憤。
湘省地當南北要沖,民國以來,無論北洋軍南下還是南軍北上,湘省都會成為主戰場,大大小小的戰事常有,有戰事便有征發,本省駐軍與外省路過的軍隊用自制的軍票輪番征夫征糧征各類軍需物資,大戰大征,小戰小征,因此湘省農夫缙紳及商人受害尤深。對于這些事情,顧岳以前只聽講教官講時事時提到過,尚無切身感受,但是回鄉途中見聞漸廣,這段日子裏又已親身體會到稼穑之艱難,因此大姑父和大姑姑面對軍票時的不甘與忿恨,不知不覺之中,已是感同身受,脫口便問出了自己心中的憂慮,擔心戰事規模越大,軍票發行越多,李家橋的親友們也受害越深。
張老板嘆氣:“上頭的事,咱們小老百姓哪裏知道?軍票攤下來了,八橋鎮又正好駐着一個營還沒走,咱們哪還敢多問什麽?”槍杆子底下,認也得認,不認也得認。
他看看大姑父,又一臉豔羨地道:“還是水生老弟你們那邊運氣好,李家橋在外頭從軍的多,做官的也多,上頭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歷來就是攤軍票也會少攤一份。”
大姑父擺着手道:“哪裏哪裏。”大姑姑快嘴快舌地接過來道:“就算少一份也少不到哪裏去。再說了,如今不管買啥賣啥,哪家店子不搭點兒軍票?”八橋鎮的通例是十搭一,一塊錢搭一角,還得是八橋鎮周邊幾個村子的人才讓這樣搭,不然就不是這個價錢了。大姑姑手裏捏着一把軍票,常常抱怨說用不出去,顧岳也聽過幾次抱怨。
張老板嘿嘿笑着轉過了話頭,不肯再接下去。
顧岳挑着空籮筐,跟着大姑父一家出了張家米鋪。
今日恰好逢集,又到了中午,四鄉八方來趕集的人流湧到了最高峰,大姑姑領着他們先到米鋪隔壁各吃了一碗米豆腐。這樣熱的天氣,趕集的從家裏帶飯是帶不成的,因此臨街人家裏賣吃食的不少,錢少的吃兩個煨紅薯也能填填肚子,手頭寬裕一點的就可以嘗點平日家中沒有的吃食,這糙米粉做的豆腐便是其一,熬出來的米豆腐切成半寸見方的小塊,煮熟了點上辣醬湯,再灑幾粒蔥花,滴兩滴芝麻油,算是難得的美味了,又能填飽肚子。大姑姑老早就和顧岳說過要讓他嘗嘗,瞧着顧岳被熱豆腐辣醬湯激得滿頭大汗,大姑姑很懷念地道:“品韓那時每次跟着家裏人來趕集都會到這家店子裏來吃一碗米豆腐。這日子還過得真快。”
很奇異的,這一次聽到大姑姑談起父親,顧岳心中的悲痛幾乎不可見了,只有着淡淡的溫暖與想念,仿佛父親只是尋常遠行而已。
街上人多擁擠,顧岳一行人費了不少勁才慢慢擠過人群,将大姑姑家裏要用的農具、細布、針線、火柴、煤油之類買齊,不過并沒有鹽。顧岳見別村不少農人都買了鹽回去,不免有些詫異地問起個中緣同,李長庚悄聲說道:“咱們村裏不用到外邊買鹽,都是臘月裏去廣東挑鹽的。”
鹽價太高,因此私鹽從來屢禁不絕。大鹽販常常家丁數百、販鹽數萬斤,勾連官紳,一言不和便刀兵相向;村間小民則多是私下販運,通常不過一二十斤而已。不過聽李長庚的口氣,一個村子都到廣東挑鹽吃,只怕也不在少數,難怪要悄聲解釋、不欲廣而告之。
李長庚又道:“聽學堂裏的先生說,西洋那邊的新式制鹽法,費用省,出鹽多,又很精白,鹹味十足,比咱們的土鹽好得多,可惜那個法子難得學會,制好的精鹽賣到中國來,價格也太貴,一般人家都是吃不起的。”言語之間,很是豔羨。
顧岳道:“我讀中學時,聽一位去過天津的先生說,天津有一家久大鹽業公司,老板姓範,能夠制出和西洋一樣好的精鹽,但是洋商和江淮鹽商都不許那家公司的精鹽出天津,英國人還出動了軍艦來攔截鹽船。先生說他離開天津好幾年了,不知道現在的情形怎麽樣,不過昆明是一直沒見過那家的精鹽賣過來的。我們這邊好像也沒見過。”
雜貨店裏的鹽,仍舊是當地常見的粗砂一樣的黃色土鹽。
李長庚忍不住惋惜地感嘆:“天津太遠了,要是離得近……”
顧岳在心裏默默地替他接了一句:就可以去那家公司挑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