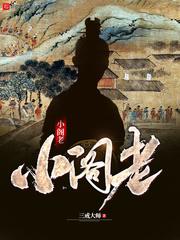第37章 章節
甚連貫,何況他禦劍咒修為尚淺,尚不能随心所欲,待見到石盤陀欲持刀行兇,只得出聲示警。又見石盤陀兇神惡煞般朝自己走來,心中一急,禦劍咒反倒頓時靈驗,将刀從石盤陀手中奪下。
兩人通過姓名,許觀才知玄奘法師正是涼州都督李大亮欲拿之人。玄奘因覺在東土所見佛經多不完備,便立志前往西方婆羅門國求取真經,石盤陀則是玄奘在瓜洲所收弟子,本許諾要護送玄奘經五烽而出唐境,不料卻在半途動了惡念。玄奘謝過許觀救命之恩,又知許觀也要前往莫賀延碛,問道:“小施主,你又是為何要去那裏?”許觀見他目光中滿含仁慈之意,不知怎的胸口一熱,便将如何在成都遇到小宴,如何同她來到長安,又如何失散等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說到小宴孤身去了險地,心裏一急,眼圈也紅了。玄奘聽罷,雙手合十禱道:“願佛祖保佑,施主終能和小宴姑娘相會。”許觀大是感動,說道:“也願法師早日到達婆羅門國取得真經。”
兩人在廟中過得一宿,次日向西進發。行了八十餘裏,見到第一座烽燧。玄奘道:“石盤陀曾道一路上惟五烽下有水,卻都駐有守軍,若有一處被覺,便會被捉拿處死。我們不如等到入夜再去烽下取水。”許觀稱是,玄奘便将馬放到一旁。二人與伏在沙溝中捱到天黑,才蹑足緩緩走近烽燧。待走到烽燧西角,果然見到一條溝渠,忙各自取出皮囊盛水。忽然一支響箭嗖的一聲射來,正中許觀的皮囊。烽上一棒鑼響,有人大喝:“什麽人敢來偷水,給我拿下了!”又沖出六七個軍士,皆是怪形惡相之輩,将兩人橫拖倒拽,捉上烽燧。玄奘與許觀被押到烽燧內一間囚室裏,見正中坐了一名軍官,生得又高又瘦,面頰凹陷,左眼下老大一搭朱砂記,瞧上去說不出的瘆人。
那軍官見了兩人,冷笑道:“朝廷三令五申,禁約百姓私自出蕃。你們好大膽子,當我這五烽都是空設嗎?來人!将這兩人拖出去打殺了。”玄奘嘆道:“阿彌陀佛。不想玄奘取滅于此,不能取得真經。只待來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舍諸惡業。”那軍官聽到“玄奘”二字,站起身來喝住衆軍士,問道:“你是哪裏的和尚,自稱玄奘?”玄奘道:“貧僧法名玄奘,自長安而來,前往西方婆羅門國求取真經。”那軍官滿臉驚異道:“我聽涼州人說有僧人玄奘欲前往西方取經,不想果真遇見。”又問了許觀來歷,更覺驚奇,對許觀道:“原來你不是去往西方諸國,而是要去莫賀延碛。那裏寸草不生,又無水源,你去豈不是白搭一條性命嗎?”見許觀與玄奘卻都是一臉堅毅,那軍官對玄奘道:“我是守這烽燧的校尉王祥,曾在家鄉敦煌聽報恩寺張皎法師說解佛法。你欲去西方取經,原是好事。只是西路艱險,此去婆羅門國何止萬裏,你如何能到?張皎法師曾對我說過三段故事,我終不明其意。天亮之前你若能解,我便放你們西去。若不能解,我亦不予你罪,你自去敦煌随張皎法師傳法,也不必喪身在西行路上。”
許觀聽罷,心中驚疑,暗道:“這賭賽太不公平。故事解開與否,都由這王校尉一人說了算。”玄奘卻點頭道:“校尉請講。”王祥道:“第一段故事據張皎法師所言,便是傳自婆羅門國。是說昔有一人有二百五十頭牛。一日此人放牛時見一頭牛被虎所食,便道:‘我這牛失了一頭,再不是全數了,還留它們作甚?’便将剩下的牛都趕到深坑中宰殺了。世上怎會有這等蠢人,這故事說的是什麽意思?”玄奘道:“如來有二百五十條戒律,倘破一條,當生慚愧心,作清淨忏悔,不再犯戒。若犯如來一戒,便道戒不具足,何用持為,索性一戒不持,便是因失一牛而殺群牛,如那故事中的愚人一般了。”
王祥聽罷,以手撫頭,恍然大悟,又道:“第二段故事是張皎法師遠行至西域某國所聞。說那國中有位美貌王後患了重病,終日昏睡不醒。國王便喚了醫者醫治,誰知那醫者開出一劑毒藥。國王大怒,欲斬醫者,那醫者卻道:‘王後之病,非此藥不可醫。’見王後奄奄一息,來日無多,國王無奈便讓王後服了那毒藥。誰知藥到病除,王後竟霍然而愈。王後蘇醒過來說道:‘我昏睡時夢到來到一地,人人都牛頭馬面,醜陋不堪,見到我卻都譏笑我生得難看。’這故事說的是什麽意思?”玄奘道:“恒河水,魚龍以為窟宅,天衆以為琉璃,人間以為波流,餓鬼以為猛焰。彼之毒藥,于此或為良藥。此之美貌,于彼或為醜陋。故外境之色,皆依其識,而所見不同。這便是故事本意。”
許觀幼時廣閱佛經,聽完玄奘所說,深覺飽含精義,只盼能再多聽幾句。王祥也若有所思,不住點頭,又道:“第三段故事,張皎法師講時哈哈大笑,我卻不明其意。”玄奘道:“檀越且說來聽聽。”王祥道:“說昔有一人叫作唐僧,有四名弟子叫作悟空、八戒、沙僧與白龍。悟空頭上有一道金箍,這日唐僧欲給八戒、沙僧與白龍都套上金箍。套到白龍時,白龍哭道:‘師父,莫套了。再套便是四個箍了,我是寶馬,莫叫我作奧迪了。’這故事又是何意?又有什麽好笑?”這次玄奘聽罷,盤膝低頭而坐,皺眉想了良久,卻仍沉吟不答。許觀看得心焦,湊上去問道:“法師,這故事莫非比前兩個都難解嗎?”玄奘道:“你不曉得。他那頭一個故事是《百喻經》中故事,殊不難解。第二個故事雖不見經典卻暗合佛理,也能解得。惟獨這第三個故事,百思不得其解。”
許觀滿心擔憂,忽然腦中一道靈光閃過,對玄奘道:“這故事既是張皎法師所講,他必知其義。我去尋他問個明白不就是了?”玄奘道:“敦煌離此地尚有兩百裏,此時已是四更,你如何能在天亮之前找到張皎法師?”許觀道:“只要王校尉肯放,我自有個趕路的法子。”玄奘道:“既如此,我與那王校尉說。”便對王祥道:“這第三個故事,貧僧一時也解不開。不過這位小施主要連夜趕到敦煌去問張皎法師,天亮之前定然趕回,還請校尉應允。若是他逾期不回,貧僧願任憑處置。”王祥道:“你好不糊塗,他若去敦煌如何能在天亮前趕回,分明要獨自逃走。”玄奘道:“我卻信他。”王祥笑道:“好!我便放他,也叫你輸個明白。”
許觀問明了路途不敢耽擱,離了烽燧将波月石揣在胸口,一路趕去敦煌不提。玄奘繼續苦思這第三個故事所含深意,不知不覺天邊已泛起魚肚白。王祥道:“他果然一去不返,你也該依我所說去敦煌傳法。”玄奘肅然道:“貧僧家在洛陽,少時慕道。兩京名僧,吳蜀大德,玄奘皆有拜谒。莫不窮其所解,倘若我只為養己修名,何必前往敦煌。然恨東土經有不周,才無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擅越若必欲拘留,任由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步。”說罷玄奘雙目一閉,再不發一言。王祥見他寶相莊嚴,這番話說得大義凜然,也暗自佩服。此時旁邊一名軍士上前報道:“那人已回來了。”王祥奇道:“居然回來了?快帶上來!”
只見許觀抱了個木匣風塵仆仆奔了進來,王祥道:“你是從敦煌回來嗎?”許觀道:“正是。不但到了敦煌還見到了張皎法師。”王祥怒道:“空口白話!何以為證?”許觀道:“我到了報恩寺,張皎法師正在大殿等我。他道:‘你不必多言,快将這木匣帶給王校尉。’我待要多說幾句,他卻揮手令我快走,又道:‘你同王校尉說:放了玄奘西去,日後方知我那故事為何好笑。’我見他不開口詢問,竟然盡知我來意,也不敢耽擱,連忙趕了回來。”王祥聽完,将信将疑,命人打開木匣,衆軍士往內一看竟都是一片歡呼。
原來那匣內放了滿滿一匣脆棗,上面擱了一張信箋。大漠苦寒之地,守軍都已數月不曾見過瓜果了,見了脆棗自然人人歡喜。王祥拾起一枚棗看了又嗅,喃喃道:“只有敦煌鳴山大棗才能生得如此飽滿……”又拿起信箋,見上面只寫了一個“放”字,心道:“這倒奇了,果然是張皎法師的筆跡。莫非真有神佛護佑這玄奘法師?若當真如此,我又怎能逆天而行?”王祥想到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