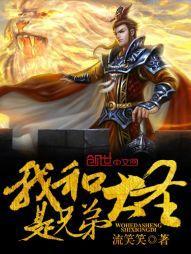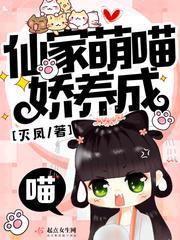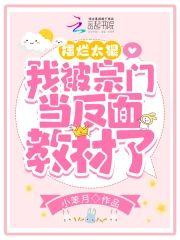第3章 (3)
誰派你們來的,還有何同夥?”
“天機!”那人揚起一張普普通通的臉孔,呵呵冷笑,“此乃……天機!”
他顫巍巍伸出血淋淋的手,遙遙指向法壇。
董罡鋒又驚又怒,雖知此人多半又在使詐,仍不禁側頭望去,卻見法壇上那盞最大的明燈不知為何竟已熄了。他悚然一驚,忽聽身後一聲呻吟,扭頭看時,見那刺客嘴角流出一線黑血,脖子已慢慢歪到了一旁。
“服毒?”董罡鋒大驚,忙伸手揪住那刺客的嘴巴,卻已晚了半步,那人眼神已經渙散,只那張滿是黑氣的臉上卻兀自浮着一抹詭異的笑意。
一場驚心動魄的激戰終于消停下來,遠方牆角處,那雙孤傲俊朗的眸子裏卻流出一抹憂傷。
“蛇隐,大膽魄,真豪傑!可惜啊,大哥,為何你不讓我與蛇隐一起動手?”
前方燈火閃耀,這人英挺的身形卻隐在最漆黑的角落裏,如墨色般難以察覺。
“葉橫秋,看看有何蹊跷!”朱瞻基這時才緩步踏上。
葉橫秋随即走上,俯下細查。“一葉知秋”這綽號既贊其掌法過人,更贊其精研諸般毒物,可見微知著,辨毒解毒之術獨步天下。
葉橫秋只掃了兩眼,便道:“見血封喉。這毒物塞入魚鳔中,藏于耳後,有細線與其牙齒相連,适才他咬過細線,吞毒自盡了。”
“掌教真人,你怎麽了?”蕭七忽見一塵掌教身子搖晃,急忙扶住他。
一塵的臉上已籠上了一層青氣,搖頭苦笑:“不大妙,小腿中了一枚毒針!”俯身連環兩指,封住了腿上穴道。
葉橫秋忙趕過來細查,小心翼翼地自武當掌教的左小腿上拔出了一枚毒針。閃耀的燈芒下,卻見那針色烏黑,一塵的小腿已淤青一片。
“劇毒,似乎是蛇毒……還好毒針只是擦肉掠過!”,葉橫秋說着,手腳麻利地剜肉、放毒、抹藥。一名白發蒼蒼的武當長老又自懷中掏出武當秘制的祛毒靈藥“天犀丸”,請一塵服下。
院中一片忙碌,董罡鋒卻始終似一只獵犬般緊緊護在朱瞻基身側,目光灼灼地掃視四方。
“殿下,”一股詭異的氣息若遠若近,董罡鋒老覺得心底生寒,忙道,“只怕還有奸賊混入了此間,殿下最好先暫避一時,以策萬全。”
朱瞻基神色變幻,沉了沉,忽然将手一擺,揚聲道:“都說真武大帝最能蕩魔除妖,福薄之人卻無緣得見,眼下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一發話,片刻前還亂糟糟的庭院間霎時肅靜起來,無數道士、侍衛全停止喧嚣,幹瞪着眼望向他。朱瞻基遙點着地上的死屍,叫道:“這便是神跡,便是真武大帝護佑我大明的實證!真武大帝佑我大明,法力無邊!”
聽他如此一說,不少人均是化憂為喜,向庭院當中法壇上高坐的真武神像叩頭喊道:“真武大帝佑我大明,法力無邊……”
朱瞻基又将手一擺:“來人,将此處收拾幹淨,速速再行北鬥燈儀,再祭真武!”
武當衆高道也均定下心神,金鐘、玉磬、铙铛、笙笛悠然奏起,幾名手腳麻利的小道趕來拼力清掃。
朱瞻基才吐了口氣,低聲對戴烨吩咐:“速請掌教真人回去安歇,葉橫秋同去醫護。将這屍身速速移到妥善處,細細查看,即刻查明他身份。”
戴烨點頭微笑:“殿下彈指間凝聚衆心,轉亂為安,老臣深覺欣慰。”
“老師言重了。”朱瞻基卻微微蹙眉,淡然道,“瞻基做事務求圓滿,眼下只不過順勢而為,說些該說的話而已。”
不知怎的,見到這位往昔弟子長眉一蹙間眼角閃過的鋒芒,戴烨不由心底一顫,忙躬身道:“老臣領命!”帶着葉家兄弟,收拾完屍身,匆匆出了庭院。
法壇前已收拾一新,明燈燦然舞動,道士們的詠唱聲中,朱瞻基面向法壇,再次跪倒。
七星燈儀是在父母殿前的大庭院中舉行的,高高的法壇上供奉着紫銅鎏金真武坐像。神像披發跣足,氣象雍容。
适才的驚險刺殺,此時朱瞻基還是心有餘悸。叩拜時他不由多看了幾眼神像,世間傳說,武當山的真武神像是依照皇爺永樂帝的容顏建造的,今日一見,果然有幾分神似。
起舞游動的明燈在銅像那修眉闊鼻間投下七彩斑斓的各色光影,真武大帝卻永遠是一副恒久不變的寧谧沉着之相,嘴角更隐隐挂着一絲淡淡的神秘笑意。
仿佛已洞悉了一切玄機,又似在苦笑芸芸衆生。
?
貳·金頂論道
七星燈儀雖被刺客一擾,弄得人心惶惶,好在太子朱瞻基遇亂不驚,使得祈福科儀如願完成。只是沒有想到,一塵掌教的毒傷竟這般重。
葉橫秋已使盡了手段,卻無顯效。武當山上歷來有“十道九醫”之說,精通醫術的高道不少,經兩位手段高明的長老道醫調治了兩日,一塵的毒傷竟也不見好轉。
這日清晨,病體未複的一塵起來後卻沐浴更衣,命蕭七背他上金頂參拜。
金頂,為武當山最高的天柱峰頂,號稱“去天咫尺”。
正是上午巳午之交,金頂上清風習習。蕭七背着師祖一塵,健步如飛地掠上了金頂。
蕭七的心中有些難過,師祖內功修為精深如海,但此時卻軟軟地伏在自己身上,渾如一個虛弱老人。更讓他內疚的是,若不是師祖橫身擋在自己身前,自己決計躲不過暴雨般的毒針,以自己的內功修為,挨上一兩針,只怕會當場喪命。
終于進了金頂當中的金殿,挾着一塵掌教在金殿邊一張木凳上坐定,蕭七便向他鄭重地叩下頭去。
“師祖,蕭七這條性命,是您給的。”
“你的日子還長,師祖是一把老骨頭了,沒幾日活頭。”一塵的目光永遠是那樣溫煦而悠然,他捶着腿道,“你趕來為師門排憂解難,師祖怎能讓你擋這冷箭。”
蕭七臉上一紅,不由垂下了頭去,心下自責更甚:我當真是為師門解難而來麽?或許,師尊罵得沒錯……“蕭七酸!”
殿外忽然傳來一聲嬌斥,一個身材高挑的少女疾步奔入,嗔道:“又是你,沒有照顧好掌教真人,竟累得老人家受了傷,是不是?”
這少女方當妙齡,眉目如仙,只是盈盈明眸中也隐含薄怒,十分清麗中卻更增了三分英氣。
“綠如!”蕭七眼前一亮,本來與少女極熟絡的,想打趣幾句,但聽她呵斥自己累得掌教受傷,不由沉沉一嘆,“是我不好。”
綠如深深盯了他一眼,不依不饒地道:“一句是你不好便萬事大吉了麽?掌教真人身子虛弱,你卻一大早便将真人背到了這裏來!”
“是老道讓他這般的。”一塵淡淡地一笑,“綠如,你趕回來便好,你那醫道師父癡道人怎麽說?”
綠如神色一暗,嘆道:“師父說,中了這等奇毒,若無解藥,目下也只得以毒攻毒。他連夜趕制了五煞粉,命我給您送來。現下他還要入山給您抓藥去,午後再過來……”
“連癡道人都束手無策,”一塵苦笑道,“看來天下能醫治我這毒傷的,也只有我那一粟師弟了。”
“滄海一粟?”蕭七心中現出一線曙光,忙道,“師祖,你知道他現在何處麽?弟子這就去尋他。”他早聽過這位師叔祖的名頭,此人是一塵掌教的師弟、武當三奇中年紀最輕之人,只是數年來雲游天下,蹤跡不明。
“癡道人已派了座下大弟子去尋他了。只可惜一粟是個閑雲野鶴,未必會尋得到。好在老道這一兩月間,是死不了的。”一塵灑然擺手道,“且不說這些了。稍時太子殿下要來,你二人且回避一下。”
蕭七心中一動:殿下要來這裏,他這兩日間常去探問掌教,怎的偏要在這裏見面?他卻不敢多問,向綠如招了招手。
綠如憤憤瞪了他一眼,還是跟他并肩出了金殿。轉到金殿後,蕭七悶悶地坐在地上。
據說,這裏是離天最近的地方,縱目望去,武當山七十二峰的幹岩萬壑盡在眼內,但蕭七心內卻紛亂如麻:果然,如師尊所說,真有刺客在武當山上對太子動手了,好在這人不是夕夕……顧星惜,那個神秘莫測的女魔頭,當真是她麽?
“喂,蕭七酸,”少女碧裳臨風,飄飄若仙,聲音卻清冷如冰,“你離山這麽久,他們說的……有個梨花院的女子。那個女的,叫什麽?”
蕭七的心突然一縮,只得黑着臉道:“小丫頭,這事跟你無關!”
“這麽說,都是真的了?”綠如沒有看他,只是漫無目的地遠眺群山。
蕭七咬咬牙,忽然仰頭大笑:“他們都笑話我是麽?都當我是個登徒子吧,而且是個蠢到極點的登徒子吧?他們要如何便如何吧,我蕭七自行其是,自作自受!”
綠如轉頭望向他,目光中竟頗多憐惜,輕聲道:“至少我沒有笑話你。”
觸見她目光中的柔軟,蕭七的心不知怎的就是一痛,低嘆道:“多謝你了丫頭……對了,掌教真人的毒傷,癡道人怎麽說?”
綠如搖搖頭,清麗脫俗的臉上滿是憂色,緩緩道:“很厲害,癡師父推斷,若是他竭盡所能,或許能延得三月壽命。”
“三個月!”蕭七訝然跳了起來,随即又頹然坐倒,胸中滿是酸痛。
朱瞻基在神機五行和幾位武當高道的陪伴下大步上了山。
從金頂上揚眉遠眺,朱瞻基不由慨然生出身在仙闕、俯瞰衆峰的冉冉仙意。他揮揮手,命董罡鋒等幾位親信守在金殿門口,便緩步踏入殿內。
“掌教真人!”見一塵笑吟吟地端坐殿內,朱瞻基不由一喜,“看來那毒傷已被祛了?”
一塵搖搖頭:“只怕很難,也不知還有幾月好活,老道思來想去,也只有本門秘傳的一門‘蟄龍睡’可控住氣血運行,或能延緩毒傷。”
朱瞻基心內一沉,凄然道:“刺客為瞻基而來,掌教實是為我受傷,瞻基心如刀割。”一塵忙道:“在武當山讓殿下受驚,貧道心底更是不忍,所幸殿下無恙,實為罔家之幸,那刺客……可查出什麽端倪了麽?”
朱瞻基嘆道:“戴老和葉家兄弟細細查過,看那刺客的戰靴和內甲樣式,竟是我趙王叔的府內護衛所穿……”
一塵冷笑道:“幹謀弑太子這等大逆之事,怎會明目張膽地穿上本府服飾?”
“掌教果然洞若觀火,這定是有人嫁禍于趙王叔,而罪魁禍首,已昭然若揭!”頓了頓,年輕的眸內閃過一絲冷冽,朱瞻基緩緩道,“便是我那獨一無二的好王叔,漢王千歲!”
大明王朝自開國皇帝朱元璋駕崩之後,接連兩代,都生出波瀾起伏的皇儲之争。
因朱元璋所立的太子朱标體弱多病,死在了朱元璋之前,朱元璋便立朱标的次子朱允炊為皇太孫。朱元璋死後,朱允炆即皇帝位,是為建文帝。
建文帝書生氣十足,登基之後,便全力削弱各大藩王的勢力。其中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一直坐鎮北平,為大明防範蒙古,手握重兵,精通兵法。眼見新皇帝削藩到了自己頭上,朱棣索性舉兵造反,指責建文帝身邊有奸臣橫行,要平定禍亂,史稱“靖難之役”。
叔叔王爺和侄子皇帝苦戰了三年,最終還是勇武多智的叔叔朱棣棋高一着,出奇兵奔襲南京,終于奪得大明江山。建文帝卻在一場大火中下落不明,自稱曾多次得到真武大帝護佑的朱棣則坐穩了大明江山,是為永樂大帝。
在這場苦戰中,朱棣的長子朱高熾只是奉命固守其老巢北平,居功至偉者是其二兒子朱高煦,曾數次浴血激戰,在險境中救下朱棣。
永樂大帝朱棣的晚年,竟面臨着和其父皇朱元璋一模一樣的困局:長子朱高熾早被立為太子,卻體弱身胖,不為朱棣所喜;與太子一母同胞的漢王朱高煦則在靖難之役中立下奇功無數,且形容英武,能征慣戰,頗有朱棣之風。于是,朱棣幾次動過念頭,要換漢王朱高煦為太子。
說起來,朱高熾最終坐穩了皇太子之位,還是緣于他的兒子、眼下的大明太子朱瞻基。
這朱瞻基自八歲起,便深受皇爺永樂帝朱棣的喜愛,十六歲時便被朱棣帶在身邊遠征漠北,并親自指示兵法。據說當年朱棣最後一次動起撤換皇太子念頭的時候,曾垂問近臣解缙,解缙只回答了三個字“好聖孫”,暗示皇太子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聰慧沉穩,是仁君之相。自此朱棣就永遠斷絕了換太子之念。
朱棣死後,朱高熾登基,是為洪熙帝。
世事輪回,當今局勢,竟已與當年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相似。洪熙帝朱高熾剛剛登基,政局不穩。野心勃勃的漢王朱高煦已苦心籌劃了多年,他在自己的封地樂安州廣蓄兵馬,磨刀霍霍,行止肆縱不法,多有僭越。相形之下,太子的另一個皇叔趙王朱高燧,早年雖也跟其二哥朱高煦一起驕橫跋扈,近幾年卻已收斂了許多。
這刺客出手時的算計陰毒高明,卻故意套上趙王府侍衛服飾,那便純是欲蓋彌彰、混淆人心的手段了。 “據葉橫秋推斷,看此人的暗器術和雙刀法,分明便是漢王府內三妖四士中的‘蛇隐’餘驚鴻。”朱瞻基的目光陰沉起來,“蛇隐獨擅一種陰損毒藥,名為‘萬蛇屍心’。很可惜,搜遍餘驚鴻全身,也沒有尋到‘萬蛇屍心’的解藥!”
“都是天命,生老病死皆有定數,也不必放在心上。”一塵淡然一笑,“貧道這便要施展蟄龍睡了,數月間便會知覺大減,飯食不思,混若癡人。故而在閉關之前,這緊要事須得與殿下禀報了。”
老道長莫測高深地一笑:“此次殿下親來武當,除了拜祭真武之外,更有一樁要事,便是那……玄武之秘吧?”
“掌教真人見識高妙。這玄武之秘,先皇爺臨終前的一日,在大帳中還跟我叨念過,而我父皇,更是念念不敢稍忘。”朱瞻基的話似乎說得極客套,但卻已點明此事竟是大明兩代皇帝最為關注之事。
“殿下這是孝心孝舉,貧道定要成全。”一塵的眼芒悠然一閃,“況且這玄武之秘,老道也早就想歸還朝廷。請殿下先參拜祖師爺吧!”相傳真武大帝在武當山得道飛升,武當山道士及附近山民都稱為“祖師爺”,十分恭敬中更有七分自豪。
朱瞻基點點頭,向金殿當中的神像跪倒。
金殿的光線有些幽暗。據傳這精銅黃金所鑄的神殿居然不進風、不滲雨,任由電閃雷擊,而殿內燈焰不閃。朱瞻基特意看了一眼殿內長明不滅的神燈,果然燭焰筆直,讓人一望而心定,凝神望了殿內戎裝肅容的真武神像片晌,太子鄭重萬分地叩下頭去。
禮拜已畢,一塵才道:“不朝金殿,猶如未到武當。太子今早急匆匆地禮登金頂,莫非已動了歸心?”
“掌教高見!這是個先兆,只怕下次,他們便要對父皇動手。”朱瞻基泛着血絲的眸內閃過一抹銳芒,再向真武像稽首行禮,“我已連夜給父皇寫了密奏,急命均州府乘八百裏加急快馬,急速趕往京師禀報此事……”
“太子行事,果然是霹靂手段。”一塵也向殿內的真武銅像恭敬施禮,才慢悠悠地道,“是時候了,在祖師爺跟前,老道才好交出那玄武之秘!”
真武神帝深邃如海的眼眸下,一塵自袖中鄭重取出一物,雙手穩穩送到朱瞻基身前。
那是個紫金葫蘆,在神燈下閃着黃澄澄的光芒。
太子接了過來,凝神細看。紫金葫蘆只一尺多高,上面密匝匝刻着太極圖、北鬥七星等道教符咒,雕飾精細絕倫,顯見是出自名家大匠之手。
“實則太宗爺在世時,這玄武之秘的堂奧已然失傳。”一塵道長意氣消沉地搖了搖頭,“老道這裏,也只有當年碧雲先師請人打造出的這玄武靈壺。當時碧雲先師曾說,天機難測,壺中玄妙,留給後人去悟吧……”
道教視葫蘆為道家法器,更尊稱之為“壺天”。而一塵道長所說的碧雲先師,則是武當張三豐祖師的嫡傳弟子,當年永樂大帝朱棣苦尋張三豐不見,便命武當名道孫碧雲全面籌劃設計武當山各大道觀。
玄機重重的玄武之秘,顯然與武當山有關,而身為武當山大修總督建的道長,孫碧雲則是最大的知情人。
朱瞻基深覺遺憾,又見這葫蘆最醒目的圓肚處雕刻着一幅醒目的圖案,旁邊圍繞着一段隸書的銘文。
“這圖是‘河出圖,洛出書’的《河圖》?旁邊的銘文卻是什麽?”
“正是!”一塵點頭道,“這段銘文是先師親做的《清淨銘》,要知修真悟道,總以清淨心為第一要訣,心不清淨,修道難成。”
“《清淨銘》……”朱瞻基凝目細看,不由在心中默念。
太上玄門諸極之道源出清淨
九霄初開妙道虛無萬化遵行
上士悟之仙閣同登永世太平
這三行銘文似是咒語,又似道家經文,語意頗為玄虛,朱瞻基看得似懂非懂。
“當年先師言道,要解開玄武之秘,須得湊齊兩樣寶物,所謂‘欲窺玄武,先明天樞’。除了這玄武靈壺,還有一面天樞寶鏡……”
“天樞寶鏡……”朱瞻基顯然是首次聽到這個名字,父皇只跟他提及了玄武靈壺,忙道,“那在哪裏?”
一塵搖了搖頭:“當年先師怕這兩樣寶物放在一處,易被居心叵測之輩盜走,便将天樞寶鏡交給了貧道的小師弟一粟真人。一粟師弟已離山雲游七八年了,他近年似是在太行山中的玄武閣做觀主。貧道可修書一封,讓他交出寶鏡。先師曾說,只有先将玄武靈壺和天樞寶鏡湊齊,才能初窺奧秘,但玄武之秘,深邃難言,我輩玄門中人,以清淨虛無為要,最好少刨根問底。”
朱瞻基心中疑雲四起,又舉起那玄武靈壺細看,見那隸書銘文字體圓潤,與凝重的圖案交相映襯,別有一股玄奧氣韻。
他不由嘆了口氣:“掌教真人,能跟我細說麽,到底何謂玄武之秘?”
一塵微一沉吟,才道:“殿下可知道太宗爺為何要召集三十萬民力,耗時十四年,大修武當山的宮觀?”
“此事天下皆知,靖難之役時,真武大帝多次顯聖護佑,力助皇爺轉危為安。為感激真武大帝的護國之恩,這才下令将真武大帝修真成聖的道場武當山大修。”
“只是這番大修自古未有啊,太宗爺還曾多次親下聖旨,不得擅動武當山的一草一木……”
朱瞻基一凜,只覺一塵的話頗為含蓄,他自然知道在南修武當的同時,永樂朝還在大修北京皇城,為遷都做準備,這一南一北兩大工程加在一起,幾乎已趕上了秦長城和隋運河的規模。他清楚地記得,光是這天柱峰銅殿中沉重而精致的真武銅像,便要在南京鑄好,再走水路輾轉運到武當,那該是何等的艱難!
這其中必然有個極大的玄機,那到底是為了什麽?
一塵道:“玄武,本是北方之神,北方屬水,玄武又是水神。至宋朝時,為避聖祖趙玄朗名諱,改稱‘真武’。因真武是戰神,歷代帝王均尊崇真武,本朝洪武太祖爺,更親封神號為‘真武蕩魔天尊’。道教的戰神甚多,如二郎真君、王靈官等都是廣為人知的護教戰神,但能威力廣披、護佑國運者,只有真武大帝。”
“護佑國運!”朱瞻基聽得這四字,眉頭陡然蹙緊。
“有宋一朝,外患不斷,遼國、西夏等均來自北方,急需戰神護國,故天禧二年四月,宋真宗下诏,在皇城內建祥源觀,專門祭祀真武。仁宗時狄青為一代名将,曾戴銅面具,出入陣中所向披靡,被時人視為真武神化身,其銅面具上即刻有真武神。其後元朝自北方入據中原,更視北方玄武為王朝之神,元朝皇帝便将真武的神號由‘真君’升為‘帝’,加為‘元聖仁威元天上帝’。至本朝洪武爺起,真武蕩魔天尊更是屢次顯聖,只怕殿下都是耳熟能詳吧?”
“不錯!”朱瞻基的眼睛亮了起來,“在永樂皇爺那時,無論是靖難之役還是老人家親征漠北,真武神都曾屢次顯靈。最初起兵靖難時,便狂風怒雲,咫尺不見人,皇爺正披發仗劍,猶如神帝降臨。此後的夾河之戰、拒馬河之戰、藁城之戰等,皇爺每到身臨危境時,均有風沙大起,真武顯威而轉危為安。”
說起祖宗天佑神護的功績,朱瞻基頗有幾分自得,侃侃道:“洪武太祖爺也是這般,當年鄱陽湖大戰陳友諒,太祖爺剛定下火攻妙計,立時風雲突變,一場好風助力,奠定不世之功。據說此戰之後,洪武爺對玄武神頗為虔誠,這時我才明白緣由,原來玄武既是戰神,也是水神啊,這一戰,玄武大帝護佑最力!”
“這就是了,真武大帝神威大顯,在本朝最為靈驗。殿下可否想過,為何在金宋元時,真武大帝也曾顯聖護國,但所顯示的威力卻沒有本朝太祖、太宗年間這樣盛大?”
銅殿內忽然悄寂下來。
沉了沉,一塵才徐徐道:“據說,這與三豐祖師、周颠、道衍等幾位高道有關。他們都是武當玄武道派的傳人,潛修多年,已悟出了獲得玄武護佑的秘法。周颠在太祖爺身邊,道衍在太宗皇帝身邊,秘布道法,獲玄武之力,果然效驗如神。所謂玄武之力,其實是天地間一股絕大的神秘力量,我輩凡夫俗子若獲得了玄武之力,施運此力,便可佑城護國,也可以……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
朱瞻基的心驟然一個哆嗦,皇爺朱棣不就是如此麽?以王爺身份起兵對抗當時的大明建文皇帝,名為靖難,實則就是扯旗造反。如果上溯千年,歷朝歷代還從沒有一個王爺造反成功過,無論是漢代的八王之亂,還是大唐時越王李貞起兵反叛武則天,都是敗得一塌糊塗,但偏偏自己的皇爺朱棣成功了,建文朝變成了永樂朝。
朱瞻基沉吟道:“大修武當山,難道竟是為了獲取玄武之力——這才是玄武之秘的真義?”
一塵沉着地點頭:“太宗皇帝身登大寶之後,籌謀十年,聚足國力之後,才大修武當山,只因他深知,獲取玄武之力的關鍵,便在這武當山上。可惜,最終的結局,雖然在世間多了一座祭祀玄武的仙山勝景,但太宗皇帝顯然沒有完成獲取玄武之力的宏願!”
“可惜啊。”朱瞻基自幼便被永樂帝帶在身邊,對這位皇爺情深意重,想到他壯志未酬,也不由郁郁嘆了口氣,“那武當山七十二峰,九宮十八觀數千間殿宇,這玄武之秘,到底與何處最為相關呢?”
“慚愧,老道先前已說了,玄武之秘,實則在太宗皇帝在位時已然失傳。除了這玄武靈壺和天樞寶鏡,先師也并未留下其他只言片語。或許,玄機就在這葫蘆之中。”
朱瞻基低頭把玩那紫金葫蘆,果覺這葫蘆奇妙異常。
一塵嘆道:“這葫蘆底處有一細孔,似乎此壺可以開啓,但老道推敲多年,也不得其解,只知道此壺由機關術名家費時三年打造,內含巧妙機關,若是強行拆解,便會觸發機關,只怕會毀去葫蘆內的密要。”
朱瞻基只得一笑:“掌教真人參悟不透的事,天下能悟出之人只怕寥若晨星了。好在我是奉父皇之命行事,只需将此寶物交還他老人家即可。”
将玄武靈壺鄭重收入懷中,朱瞻基心內大事已了,心神才輕松了些。
一塵拱手道:“殿下今晨遠路登山,勞頓至今,請先至皇經堂飲茶。”跟着喚了蕭七過來,背他同去皇經堂。
皇經堂的位置在金殿之下不遠,地勢卻開闊了許多。一株桂樹舒展出蓬勃的枝葉,撐出一片清陰。
後殿的小院內,紅泥小火爐上,只架着古拙的青玉石壺,壺中的水是自五龍宮下的龍池汲來的。相傳五龍宮下的清泉,有五位龍王護法,其水清澈甘甜。
烹茶的是一位須眉皆白的老道士,看形貌竟似有八九十歲了。一縷琴音則自殿內的屏風後袅袅傳出,中正平和,浸着震懾人心的清定自然。
紅泥爐,青玉壺,琴聲疏曠,茶香缥缈。庭間數叢翠竹随風搖曳,奏出飒飒竹韻。朱瞻基只覺一顆心瞬間寧谧下來,凝神看時,彈琴的人給淡紫色的屏風遮住了,只能看到一身纖細的綠衣,似乎是個女子。
“多謝!”朱瞻基籲了口濁氣,忽然間覺得全身皆松,緩緩坐在了院間的桂花樹下。他已明白一塵掌教的苦心,過得今日,一塵将要閉關抗毒,自己則要進行一場千裏奔波,眼前這一刻,是難得的清閑時光。
轉眼間,兩杯清茶便被老道士點入茶盞中。一塵親自将一盞茶遞到朱瞻基身前。武當山常受先帝禦賜諸般珍品,其中自有珍稀茶具,但一塵遞過來的,只是普普通通的青玉盞。
茶香随着袅袅白氣飄出玉盞,在竹林間游蕩,朱瞻基的心神也是一曠,輕啜了一口,登覺醇厚醒腦:“茶味清甘,別有一番滋味,真是茶道妙手!”
“其實天下茶道,最終只有一個勢……”武當掌教笑吟吟地飲了茶,才穩穩放平茶盞,悠悠道,“放下!”
“放下?瞻基受教了。不過這‘放下’,似乎更近于禪宗之說吧?”
“何必拘泥于禪宗、道家的分別,武當有太極之道,而太極之道的第一步,也是放下。”
朱瞻基不由來了興致:“記得頭一日到武當時與掌教閑談,曾聽真人說起,太極之道乃是大明天下的至道,不知此話何解?”
“殿下還記得那晚刺客行刺時,蕭七所使的招數吧?那刺客揮刀全力直擊,勢不可擋。世人對應此招,多是全力阻攔,或是拼力對攻。但蕭七所使的太極劍法卻既不直攔,也不反擊,而是在斜處裏給他一個勁,将其力道引入,再化開,讓敵勢落入我勢內。太極之道,先是放下了直争勝負之念,以退為進,引進落空,最終則是連争鬥之心都盡數放下,方能回歸太極。”
蕭七聽到這裏,心中一顫:放下勝負之念,我那時雖僥幸占了上風,但離着放下勝負之念,還差得遠。至于放下争鬥之心,那更是遠之又遠了。
朱瞻基雙眸一亮,忍不住道:“太極之道雖是武學,卻也是處世之道!”
“天下之法,多是強迫外人,屈從自己的意念,唯有太極武學,是舍己從人。當人打你一拳,尋常武夫都是全力反擊,把勁道扛出去。但在武當太極看來,這一念已經落在了下乘。簡單的反擊,那就是跟着對手走,為太極之道的大忌,一順勢而化,方合大道。”
一塵指着石桌當中那古樸圓潤的太極圖,道:“便如這太極圖,用陰陽相抱的圓環,喻示無限循環轉化之理。故而,萬事皆在轉化,遇事要借勢化之,何須用強!世人皆知太極武學為武當獨門奇功,卻不知太極武學最神妙之處,還是藏于這套拳劍之後的太極之道,以柔克剛,得天下勢。”
朱瞻基悚然有悟,道:“我這人行事剛強,必求圓滿,掌教是讓我柔弱勝剛強,行事不可求急求全?”
一塵低嘆:“太子銳意英發,天下罕見,只是……萬事求急求全,未免欲速不達。”
朱瞻基嘆道:“掌教之言真是直指人心之語,瞻基必銘記在心。”
“殿下身系天下衆望,有真武大帝護佑,老道哪裏談得上指點二字。”
朱瞻基連連點頭。他心結一去,不免歸心似箭,望了眼蕭七,忽道:“掌教真人,這位蕭七小道長,英武機敏,我想向你讨來,随我一同進京,掌教可舍得割愛麽?”
望着掌教問詢的目光,蕭七穩穩跪倒,道:“掌教真人,弟子願效犬馬之勞。”他知道,此時武當宗門的形勢不同以往,而且這是個求之不得的機會,只有随着太子,自己才能徹查出顧星惜到底是不是夕夕。
一塵點了點頭,又嘆口氣:“殿下來自京師,應該知道抑武策吧?”朱瞻基眼芒一閃,不知為何武當掌教忽然提起此事,只得道:“抑武策由父皇親自耳提面命,瞻基只知其大概。”
“抑武策是陛下親下的旨意,”一塵有些無奈地一嘆,“對武當雖然網開一面,但本門得了風聲後,卻不得不嚴加操行,三個月前,門內數十名精幹高手已盡被遣散。目下留在本山上的修道者多,習武者少。武功精強者,則只有幾位長老了,可他們均是年歲已高。少壯中的佼佼者,只有兩人,蕭七便是其中之一,他外松內緊,倒是能堪大任的。”
朱瞻基一怔,沒想到父皇大力推行的抑武策竟會讓自己束手束腳,如果武當那些高手哪怕只剩下一半在山上,又豈會容一個小小的蛇隐如此張狂?他只得嘆了口氣,道:“好在路上有大軍随護,蕭七和神機五行只是以備不虞而已。”
蕭七見一塵向自己點頭,知道掌教這算是答允了,忙叩下頭去。
一塵揚眉道:“你的武功還須修煉,便再指點你一句吧——無形無象,全身透空,應物自然,西山懸罄。”
蕭七一愣,沉吟道:“西山懸罄,是說要随對手拳勁而應,如擊罄出聲,而全身透空,則是随響而應的根基……只是‘無形無象’這四字,有些玄妙過頭,弟子眼下還參悟不透……”
“參悟多少,就看你的造化了!”一塵的老眼中射出一道精芒,“記住,練功時還要留意你的脊椎,你的兩腎,就是太極圖陰陽魚的魚眼。”
蕭七一震,霎時如嚼枇杷,心中回味無窮,緩緩退到一旁,凝眉沉思。
一塵又道:“綠如,你也随太子進京,這一路,要力保殿下無恙。”
屏風後的琴聲忽止。翠裳少女抱琴而出,眸中滿是疑惑。
朱瞻基望見綠如,霎時一愣,眼前的少女清麗如畫,雪腮上凝着淡淡輕紅,配上一身淡綠衫裙,恍若初春時節剛發的第一抹綠枝。他雖閱人無數,此時也覺眼前一亮,暗道:原來彈琴的便是她,真是罕見的佳人。他當下微笑道:“掌教,莫非這位姑娘除了彈琴,還是位武學高手?”
一塵道:“她便是我說的那兩人中的另一人。高手談不上,但她的劍法也還可入眼,更因她是個女子,不會引入注目。路上若有差池,或許能當大用。”
朱瞻基與一塵相處數日,知道武當掌教口中若能說出“能當大用”四字,必有驚人技業,點頭道:“如此,倒多謝掌教真人的美意了。”凝目在少女的臉上一轉,“你叫綠如,适才這首琴曲真能讓人清心靜慮,不知是何名字?”
綠如沒有言語,直視太子的目光清冷而執拗,忽然一抿嘴,略一躬身,抱起琴來,轉身便行。
蕭七見朱瞻基愣愣地僵在那裏,忙踏上一步,笑道:“殿下見諒,我這位綠如小師姑,自幼失聰,口不能言,故而麽.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請殿下恕罪則個。”
朱瞻基登時心下一沉:如此美女,竟是個啞巴,真是天妒紅顏!正自暗叫可惜,忽見綠如怒視着蕭七,嗔道:“蕭七酸,你才是啞巴,你才是聾子!你這又聾又啞的蕭七酸!”
太子和掌教一愣,随即齊聲大笑。一塵道:“殿下莫怪,綠如自幼孤苦,被武當山的坤道收養,五六歲時跑到老道身邊,纏着要跟我學武,老道便随手指點她幾下子,一晃,便這麽大啦。只是山野女子,不通禮數。”
朱瞻基聽得綠如适才輕嗔薄怒,語聲嬌脆,心內憾意頓去,笑道:“這才叫清泉出山,自然天真,我哪會怪罪。只不過這一路長途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