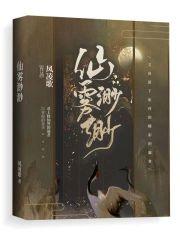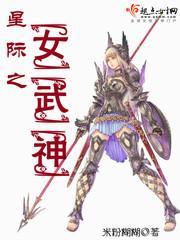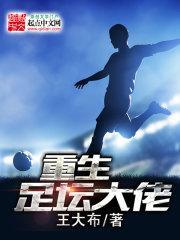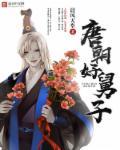第2章 ☆、章
那時,劉家還是鎮上少有的富裕之家,住在鎮西的一條小主幹道上,離中心地帶很近卻不至于因此失去寧靜的生活。過往的人不多,但閑來站在門口曬太陽的時候也常能見到幾個熟人,拉上幾句家常。這才是真正的劉家大宅。
已不知是哪一位祖先買下這塊地,從此開始世世代代的傳承。這宅子的年紀大概和小鎮的歷史差不多長了吧,帶着歲月痕跡的大木門上挂着一塊“劉氏大宅”的匾額,匾上的幾個鎏金大字由于每天清早都有人擦拭,依舊閃閃發亮。
大戶人家總是喜歡人丁興旺,劉家也不例外。對如今的劉家而言,要一手掌控原先數百人操持的家業,家族的人口需求自然更大了。為了避免內外親疏造成家族矛盾,先代早已制定的《劉氏家訓》中言:劉氏分本家、分家,本家系正宗,每代由族人從本家的嫡系子孫中舉薦一人管理全族,終守本家;分家不得居于本家之宅,不得忤逆本家之命,世代效力本家;凡劉氏之後,必遵此令,否則逐出家門,除劉氏族譜,奪劉姓,不入劉氏祖墳。
就這樣,随着代代傳承,分家不斷地向外遷移,與本家的關系漸漸疏遠,只有每年的祭祀,各分家才會派出代表回來一趟。有些分家中的劉氏血緣其實已經占得極少,在外多年不露面,便斷了聯系。時間一長,即使是本家也弄不清真正的劉氏分家究竟有多少個、現居何處,所以劉氏族譜上出現了許多斷肢,僅本家一脈尚且完整。
一直以來,劉氏憑借祖輩留下的豐厚家産從不為生活所愁,盡管随着時代的變遷和鼎盛時期的過境,劉家表面上漸漸失去了幾代之前的繁榮,但細水長流,由臺前轉到幕後。外人只知道昔日的劉氏能夠翻雲覆雨,孰料即使是今天的劉家較以前也毫不遜色,不過愈發低調,如同鋒芒畢露的少年轉變為沉穩的成年人。等傳到劉二爺——即劉叔——的手中時,劉家燒毀了所有仆人的賣身契,僅留下幾個自由之身的忠厚老實人幫着做些打掃、采購等雜活。靠着少數近親、世交、世代忠于劉家的仆從全家和離鄉後散至各地的劉氏後人,劉家的産業經營得井井有條。數代人積累的豐富的管理經驗,再加上劉家人自小耳濡目染,使得他們無需過多的外界力量便可輕松掌管全部家業。而這,卻恰恰是外人以為劉家已經衰落的信號。
這一年,劉氏本家的幺兒家毅滿十八歲了。他在鎮上的中學念書,頭腦相當聰穎,成績數一數二,再加上他素日彬彬有禮,很受鄉人喜愛。在家毅之上,劉家還有大姐家娣、大哥家偉、二哥家耀以及二姐家玲,都在初中乃至小學一畢業就回家幫忙了。而現在家毅卻仍然留在學堂讀高中,絲毫沒有接手家中生意的動向,鄉裏人都以為是劉二爺有意培養他哩。
其實,這不過是外人的猜測罷了。家毅年齡最小,從小深受父母、哥哥姐姐的寵愛是不假,可管理生意畢竟不是一件易事,需從基礎開始慢慢累積經驗。而家毅對這些完全沒興趣,向來不管不問,即使書讀得好也不意味着就能管好家業。近幾年家毅的哥哥姐姐們逐漸挑起大梁,劉二爺肩頭輕松了不少,生意上并不緊缺人。除卻劉家最初積累財富的階段,劉氏的歷任家主向來重視後代的文化水平,何況劉二爺也是個開明的,既然家裏負擔得了,小兒子又喜歡讀書,便由着他去了。
每天清晨,劉家依照祖上流傳下來的規矩全家人一起吃早餐,且年青人必須向長輩問安。不過延續了那麽多年的傳統也只是例行公事,不需真的還像百年前似的畢恭畢敬地低頭彎腰道:“父親/母親,兒給您請安了!”頂多就是見到劉二爺或劉二嬸的時候道聲“父親/母親”便夠了。
**********************************************
“我去學校了。”吃過早飯,家毅斜挎着一個藏青色布包邊出門邊說。
父親和大哥與一個大清早就過來的中年男子在書房商談,母親在廚房忙活,大姐、二哥手邊都擺着一疊書,大概是在尋找什麽資料,二姐則早已有事出門。大姐聽到家毅的聲音,擡頭笑着說聲“路上小心”,然後又埋入書中。
家毅騎上自行車——是父母提前送的十八歲生日禮物,心情頗佳地前往學校。其實,看見父親、哥哥、姐姐們整日為了家族生意忙得腳不沾地,他心裏也有所愧疚:只有他還在念書,完全幫不上家裏的忙。可是他真的對家族産業提不起興趣,書本為他開啓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令他沉浸其中,欲罷不能。而且父親不曾責怪他,哥哥姐姐一力包攬了瑣碎的事,讓他安心上學。家毅深知自己是多麽幸運,學習上很刻苦,成績優異。他的同學并不是不聰明,但家裏不及劉家,放學後還需在家裏幹活或者出去打零工,無法像家毅那樣一門心思地只想着學習,也沒有足夠的時間溫習功課,在校的表現自然差了些。家毅明白他們的難處,雖然生活上不好直接給予幫助,但在學習方面他還是很樂于幫助解答他們沒弄懂的地方。
“毅,早!”
一路上,不時地有同學和家毅打招呼,用羨慕的眼神看着他的自行車。這個時候的自行車還未普及,尚在讀書的學生的學費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已是個不小的負擔,不管他們心裏多渴望擁有一輛自行車,也都清楚眼下是不可能的。倒是有些早早辍學打工的人辛苦積攢幾個月後,一咬牙就買了輛嶄新的自行車,天天在鎮上四處溜達顯擺。
家毅微笑着回應每一個人,騎車超過許多或熟悉或陌生的同學,在學校傳達室旁的一小片空地停下,利落地下車落鎖。
“顧叔早!”家毅向傳達室裏的人影道。
“喲,劉家小子啊,”顧叔伛偻着身子一看桌上的老式發條鐘,“還早着呢,進來嘗兩口老子新腌的鹹菜!”
“不,不用了,我吃過早飯了。”家毅推辭道,卻抵不過顧叔的熱情,到底還是被拉進了傳達室。
通常,學生都不怎麽敢接近這個看門的人,見了他恨不得繞道走,因為顧叔樣貌駭人,臉上有一道從左眼睑斜到近右耳根的扭曲的刀疤,故而校門口進出的人雖多,傳達室裏總是冷冷清清的。家毅不怕顧叔多半是由于小時候見過他,那時他還沒有上學,顧叔也還不在學校傳達室看門。有一天晚飯後,他跟着父親上街遇到了顧叔。初始,他心裏是有些怕的,從未見過這般面目猙獰的人,直躲在父親身後,但父親似乎毫無所覺,如對待其他的老朋友一樣熱情地和顧叔打招呼。出乎意料的,這個帶着刀疤看起來兇狠的漢子竟笑着與父親說兄道弟,末了注意到小家毅,從兜裏掏出了一塊不知名堂的石頭說是見面禮。家毅看了父親一眼,然後伸出手接過,不忘小聲地道聲“謝謝”。顧叔哈哈一笑,便走了。
十多年過去了,他始終記得那響亮的笑聲,也記得父親伫立着看着顧叔走遠,然後低頭看着不安的他,問害怕嗎。他不知道怎麽答,父親也不是真的想要他回答,接着道:“有時候人吶,不能光看外表,你以後看得人多了,會懂得。你顧叔不是壞人,以後見到他有禮貌些,知道嗎?”他似懂非懂地點點頭,把話記在心裏。
那天之後他鮮少見到顧叔,直到上中學。數載光陰而已,記憶中那個嗓音嘹亮、身材高大的漢子竟變成了一個駝着背、花白頭發的老人了,但家毅确定,他就是顧叔,只有他臉上的傷疤以及大嗓門還是沒有改變。
不過幾平米的室內靠牆擺着一張簡陋的床,前面是一張攤着油條、稀粥、泡菜的桌子,一邊還坐着一個身穿校服的女生。她是顧叔的侄女顧婧蘭,經常提前來學校和顧叔一起吃早飯,和家毅在同一個班裏,不過在這個時代,男生女生間一般不怎麽講話,都是各自紮堆玩的,因而家毅和婧蘭不算熟。見她微微颔首,抿嘴一笑,家毅有些腼腆地道聲“早”。
顧叔給家毅添了一副碗筷,大着嗓門問了他幾句,沒多久就塞給他一根紙包着的油條,攆他和婧蘭快去教室了。
一路無言。
與顧叔不同的是,顧婧蘭樣貌清秀,是典型的江南女子,溫婉、親和,吸引人靠近,因而,初聽得顧婧蘭與顧叔是一家人,學校裏的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就好比是突然有人告訴你地上的爛泥與天上潔白的雲朵是一樣的。不過,這不礙人們對顧婧蘭抱有好感而遠離顧叔。家毅聽過不少男生偷偷議論顧婧蘭,他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喜歡她,但面對她的時候總覺得有點兒緊張,也不知該說些什麽。還好,沒幾分鐘便到教室了,喧鬧聲抹去了兩人間的沉默。
“毅,今天怎麽來晚了?”幾個男生揮着手問。
“沒,我剛在顧叔那兒呢。”家毅笑着說,眼角餘光瞥到婧蘭朝座位走去的同時向前後座的女生問早。
******************************************
當顧叔拉動操場旁牽着銅鈴的繩子,“叮——叮——叮——”響徹整個校園,代表着一天的課結束了。
回到家,母親在縫補衣服,大姐撥得算盤滴答響,其餘的人皆不見蹤影。這樣的情形早已見慣,家毅打過招呼便回房溫書了。
直到晚飯時,宅子裏的寂靜才被打破。廚房裏乒乓作響,飄出飯香,過一會兒一家人坐在八仙桌旁,其樂融融。劉家沒有食不言的規矩,只是一向不在飯桌上談論生意或者學校,單揀些家長裏短、鄰裏來往的事兒。
劉家有臺小彩電,但極少使用。劉二爺習慣了自小在父輩書房裏聽的時不時刺啦刺啦的收音機聲,如今依然在閑暇時打開一只邊角已經生鏽的老收音機,咿咿呀呀地唱着難以聽懂的戲曲。家毅這一輩童年時還沒有電視機,到十歲左右家裏才買了一臺黑白的。雖然幼年難免好奇,但父母都将其作為可有可無的擺設,極少去動它,他們也不敢不經長輩允許就打開它,久而久之對電視的熱情也就消退了,在日複一日的唱曲中慢慢長大。夏日的晚上,一家人會拿着蒲扇,拎着小板凳在門外乘涼,閑看晚霞消散,星月升起,間或與鄰人笑談,聽小孩子追逐打鬧;冬日,屋裏生起暖和的炭爐,看書的看書,記賬的記賬,或者幹脆圍在一起聊天聊地。這樣千篇一律的日子或許有些寡淡,卻很安詳,叫人忘記外面紛紛擾擾的世界。
作者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