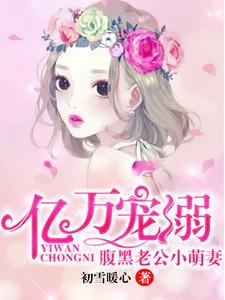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2章 章節
股輕蔑的笑隐隐在,臉上顯了一下。
楓林對楊坤還真有點垂涎,她可以用精致來概括,不高的個子,精致的五官,齊耳短發順直光滑。二十八九歲,小學舞蹈老師和老夏已經好了有四五年了,兩個人是撞車後一見鐘情的。
向陽的山坡,石頭房子的分布形狀,像是打開的折扇,一幢幢石頭房子簇擁街道,曲曲彎彎,房子街道和山坡融為了一體,是人改變了山,還是山造就人?人們只留下了搬動石塊的痕跡,山養育出石頭圪垯一樣堅硬的人,他們有像酸棗樹枝子一樣堅韌,帶着堅硬鋒利的蒺藜,默認貧瘠,但是還是要黃的小花,結出核大肉薄,沒有味道的酸棗。
廢棄房子缺門少窗戶,成了野貓野狗的天下,見人來東躲西藏,在遠處警惕的瞭望。
村口是“扇子把”處的石門洞,門洞的寬和門後的路比起來略窄。門洞是厚厚的石頭牆上,留出的一個像是通透的窯洞。洞壁有修建時預留出的方燈的壁龛。一塊平整的石頭上刀刻了字,模糊不清,老人們說,門洞是大洋馬的爺爺修建的,那塊石頭寫的是捐款記錄。
他一塵不染的軟底牛皮鞋,在凸凹石頭路上被踩的東歪西斜。沒有系扣子的藍色西服燕尾,被風吹起來,暗紅色的領帶在白襯衫前面被風吹得上下左右的翻動。他時而急促時而猶豫,時而皺起眉頭,一臉的殺氣。
沿着這熟悉的山路,找那種感覺,有素花在身邊的感覺。楓林十八歲以前唯一值得高興的事,就是上學時繞道走素花家門口,素花會準時和他彙合,爬那條山路。
堅硬的石頭蛋蛋子上,是踏着不緊不慢腳步的山民,臉色黝黑,皺紋深刻,似乎時光凝固,一茬人走了,又一茬長起來,那面孔、那神态沒有變化。
年輕的他們,瞪大了眼睛,尋找,享受任何一點的變化帶來的快樂。素花在家裏是四個孩子裏的老幺,三個哥哥,山裏人勞力多了日子就寬裕。三哥圏生是楓林的死黨,素花是三哥的小尾巴,和楓林一起形影不離。上山抓蛇掏鳥,烤熟了,楓林和圏生都把厚肉留給素花。素花說我也叫你哥哥吧,楓林說:叫吧。圏生說:不行,咱爹說楓林叫你姑姑。他娘叫咱爹叔叔。素花說楓林哥,喊姑姑!一群滿嘴肉香的孩子放肆的大笑。那笑聲在山谷裏回響,還有忽遠忽近的山鷹嘎——嘎——的叫。他們眼裏,沒有貧窮和苦難,只有快樂和溫情。
住在鳳起廟裏的老潘兩口子,說他們是金童玉女。從那以後,兩人一前一後走。見到人了就走的更快。
那年夏天,一個陰郁的早晨。緊一陣,緩一陣的雨一從晚上就沒有停。清晨天陰沉着臉,不時噼噼啪啪扔下幾個大雨點子。
黑雲彩翻卷着超南狂奔。風不大,像是戲臺上黑臉老包用寬大的袍袖佛過樹腦袋,碰掉樹葉子上存下的雨水。秋雨豪爽,大而且勤,酣暢淋漓的一場後。即使喘息時候的陣雨,也比現在說的,明顯降雨還要大。
楓林披塊塑料布,鞋脫下來放進書包裏,卷起褲腿,光着腳丫,兩個人還是一前一後,素花看前後沒有人,從後面快步趕上來,從蓋在粉紅色雨衣下面的書包裏,迅速拿出一條鮮豔的棗紅色圍脖,塞到楓林懷裏,臉很紅。楓林心跳的厲害,這一年素花和楓林都十五歲,從那以後,楓林喜歡雨,有了另一個原因。兩個人有了一個讓人心跳的秘密。兩人上學路上的陪伴,從前後改成了幾裏路外的等待。
素花出落的細挑的身段,鴨蛋臉,有山裏孩子的健康紅暈,又有那高貴的白皙,大眼睛似水,精致像模子鑄造出來的,性格開朗、和善,以致塵世似乎與她格格不入,她遠離了世間粗俗的凡人。
楓林是全公社學習和跑步的寶貝。素花唱歌是在縣裏拿獎狀的人。兩個人從娃娃長成了振翅欲飛的金鳳凰。
四
Advertisement
從學校到家,都要經過戲臺,在村子的最上面一塊平地上。
糙面石塊鋪面,條形青石戲臺建在空地的北頭,背靠青磚牆,前面立四根頂梁柱,紅漆斑駁。鬥拱、挑檐枋藍白油漆尚存,五脊頂正脊,垂脊,戗脊,花脊,鋪筒型小青瓦,牆面上,整個戲臺寬度上寫了标語“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頂梁柱後,是镂空帶花木格栅,留出拱形門洞,下接臺階,是演員上下用的。演出時又藍布門簾,分出前臺和後臺。
當年唱戲臺下坐的是觀衆,開會是聽衆,□□會是群衆,領導來了迎接的是學生。
楓林走的身上有了汗,坐在當年女人們捶衣服的條石上,他手裏的玉石念珠被快速的撚轉起來,手在簌簌地抖。
戲臺的左邊是鳳起廟,香客們不但送來貢品,點上高香,每年要為鳳起請戲。
戲臺背後是村委會,過去叫大隊部,和戲臺頂上的麒麟、鳳凰相伴的那兩個銀色的高音喇叭還在。
坐東北,向西南的一排石頭房,門窗全無,露出窯洞一樣的一個個穹頂,厚重的石頭牆,明顯氣派,五個拱門中間一個大,兩邊對稱的四個小,門後是走廊,走廊沿着走廊是一排房間的門,就像現在的辦公樓格局一樣。
院落圍牆的根基還在,院子裏水井,大塊青石做的井壁沒變,井口斜放了條石,架在上面的辘轳已經風化到不能觸碰,井下能照清楚眉眼的水面,現在只能遙遠的看到井口送下去的一點反光。
水井全村共用,老榕樹用磚圍了一個大圈,因為它的根做不能再向下長了,石頭太硬,只能浮在的地面有土的地方,像是巨大的龍爪抓到了地面上,石頭的井臺,是婦女們洗衣洗菜的地方,也是一個村子新聞的生産和傳播地。
他的意識回到過去——井旁的花開了,單花瓣,花朵巨大,像是彩色的喇叭。
貧嘴的老爺們牽着牲口經過,對聚在井邊洗衣服的娘們一句騷話,一群母鴨子樣敞亮的笑聲傳遍了整個村子。
樹後也有警惕而狡黠的目光,她們在面交頭接耳,後搬來的鐵匠劉新奇的老婆就掌握這種技能,在向別人附耳傳播秘密,眼睛向外翻,搜獲能注意到她的人,她要告訴更多人,自己在傳播的“秘密”。
“那寡婦家的楓林和他房後的梁家的素花,嘿!在柿子溝後的山砬子上親嘴兒哩,”她說完鼓起大眼泡的雙眼,看對方的反應,“那還差得了?俺家三小子背柴回來親眼看見的,說瞎話我掉崖下摔斷腿。”劉新奇老婆表情豐富的臉,扭曲着。
鳳起廟的兩間配房,省上來的“罪人”老潘兩口子住過。老潘是指老兩口子中的胖大女人,大家的印象中老潘一直是一身暗紫花的裙裝,抽煙卷兒,說話沙啞帶鼻胸腦腔共鳴,老頭帶灰色餅折鍋一樣的帽子,除了和老婆子在門口喝茶抽煙再就是把凳子做拐杖,貓着腰費力得走兩步。
至于他們犯什麽罪,只有村長和會計——梁鐵忠知道,他們從來不說。新奇老婆之流猜測一下,不着邊際一氣胡侃,大家一聽就沒有人提了。
村子裏供給他們吃的,有時候鐵,忠幫他們從縣上捎一小塊豬肉,讓自己孩子,卷生或者素花送過去。老婆子滋滋啦啦的炒菜,一個村子香。每次素花從那裏回來,不是頭上多了一個塑料發卡,就是手裏拿一本用報紙包了皮的書。
陰歷的九月二十五,是廟會,這時候和過年一樣的慶祝規格,親戚朋友都來上廟。
廟裏供奉的人是山西的一個買賣人,叫高鳳起,縣志上記載,明代初期,岸上村人從山西老槐樹下遷徙而來,有明白人看了這太行山上的陽坡,靠山面水,綠樹蔥茏,便駐紮下來,果然豐衣足食,人有旦夕禍福。
到元初,大旱,顆粒不收,路有餓殍,這時高鳳起送來了柿子樹種,不收一分錢,種滿了整個的柿子溝,救活了方圓幾十裏的人,鳳起廟,戲臺就是那時候建的。
鄉裏來人說了,這只是傳說,不能搞個人崇拜,能救窮人于水火的只有□□領導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四舊,迷信,要砸爛。
果然燒香被禁止了,但是沒有人敢動廟宇和戲臺,縣上來的宣傳隊也是在這戲臺上演節目,戲臺下放電影。唱戲、秋千還是轟轟烈烈。
從縣中學回來的三個人,楓林,素花,和衛國。臉上的靈性和睿智,已經和放羊種地的卷生之流有了明顯的區別。
蕩秋千是男孩子的事,楓林的每一次高高的蕩起來都引來下面的一聲噢——,每一個單手抓縄、橫騎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