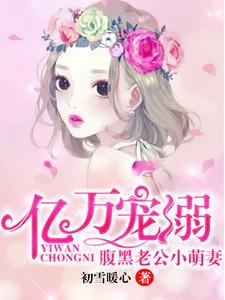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7章 戲如人生夢醉(1)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劇組聘了一個數學老師為夢非輔導功課。
晚上收了工、卸了妝,夢非已累得想趴下了,偏偏還要捧起課本,面對圖像和公式。夢非感到眼皮沉重不堪,哈欠連天,做幾道題大腦就混沌一片。
補課老師只管拿錢上夠鐘點,所以并不嚴厲,“慢慢來,挑會做的先做,來不及做的咱們明天再讨論。”
夢非抿嘴,合上課本,心有惆悵。其實她讀書還算刻苦,只是理科方面确實少些天賦。這讓她苦惱。
回到房間,夢非倒在床上,長嘆一聲,“太累了。”
張姐笑,“這就喊累了?罪都還在後頭呢。”
張姐說:“我拍了十幾年戲。這大冬天拍武戲外景,是最要人命的。”
夢非唏噓不已。
張姐又說:“以前我做場記,大雪天跪在攝影機前打板。還做過導演助理,起早貪黑,伺候導演鞍前馬後,一整天顧不上喝一口熱水。年輕的時候,不知什麽是苦,只會苦中作樂,落下一身病才後悔莫及。”張姐說着又嘆氣,“這行飯不好吃,受不完的罪,現在想通也已經晚了。好在如今做統籌,不用駐守現場了。在賓館裏做做表格,身體是不累,就是責任大,心累呀。”
話匣子一旦打開了,張姐便絮絮叨叨說不停。夢非累得一動不動,閉上眼睛,只想衣服不脫就這麽直接睡過去。
這時手機突然響了。夢非支起身,拿過手機看消息。
是芳芳發來短信。她說期中考試成績出來了,班裏一半人不及格,數學卷子出難了,她自己只得105分。
夢非看着短信,不由心驚。芳芳是班上理科最好的學生之一,尚且只得這個分數,自己沒有去參加考試,若是考了,估計是無法及格了。想到此處,她憂慮不堪,本來基礎就差,又落下大半學期的課,期末大考可怎麽辦?
夢非正發愣,芳芳的短信又來了:信給他了嗎?
夢非猶豫片刻,回過去:還沒機會,會盡快給他的,放心。
躺到被窩裏,夢非難以入眠,為期末考試擔心不已。若考不到班級前十,只怕無法向母親交代。
考試、成績、排名……她瞪着暗沉沉的天花板,只覺得壓力深重,禁不住胡思亂想起來,感到無奈且困惑。大人們總是教育孩子,要彼此友愛,互幫互助。可她不能想象友愛這種東西如何能存在。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生被灌輸的核心價值觀就是“競争”和“輸贏”。老師都喜歡給學生排名,誰“最好”、誰分數“最高”、誰“最聽話”,誰又“最笨”、“最低”、“最差勁”。老師鼓勵孩子們争當第一名,可當第一名的唯一辦法就是讓其他人都當不了第一名。成功的唯一手段就是讓別人統統失敗。所以,大家拼命苦讀,十六七歲就一大半深度近視。競争這麽激烈,當然不再有友愛、寬容、互助,只有嫉妒、自私、幸災樂禍。排名的壓力還間接導致了作弊和欺騙,以及只重結果的功利心。為了一個光榮的結果而放棄快樂的時光,甚至放棄誠實與友愛,這才是最可怕的。
讀書這麽多年,接受了各種知識和教條,背誦了各種數據和公式,但不再有思考、直覺、天賦、喜好,因為這些是不被鼓勵的。當然也很少有真正的友愛、互助、舍己為人,因為這樣做就會導致在排名上落後。
其實每個人都有各自獨特的天賦。為什麽要所有人都在統一的、标準的模式下成長,甚至強行分出優劣?每次考試,總有第一名和最後一名,對于本該快樂無憂成長的孩子來說,這真是可怕的夢魇。
夢非實在太累了,就這樣憂愁地想着心事,睡着了。
累極而眠時,反而容易做夢。她夢見自己坐在鋼琴前彈奏速度極快的《土耳其進行曲》。母親在旁手握條尺,不停敦促:集中精神,不準出錯。練完這一曲,趕快去做功課。她越彈越快,又怕出錯,幾乎喘不上氣來。
突然間,鈴聲大作,夢境切換到了考場。交卷時分已到,而眼前的試卷仍然空空。她急忙抓起筆,一題題演算。數字交疊在一起,她竟一道題都答不出來。老師從她手中抽走了試卷。她瞬間驚醒過來。
原來是制片部門的叫早電話到了。鈴聲響個不停。
她伸手抓起床頭電話,迷迷糊糊地應了一聲,“起了。”
窗外,天未明。
夢非睡眼惺忪地走進化妝間,泡上一碗方便面。
化妝助理一邊為她梳頭發,一邊問:“又沒睡夠?”
“可不是嘛,收了工還要做功課,我每天打雙份工呢。”夢非打了個大大的呵欠。
化妝助理笑,“功課很緊嗎?”
“當然,日讀夜讀,也只夠擠進班級前十。”
“何必總要争前十呢?”
“因為我是學生啊,考試成績就是一切。所以只好苦讀。”
化妝助理沉默了一會兒,輕聲說道:“做學生再苦,也比進入社會打拼舒服百倍。”她嘆了口氣,“就說咱們這個行業,這些年門檻越來越低,工資年年下滑,都被制片從中漁利了。我也想過轉行,可是年齡大了,專業太窄,沒有更合适的工作。早知就該好好讀書,也不至于現在累死累活。”
夢非從鏡子裏看着化妝助理,不過是二十五六的年輕女子,正值妙齡,說話卻老氣。在劇組工作的人都有一股高于實際年齡的滄桑感。
“我倒也不怕讀書苦。”夢非嘆氣,“只是覺得做學生很悶。學校發給你那幾本書,天天對着它們算呀背呀。就那麽三五本書,幾乎霸占了我們所有的時間,而所謂的課外書都成了閑書,只能偷偷看,弄不好還會被沒收。”
化妝助理聽着夢非學生腔的抱怨,淡淡地笑笑,溫柔地說:“無論如何,珍惜現在的時光吧。如果能讓我回到十七歲,我什麽都願意。”
是嗎?夢非笑笑不語。她倒希望自己現在是二十五歲。
梳好頭發,夢非低頭默讀劇本,複習當天要演的段落。此刻的她,最想珍惜的是在劇組的時光,這是她短暫逃避現實的唯一機會。
新的一天又在眼前了,她又可以把一切煩心事抛到腦後,專心地做她的若翎公主了。她感到快樂。在若翎公主的身份中,再累她也沒有怨言。
人人都看出她努力,都說她将來可以成明星。
她聽了不當回事。她并沒有什麽功利心,也不打算以後做演員。
演藝生涯免不了逢場作戲,阿谀奉承。劇組是個奇特的小社會,等級森嚴,人際關系複雜,又太過親密,吃住行全在一起。以演員作為職業,她未必适應。
所以,眼下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是她生活以外的風景。
這場殊遇,無關乎名望、利益,或者前途,只關乎她個人的成長。這是一次自我表達并發揮潛能的機會,一次蛻變的機會。她所看重的,并不是外在的榮耀,而是她所能獲得的內在經驗。
她早已決定,拍完這個戲就回到學校,過回原來的生活。她還是原來的蘇夢非。她必須,也只能夠,走這一條路。
她只把這次演出作為一份獨一無二的經歷來體驗。所以她認真、執着、全力以赴。這所有的記憶,都是她人生最寶貴的財富。
亦是一種因緣。
應制片部門的要求,夢非每天都會上網發布一條微博,有時表達自己對角色的理解,有時講述拍攝過程中的趣事,有時發一張現場的工作照。夢非知道,所謂面向公衆的日記,其實根本就不是日記,而是工作的一部分。
有時她實在累了,又想不出該發什麽內容,便對張姐叫苦,“還不如讓他們把每天的內容都寫好,我直接複制粘貼上去得了。或者,這個賬號幹脆就交給制片人去打理算了,反正也是宣傳工具,又不是我的個人觀點。”
張姐對她笑笑,笑裏有寬容,像是諒解她孩子氣的抱怨。張姐給出建議:多放幾張席正修的照片。這樣既可以省去筆墨,又能迅速增加粉絲的關注,還可以增加宣傳力度。畢竟席正修的知名度才是影片的最重砝碼。
夢非照做。果然,她的微博粉絲數迅速上升,短短數日內增至十萬名。但凡張貼的照片裏有席正修的身影,下面的評論便如潮水般洶湧,各種溢美之詞源源不斷。夢非算是見識到鐵杆影迷有多誇張。
不少影迷給夢非發來私信,詢問席正修的各種生活細節,還要夢非談談與他近距離接觸的感受。這類私信是不能回複的,夢非知道,就算回複也無可奉告。她只能關掉微博,佯裝不見。但每日數百封信件必然到達,又讓她不堪其煩。想知道他的事,為什麽不直接發信去問他?夢非想。但又想,怎麽知道他們沒發過呢?席正修的信箱肯定每天都爆滿。想到這裏夢非笑起來。看來做名人也沒什麽開心的。
與他接觸下來有什麽感受呢?夢非在心裏問自己。她忽然發現自己并不比其他人更有發言權。因為,他跟她幾乎就沒什麽接觸。
大部分時間裏,席正修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保持冷靜客觀,不流露明顯的愛憎,也從不表現情緒。
所以,在衆人眼中,席正修是一個非常冷、非常有距離感的人。
即便和他在一個劇組工作,天天見面,也無法從他身上窺透到任何更多的東西,他內心世界的東西。
直到很久之後,夢非才知道,冷漠只是一種表象,席正修的內心其實非常豐富、敏銳,別有一番天地。只是他很少給別人機會去靠近他、了解他。
也是到了很久以後的将來,她才漸漸明白,他們之間的故事,并非只是她一廂情願的少女懷春。若他對她無意,她是根本沒有機會靠近他的。
是他,主動向她打開了一扇久久不曾開啓的門。
是他,邀請她走入他的世界。
在夢非後來的回憶裏,席正修第一次與她深入交談,是在一次換景休息的間隙。她記得那是一個金燦燦的午後,陽光把林子裏厚厚的落葉都曬得焦黃生脆。工作人員各司其職。夢非因下一個鏡頭不是她的戲,偷閑坐在一旁捧起一本詩集來讀。片刻之後,她餘光感覺到席正修走過來。她擡起頭,看到他在不遠處站定,喂他在戲中騎的一匹棕色大馬喝水。他輕輕撫摸它的脖子和鬃毛,眼神和動作都極為溫柔耐心。
她在一旁靜靜地注視着他,只覺得他對待那匹馬十分友愛,仿佛這匹馬并非劇組租借來的道具,而是他從小飼養的寵物,是他的家人和夥伴。
她不禁好奇,問他:“你不怕嗎?”
她曾多次被人告誡,不要随意靠近劇組裏的馬匹,牲口畢竟是牲口,萬一被踢到撞到,有個好歹,沒人負得起責任。
“怕什麽?”他微笑。
她答不上來,抿嘴一笑。
他卻說:“動物有靈魂,你相信嗎?看它們的眼睛。”
她看向那匹馬的眼睛,像很大的玻璃珠,漆黑而溫潤,有一股溫柔的哀愁,又不乏流露出警覺與自尊的神态。她相信他的話,動物有靈魂。
“你很愛動物。但是,不怕它們突然傷害你嗎?”她問。
“不怕。”他微笑着,走到她身邊坐下,“害怕是社會教化的産物,并非人的原始屬性。小孩子都不懂得害怕,敢于赤裸地在泥地裏奔跑,敢于擁抱自然,擁抱任何人、任何動物。人若都能變回小孩的樣子,多好。”
“可小孩如果沒有大人管束,遇上危險怎麽辦?”
“什麽是危險?”他笑着反問,“我小時候在非洲,騎過大象,抱過獅子,還同蟒蛇玩耍,現在依然活着。”
她驚呼道:“你去過非洲?”
他看着她吃驚的樣子,只微笑。
“你怎麽會去過非洲?”她追問。
他笑而不答,只撿起她手上的書,“你在讀什麽?”
“一本詩集。”她有些不好意思,“你可能沒聽說過。”
他随意地翻看着,臉上有微妙的笑意。
她想,他一定在心裏笑話她,小小年紀讀這種文藝而晦澀的英文詩,太做作了。但下一刻,又不知哪兒來一股勇氣,她拿起書,對他說:“我念一首給你聽,你想聽嗎?”
他未答,她已兀自念起來:
We underestimate damage
done to the sky
When we allow words
to slip away
into the clouds
I remember……
她念到一半,他已跟上:
I remember ****** promises
to you outside We
were watching flowers
that hadn’t opened
A bee darted, careful
not to stick to
your half-shut mouth
她驚訝地瞪着他,“你也知道Mortensen?”
他微笑不語。
那一刻,她看着他,腦海一片寂靜。
她最喜歡的丹麥詩人的詩歌,他竟然也會背誦。
他身上究竟有多少讓人驚嘆的秘密能量?
在他開口念出詩句的那一瞬間,她覺得內心的花園來了造訪者。
她是一直在此守候的人,身邊有花朵、飛鳥、大樹和沙沙的風聲。但很多年很多年,都只有她獨自一人。獨自等待,獨自長大。
然後,這一天,她忽然聽到了腳步聲。他的腳步聲。
柔軟的青草和泥土在那小心翼翼的步伐下,發出輕輕的嘆息。他就這樣靠近她。她擡起頭,迎上他的目光。
“他是我最喜歡的詩人。”她克制着內心的驚喜與激動,平靜自然地說。
“你喜歡他什麽?”他問。
“自由。”她脫口而出,“他的作品所傳遞的自由精神。”
他看着她,眼中隐約浮現出笑意和贊許。
她又說:“我們的生活充滿了規則、限制、教條。我心底最渴望的,是突破所有的羁絆,自由地來去,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追求心中所念。”
還有,自由地擁抱一切,擁抱自然,擁抱所有的人、所有的動物,就像他所說的那樣,毫無畏懼,不害怕任何事物,只跟随內心的自由與愛。
她說:“自由,幾乎就是生命存在的最大意義。”
這些心裏的話,她不曾對任何人說過。不知為何,卻願意在這個依然陌生的男子面前吐露心聲。
他微微一笑,輕聲說道:“等你再大一點,你就會懂得,沒有人可以擁有絕對的自由。我們無非是犧牲某一些自由去換取另一些自由。”
她怔怔地看着他。他溫和簡單的幾句話,觸動了她的心靈。
平常從無人與她這樣對話。她完全不曾想到,他,一個大明星,會與她懇摯相對,平等交談,并探讨她所感興趣的話題。
她略有恍惚,沉思片刻,鼓起勇氣問道:“那我該如何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如何實現自己的夢想?”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實現自己的夢想。”
她笑起來,“你只是在重複我的話。我想知道的是,做成這些事情的秘訣是什麽?”
“秘訣就是,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實現自己的夢想。”
他的表情十分認真、虔誠,并無絲毫戲谑。
自由是終極追求。但在世俗社會中,自由畢竟是有限的。
可那不能成為逃避夢想的借口。生活中的一切選擇,最終都只是在“取”和“舍”之間選擇。想要達成夢想,并沒有什麽秘訣,有所舍,有所取,然後,放手去做。就像Nike廣告說的:Just
do it。
關于萬事萬物的一切道理,其實就這麽簡單。
她看着他,心裏又靜又空,發不出聲音。
一種無可名狀的情緒萦繞在兩人之間。
她感受到他的氣場,感受到自己被鄭重對待的情誼。
或許,從一開始,他就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把她當成小孩子。
他對待她的方式,有一種特別的張力。他對她的親近,以及在控制力下表現出來的疏離,都帶着真誠的善意,以及謹慎的持重。
在某些時刻,她能夠感受到他內心的光芒。那光芒穿透他冷淡矜傲的外表,抵達她面前,飽含着力度與溫情。
她由此知道,他認識她。他能看到她內心深處那團微小而執着的火光。而他的身心內在,亦有某種東西與之映照。
劇組每天七點出發。賓館的早餐六點開始供應。主要演員每天五點就要起來化妝,有時化完妝已沒有時間吃早餐。所以夢非常常只在化妝間泡一碗方便面當早餐。
這天清晨,席正修走進化妝間,把一冊書和一只紙袋放在夢非面前。
夢非詫異,拿起書,是Mortensen的最新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