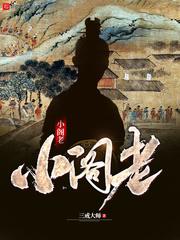第22章 章節
人以降及物故,分随武還者九人”。注:“物故謂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王先謙補注引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歾,音沒。”又引王念孫曰:“《釋名》:‘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史記·張丞相傳》集解:‘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所能與事’。案宋說近之,物與歾同,《說文》:‘歾,終也’,或作殁,歾、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死亡。”可見這裏對“物故”的解釋就是死亡,囊括諸死因。
至今日本仍舊有“物故”一詞,特指去世,也是古漢語遺留下來的一點痕跡。
而在《三國志·向朗傳》中卻寫道:“朗素與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
也就是說馬谡的結局,光是《三國志》中就有三種說法:處死、獄中死以及逃亡。
不過仔細推敲來看,這三者并不矛盾。這三個說法也許是同一件事在不同階段的發展。馬谡可能是先企圖逃亡,被抓,然後被判處了死刑,并死在了監獄中。
從“朗知情不舉,亮恨之”這一點來看,馬谡逃亡的時間發生于蜀軍從隴西撤退之後,而且他逃亡的目标并不是去私下找諸葛亮——也許他打算北投曹魏,或者準備直接南下成都找後主與蔣琬說情,不過這一點現在已經無法确知。總之馬谡非但沒有主動投案自首,反而繞過了諸葛亮企圖逃亡。
但即使有向朗幫忙,馬谡最後還是被抓住了。接下來就是諸葛亮的“戮谡以謝衆”。雖然文中說是“謝衆”,但未必意味着公開處決。考慮到馬谡的身份,諸葛亮也許采用的是“獄中賜死”這類比較溫和的做法,然後将死亡結果公之于衆。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馬谡首先被公開判處了死刑,但是“判罪”和“行刑”兩步程序之間還有一段間隔的時間。就在這段間隔時間裏,馬谡因為疾病或者其他什麽原因“物故”。因此在法律程序和公文上他是“被戮”,而實際死因則是“物故”(小說中就采用了這一種可能性)。
無論是病死還是賜死,根據前面考證,都可以被稱為“物故”。
〔關于費祎〕
吾友葉公諱開對于費祎其人有專題文章論斷,此處就不贅言,請參看《暗流洶湧——也談費文偉》。小說中的費祎性格就是參考此文而形成的。
〔關于費祎遇刺事件〕
《三國志·蜀書·費祎傳》雲:“(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費)祎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
費祎被刺是蜀國政壇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國自諸葛亮死後所采取的防禦性國家戰略再起了大變動,蜀國鷹派勢力的擡頭。這件事單從《費祎傳》來看,只是一次偶發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聯系到一起,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麽簡單了。
刺客郭循的履歷是這樣的。《魏氏春秋》說他“素有業行,著名西州”。《資治通鑒·嘉平四年》載:“(延熙十五年)漢姜維寇西平,獲中郎将郭循。”就是說姜維進攻西平,雖然西平沒打下來,但抓獲了時任魏中郎的郭循。後來郭循歸順蜀漢,官位做到左将軍。要知道,這可是馬超、吳懿、向朗曾經坐過的位置,足見蜀國對其殊遇之重,不亞于對待夏侯霸。
但是這個人卻并不是真心歸順,他終于還是刺殺了費祎。魏國得知以後,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使其子襲爵。(《資治通鑒·嘉平五年》)
Advertisement
這起刺殺事件仔細推究的話,疑點非常之多。就動機來說,這不可能是魏國朝廷策劃的陰謀。費祎是出了名的鴿派,他在任期間是蜀魏兩國最平靜的一段日子,幾乎沒發生過大規模的武裝沖突。魏國正樂享其成,不可能刺殺掉他而讓鷹派姜維上臺,自找麻煩。
這也不可能是私人恩怨,郭循跟費祎就算有仇,他也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出姜維什麽時候會攻打西平,自己會不會被俘,被俘以後是直接殺掉還是受到重用等等。如果真的是因私人恩怨而刺殺費祎的話,不可能将整個計劃建築在這麽多偶然之上。
這兩個可能都排除的話,剩下的最有動機殺費祎的人,就是姜維。
姜維與費祎的不和是衆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魏的鷹派,而後者則是堅持保守戰略的鴿派。在費祎當政期間,“(姜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祎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可以說姜維被費祎壓制得很慘。費祎死後,能夠獲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維。事實上也是如此,陳壽在《三國志·姜維傳》裏很有深意地如此記錄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短短一行字,姜維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換句話說,費祎的死,姜維是有着充分動機的。
而姜維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呢?《姜維傳》裴注裏有載:“傅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就是說姜維這個人,對功名很執著,而且不像《三國演義》裏一樣是個愣頭青,反而很有城府,好“陰養死士”。而郭循在衆目睽睽的歲初大會上刺殺了費文偉,擺明了他自己就是拼個同歸于盡,不想活着回去,這是标準的死士作風。
再回過頭來仔細研究郭循的履歷我們會發現,西平戰役的發動者是姜維,捉住郭循的是姜維,把他抓住不殺反而送回朝廷的還是姜維。換句話說,郭循看似是偶然地被俘才入蜀,實際上這些偶然卻是完全可以被姜維控制的——姜維有能力決定發動戰役的時間、地點以及對俘虜的處置,這一連串偶然只有姜維能使其成必然。
這幾條證據綜合在一起推測,再加上動機的充分性,很難不叫人懷疑姜維在這起刺殺事件中是無辜的。
我們這些生活在後世的人,憑借殘缺不全的史料尚且能推斷出姜維有殺人的動機和嫌疑,當時的蜀國肯定也有人會懷疑到他。但是史書上的記載中姜維是完全無辜的,和這事絲毫沒關系,這是為什麽呢?
在《資治通鑒·嘉平四年》載有這樣一件事:“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這一條記載很值得懷疑,因為如果真是郭循上壽時想刺殺後主而“為左右所遏”,那他的意圖早在拜見後主前就暴露出來了,當時就應該被拿下治罪,怎麽可能還會放任他到延熙十六年年初去參加歲初宴會并接近費祎呢?
更何況,刺殺後主對于魏國來說是沒什麽好處可言的。那時候劉禪的兒子劉睿在延熙元年就被冊封為太子,而且朝內并無立嗣之争。也就是說,劉禪的死不會導致蜀漢局勢混亂。一名魏國降人有什麽理由對後主如此痛恨到了屢次企圖刺殺的地步呢?
所以這一條記載不像是對郭循拜見後主情景的描述,倒像是在刺殺事件發生後為了充分證明郭循“存心不良”而後加進去的補敘。然而,這條補敘看起來似乎只是蜀漢群臣深入揭批郭循反革命行徑的一條黑材料,但仔細推究來看,卻不難發現它大有深意。它給人一個暗示:“郭循原本是打算刺殺後主,因為太難下手,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轉而刺殺後主的首席重臣費祎。”
只要蜀國相信那條記載是真實的,那姜維的嫌疑就可以澄清了——“我總沒動機殺我朝皇帝吧”,進一步推論的話,也許這個記載就是姜維或者他授意的某位朝官說出來的。
最後要提的是郭循的身份。以郭循在魏國的地位和名望,與姜維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大。進入蜀國的“郭循”,也許只是姜維以一名死士做的替身罷了,而真正的郭循也許已經死于西平戰役之中。以姜維的地位,想要藏匿特定敵人屍體,以自己的親信代替,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綜合上述種種跡象不難發現,整個刺殺事件的形成可能是這樣:最初是姜維拿獲或者殺掉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拿自己豢養的死士冒了郭循的名字,公開宣稱俘獲了“郭循”。接着郭循被押解到成都,在自己表示忠順和姜維在一旁的推動下取得蜀國信任,拜左将軍之位。然後在延熙十六年年初大會上,策劃已久的郭循殺了費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維為了澄清自己的嫌疑,在事後授意近侍官員對皇帝劉禪說郭循腦後有反骨,好幾次想刺殺皇帝都被左右攔下了,以此來防止別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