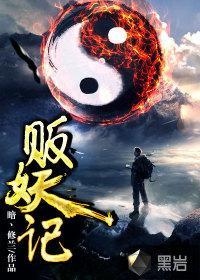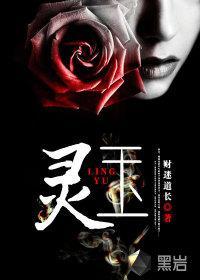第4章 章
第 4 章
趙懷民凝睇着漸行漸遠的背影,陷入深思。
古代的孩子真卷,寅時就要去上學,就他而言:5點能從被窩裏爬出來就需要很大的毅力,更遑論半夜三四點踏着星光就要去上學。
所以..他是躺平呢?還是躺平呢?
躺平的前提是生命無虞,衣食無憂,略有家底,族人欣榮。
他...好像一個也不沾邊。
天臨國建朝剛剛二百多年,現任皇帝憲元帝賺錢能力一般般,花錢手段花樣百出,生活比較奢侈。骨子裏喜歡作詩和畫畫,所以經常微服私訪下江南。
朝政大大小小事情由三省六部經手,要緊事面呈皇帝,由其審核審批,蓋章啜印。
本朝尚文輕武,文風濃郁,就去年樂陽郡科考而言,參考人數多達4萬人,樂陽郡總人口大抵才14萬左右,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茍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樂陽郡算是大郡,換算下來,錄取比例為總人口的1/50000左右,可想而知去年下場考試的舉子多麽慘烈。
哪怕有人僥幸考上,突發意外被取締了,也不能在錄取其他人,寧可不錄取,也不濫竽充數,錄取率偏低,下場考試人多,所以....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
真的是學到老,考到老,古人起得比雞早,睡得比雞晚,年年如一日,日日如時時地看書,寫文....
而他前世早上9點起,晚上11點睡覺,中午還要休息2小時,小日子過得不要太舒服。
他不卷,他們才是真正的卷王!
趙懷民悄悄摸進屋裏,靠在椅子,腦子裏想着自己要從事什麽職業。
依着他爹他娘的意思:在縣學私塾裏囫囵學寫字,不做睜眼瞎,以後在鎮上或者縣裏找夥計,書童等不下力的活計。
因為原主已經7歲,腦子轉不開,有點傻愣愣(老實基因遺傳于他爹),而同齡孩子已經學完《三字經》等基礎理論,官二代商二代的孩子4歲在家就有長者開蒙,世家大族更是從胎教開始,從小培養孩子敏而好學的秉性。
若是遇到天生愚笨的孩子,那夫妻倆都要多生幾個,練小號,培養老二老三老四,甚至是老N。比如原主爹,俗話說:三歲見老,原主三歲就算是玩泥巴也哼不出《及第謠》,7歲了連親戚關系都理不清。
他家人認為趙懷民廢了,于是他弟弟趙懷德光榮出生了。
他已經輸在起跑線,他弟弟輸不起!(他爹口頭禪)。
于是,趁着他弟弟啓蒙,連趙懷民也一起打包送到了二哥家裏寄宿。
其實這就是內卷的後果,本朝十幾年前,孩子都是7歲到14歲啓蒙都不算晚,這幾年由于五谷豐登,民康物阜,大家兜裏有些餘錢,便争相為子孫争口氣,誰都想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一首《及第謠》在民裏鄉間傳頌多年,就連偏遠村居門口玩泥巴的垂髫稚兒都能哼唱幾句,可想而知:當今文風多盛,科考多濃。
就算是家財萬貫的商賈也在階級鄙視鏈最頂端,妥妥遭人白眼兒,地位只比奴隸高一些,比士農工要低一些。
士農工商是固有階級定位,誰都站在頂端,誰就有話語權。
所以趙大伯這些年賺了些銀子,更受了不少氣,吃了不少虧。
前些年趙永祿剛上任,瑣事繁多,實在騰不開時間去教導孩子,一直奔走在官場,拉攏人心,服務百姓,摸摸索索幾年,近年方才與大家打成一片。
去歲才給自家孩子啓蒙,今年終于集齊子侄準備送到私塾去啓蒙。
至于為什麽不送到官塾?
因為塞了不少有頭有臉的官N代商N代,資源有限,關系龐雜,良莠不齊,夫子更是打不得罵不得,學習氛圍不算好,古有孟母三遷只求一個環境優良,良師益友,教學嚴苛的好學堂,趙永祿是一縣之令,又是一族之長,不得不深思熟慮。
既要旺家族,又要避開一些閑言碎語,給孩子們創造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
于是他選擇送孩子們去莊外顧家私塾就讀,那裏環境清雅,風景宜人,最是讀書好去處。
在天臨朝要想成為一族之長,一看身份地位,二看年齡輩分,三看聲望,缺一不可,官為上。
既然趙永祿想要族裏孩子都開蒙,走科考之路,那他還有的選嗎?畢竟族長都發話了,他爹娘持觀望态度,因為見過原主木楞,他們已經準備好原主的後路---當書童或者夥計,不至于堕了趙二伯的念頭。
其實趙懷民對親戚關系不是特別...理解,在現代,他們那裏都是“一代親兩代表三代四代全拉倒”。
出了門,大家打個招呼就是最大的禮貌,更別說“一人升官雞犬升天”(雞犬主要指那些極品親戚)。
天臨朝不一樣,最注重孝道,孝道不僅僅是傳統美德,孝已經成為國家政策。不孝者輕則被人辱罵輕視,其後代不可科考,重則苔刑三十。
朝廷自上而下對鳏寡孤獨者多有照顧,朝廷對那些80歲以上老人給予特殊的關照,賜杖,資助財務,減免租稅,授予侍人的等等,地方也會根據其生活情況有減免課稅等措施。
更重要的是科舉還要考《孝經》,上層就已經決定了孝道的重要性。
推崇孝治無外乎便于中央統治,從思想上讓百姓學會遵從老人,順從長者,打壓違背固有階級傳統的思維萌芽。
一連數日,趙懷興卧床修養,這可苦了趙永祿兩口子。
為了減輕兩口子的壓力,趙懷民和嬷嬷們在白天多看着點。
待到了他身體康複了,趙永祿連忙擇了佳期,送子侄們去就讀。
趙家兄弟們也開始了漫漫寄宿求學路。
“一拜三聖祖師,九叩首”聊表讀書決心,虔誠希望祖宗保佑他們一舉高中。
“二拜師父師娘,三叩首”跪送六禮束脩,顧夫子微微駭首,一臉欣慰地收下了拜帖以及其他東西,同時給趙懷民幾人回贈了一本《孝經》,意味着正式成為顧家私塾第三屆新生,擔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大任。
接下來就是顧夫子訓話時間,他清了清嗓門:“即今日起,你們就是我門下的徒兒,進了顧家學堂就要遵守學堂規矩”
“首先為師給大家一一賜名,惟願列為遵從本心,堅守學業,恪守孝道”
賜名意在表字。
按照年齡大小,趙懷民被賜名行儉,趙懷德,趙懷興分別賜名崇禮,崇孝。
“謝謝夫子”
他們齊齊跪道。
拜師禮一套流程總算是走完了,趙家幾個兄弟開始留在顧家學堂開始适應新生活。
趙永祿不免要和顧家夫子小酌一番,算是排遣一下心中的煩悶。
“師弟,這裏就是咱們日常學習的地方”
周圍是一圈花圃,最顯眼的花束是牡丹,放在學堂門口兩側,玫瑰次之,正是嬌豔。
在前面帶路的學子是顧翀,表字:顧崇廉,比較活潑。
也是顧夫子的侄子。
“這裏是工房,主要放琴棋書畫常見範本以及農具,工具等,以後老師會展示給大家”
他邊走邊介紹,還不忘留意大家的反應,不過都是蘿蔔頭,看都看不見裏頭什麽樣子,能有什麽好奇心。
地方不大,勝在環境清幽,一顆參天槐樹亭亭如蓋也,人多庭前植之,一取其蔭,一取三槐吉兆,期許子孫三公之意。
趙懷民逡巡一圈,方才問道:“多謝師兄”
“敢問在哪裏出恭?”
趙懷德小嘴一撅,死死夾着屁股,板着小臉,忍得有點辛苦。
趙懷民自是察覺到他的一樣,拉着他看向顧崇廉,一臉歉意。
“出了門左拐”
趙懷興那雙吊梢眼滴溜溜轉,不聲不響地跟在趙懷民身後,到了廁所,就擠開他們,使勁兒往裏頭鑽。
迎面就撞見趙恣,兄弟倆摸着鼻子一臉曬然。
原來趙恣沒有見他們是在廁所,知道真相的趙懷民有點...尴尬。
倒是趙恣行了禮便徑直走了。
出了廁所,趙恣和顧崇廉都在外頭等着。
“...這幾日父親為了抗旱,白了頭”
“不是有渠水?怎會幹了田地”
顧崇廉摸着腦袋,很是疑惑。
趙恣指着院子裏的花草樹木解釋道:“遠水解不了近渴”
“今年高溫不下,沿途莊稼葉子焦了,稻田裏魚蝦絕跡,初露細痕”
“遠得不說:咱們這裏的夜風都是熱浪..由此看見:幹旱也是很有可能”
顧崇廉想不出什麽好點子,正好看見趙懷民出來,激動地招手。
“好了嗎?”
“咱們快到處走走”
他以為成功岔開了話題,熟料趙恣涼涼一瞥,道:“夫子說今日的課外作業:如何抗旱保收?”
顧崇廉摸着他的腦袋,眨巴眨巴眼睛,笑道:“謝謝”
“抗旱的法子那麽多,總有一個合夫子的胃口”
好不容易休沐一天,他才不想看書墨字帖。
“可是...先生要求:大家的答案不能一樣,如有茍同,一律罰抄孝敬十遍”
顧崇廉收回了腳,臉上艱難地擠出一絲笑意,“師弟...真是對不起”
“學習為重,師兄請便”
顧崇廉垂頭喪氣地往學舍走去,好像鬥敗的公雞失魂落魄,趙懷民不由得咂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