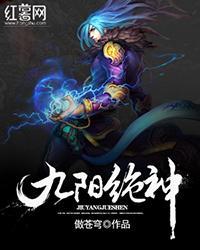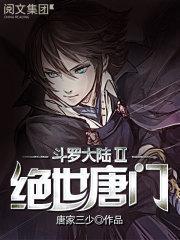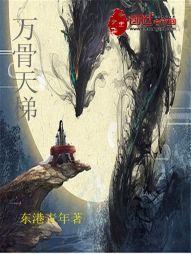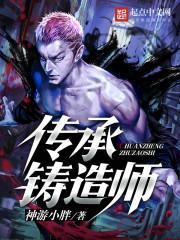第11章 ☆、桓氏之興(下)
次日清晨,天灰蒙蒙亮,廿人廟外已經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有人在大聲叫門。桓啓驚醒,一手拿佩劍,一手抓衣服,便湊到窗邊觀察情況。
老巫師不急不緩地從房間裏出來,廟門大開,幾個壯漢便擡着一個人進來。那人奄奄一息,像是久病将死之人。
那幾個壯漢看似粗魯,到了院子裏卻低聲細語,不敢喧嘩。病人擡到一間屋子裏,不久便傳來了哭喊聲,看樣子是沒救了。
又過了一會兒,那幾個壯漢将人擡了出來——此時已經用白布覆蓋。老巫師在後面跟着,面容嚴肅,一直送到大門外。
桓啓本擔心那些人會鬧事,看到這兒才松了一口氣。他推開門走到外面,将早已備下的珍稀藥材奉上,口中道:“蒙大人留宿,弟子無以為報,只有略奉薄禮,請大人笑納。”
他這話說的很假,老巫師卻很不客氣,只略微看了一眼,便收下了。又留了桓啓用早飯,這時候沒有看見源靜。
“你無需東瞧西看,源靜已經去采藥了。”
老巫師這麽說着,又感嘆道:“此地雖不是窮山惡水,亦不是什麽富庶的地方。洵都的好藥很難送過來,只靠着我這老骨頭日日上山采藥,終究不是個辦法。現在源靜來了,實在不忍看她這樣度過日後的日子啊。”
桓啓想起老巫師昨晚的話,與現在的對比對比,便覺得好笑。他倒是生出了一絲憐憫之心,便問:“翕教的神廟都是要登記造冊,難道廿人廟不曾……”
他話說了一半,老巫師的臉色便已經作了回答。翕教的神廟确實需要登記造冊,收入頗豐的大廟因此上繳供銀,若是有入不敷出的小廟,亦可借此維持日常開銷。只是,據說這廿人廟荒廢已久,靠着村民捐贈才修繕一新,只怕還沒到可以向洵都要錢的地位。
然而,據說這廿人廟香火頗盛,不至于如此蕭條。桓啓擡頭看着老巫師,忽然明白了——只怕不是這廿人廟缺錢,而是廿人廟太大度,将那香火錢都拿去買藥救治村民了。若當真如此,這老巫師倒也着實令人敬佩。
老巫師也不過感慨一番,用過早飯之後,便客客氣氣地将桓啓送到大門外。
“洵都的勳舊子弟中,甚少有閣下這樣的人。希望閣下能走正道,為翕教出一份力,到時候自有那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桓啓心下吃驚,覺得這老巫師故意賣弄;又暗自歡喜,期待老巫師的話能成真了。他恭恭敬敬謝過老巫師,便上馬離開了。
走到山坳時,桓啓勒馬回望,正巧看見一襲白衣從那分割成小塊小塊的稻田間款款而過,那背上的竹簍,露出高過人頭的綠色枝葉,反射着朝陽。
那不是源靜,又是何人?
Advertisement
桓啓看得癡了,一時竟不舍得移開目光。他看着源靜沿着長長的稻田邊緣走過,一直走到那小小的神廟外面,與前來朝拜的村民打了招呼,便一同進了廟中。
朝陽一點一點升高,一點一點照亮了群山環繞的土地,照得那小小的神廟熠熠生輝,一縷溝通人與神的煙從正殿中升起,似乎飄到了雲霄之中。
突然,桓啓策馬前行,迅速離開了這個地方。他要回去,他要回到洵都去,洵都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他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這兒再好,不過是因為暫時有了源靜的存在。
這條路不好走,桓啓險些從馬上摔下來,他撫着一顆狂躁的心,跌跌撞撞地到了洵都城外。他想起老巫師的話,忽然策馬往什桐神廟的方向,然跑出半裏地,竟又回來了。他得先回洵都。
回家拜見過一衆長輩後,桓啓又出門去見新結交的勳舊子弟。他向這些人稍微透露了廿人廟的事,神女濋留雖死,餘威猶在,自然有那些願意出力的人。源靜自己也是勳舊子弟,撐着源氏的臉面,便是沖這個,也要有幾個熱心腸的人。
桓啓暗自高興,他能稍微為源靜做點什麽,便很高興了。這種事不求對方知道,回報什麽的,也不在考慮之中。
這些日子裏,洵都暗流湧動,桓氏想要複興,必須做出選擇。身為家中唯一的男丁,桓啓參與了這個關于桓氏未來的決策。
當桓啓說服長輩們站在汜留這一邊後,他不由想:若是神女濋留還活着,源靜定然不必去受這份罪。以神女伴讀之尊,也不會如此。不過一個神女之位,卻與多少人的榮華富貴息息相關。
不久之後,桓啓得到消息:廿人廟成為翕教登記在冊的衆多神廟之一,但是,老巫師過世了。老巫師過世就意味着源靜要一個人支撐起整個廿人廟,桓啓恨不得馬上去那兒看看。
老巫師就地辦了葬禮,洵都派了巫師過去幫忙,桓啓一時沒法脫身,亦不敢在此時輕易出頭,只好忍耐着。等事情過去,桓啓才尋了一個出去的理由。
神女濋留之死是翕教諱莫如深的話題,遠離洵都的人們卻在神廟之中毫不避諱地聊起來,而且暗指源靜作為神女伴讀失職。
“這樣的人如何能在廿人廟主事?”
桓啓聽到了這句話,他相信源靜也聽到了這句話,但源靜什麽都沒說,繼續為人把脈。立在庭院裏的人更加猖狂,便又口出狂言。
“你們可知妄議神女是什麽罪名?”
桓啓幹咳一聲,冷冷開口。
翕教極重上下尊卑,從不許以下議上,一般人也不會犯這個忌諱。這些人有恃無恐,怕是受人指使,再加上源靜又是個不喜與人辯駁之人,只怕會會毀了源靜名聲。而桓啓是個洵都來的外人,自然有些威懾作用。
果然,此話一出,他們便不再說話,灰溜溜地走了。
源靜仍是淡淡地,桓啓瞧了,竟覺得該如此。這二人各自懷着心事,誰也不料這竟會是最後一次見面。
桓啓第三次去廿人廟,是幾個月後的事。那時洵都附近的村寨發生了瘟疫,死了很多人,洵都城人心惶惶,先是宵禁,不久之後連白天也關着城門。幾個月時間過去,瘟疫才漸漸得到控制。
桓啓急着去見源靜,還有一個理由。在發生瘟疫這段時間裏,桓氏尊長為桓啓說了一門親,雙方的長輩都覺得好,就這麽定下來了。婚期在瘟疫結束後定了,在這之前,桓啓想去見見源靜。什麽都不必說,什麽都不必做,他只想看源靜一眼——也許是最後一眼,從此仍是陌路人。
廿人廟出奇地冷清,桓啓有個不祥的預感。他推開簡陋的大門,裏面是個曾經見過的老者。那老者說,源靜在在救治病人的過程中染疫,不治而亡,因為正是在瘟疫最厲害的時候,喪事辦得極匆忙極簡單,洵都派人過來善後,委托他這個老頭暫時幫忙照看神廟。
桓啓聽後,悵然若失。他乘興而來,悵然而歸。
有人說,源靜在神女濋留死後萌生去意,所謂不幸染疫不過是有意而為之。至于真相到底如何,只有源靜自己知道了。
裔昭用一種略帶惆悵的語氣說完這段,然後就有人來禀報,說晚飯準備好了。裔昭便要領着小徒弟去用飯,誰知小徒弟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擔憂道:“師父也會去得這般突然嗎?”
她說的是裔昭是否會像源靜那般突然離去,那流露出來的滿滿擔憂十分真摯,看得裔昭心生罪過。
在翕教看來,世有陰陽二界。陽界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死即托生陰界;陰界之人,日落而作,日出而息,死即托生陽界。連接陰陽二界的,乃是八百裏往界山,惟此山中人,可超脫陰陽二界之生死,與天地同休,與日月同壽(神尊乃神明,不受陰陽界生死循環之限)。
在陰陽兩界中,死去的人需要火化肉體皮囊,其靈魂才能被巫師引導升天。若沒有火化或沒有巫師引導,逝者之魂将在原地徘徊,最終忘記自己從何而來,欲往何處而去,直到變成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脫。
按這個說法,翕教之人并不用擔心“生與死”的問題,因為他們在實際上是“永生”的。真正需要擔心的,是葬禮能否按照教規辦,以便獲得下一次生命。
裔昭以為這個道理可以安撫好小徒弟,便說了說,眼見小徒弟似懂非懂,她只好又道:“人生一世,有生便有死。死,不過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并沒什麽大不了的。”
小徒弟仰頭道:“師父也會死嗎?”
裔昭這才明白,小徒弟擔憂的是她會突然返回往界山,而不是生與死的問題。她活得太久,像一個不會“死”的神,翕教上下已經習慣這樣一個神一般的大祭司,也就漸漸就忽略了大祭司也會“死”這件事。她雖然也曾意識到這個問題,卻總是假裝不知道。
看師父不答,小徒弟又道:“師父,如果人只是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那不就等于沒死?既然沒死,我們又為何悲傷?”
裔昭看看小徒弟,淡淡道:“悲傷只是人之常情。人既然知道如何笑,自然也該知道如何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