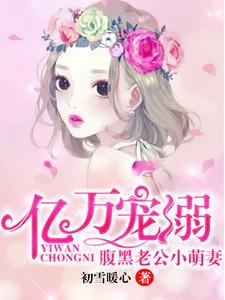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54章 :反攻(下)
第五十三章:反攻(下)
江衡的态度是如此的堅決,李昭旭也不好再多說些什麽.
他十分敬佩着這位知己,這位同志,這位革命伴侶,為對方的思想意志,以及對鬥争,對真理的極度忠誠所深深折服。
“江衡是一個極其偉大的人,她總是這樣上進,這樣忠誠,又是這樣要強,這樣渴望着進步,是一個值得人們向她學習的好同志。”
只是,在李昭旭的心裏,仍然有那麽一塊讓他如何也無法釋懷的心病——他的第一任妻子楊雯雅,和他們那個還不到兩歲的孩子李行端,正是在艱苦鬥争的過程當中犧牲的。
盡管他一直竭力勸說着自己,讓他不要把江衡當成楊雯雅的替代品或是複制品,而是把對方當作一個獨立的人,當成她自己,那段過分慘痛的記憶,依然不肯放過他,長久地萦繞在他的腦海之中,
江衡越來越像楊雯雅了,這是一個不争的事實,
當年,楊雯雅請求和李昭旭,一同投身于反抗蔣經緯的鬥争的時候,她的态度也是這樣的正義凜然堅毅且決絕。
李昭旭有些害怕——一向無所畏懼的他竟然也會害怕,他害怕自己再次痛失革命伴侶,失去那個和他約定相守終生的人
他已經失去過一次了,決不能再失去第二次,他想,
最終,李昭旭還是強迫着自己去克制了這一不該存在的恐懼。
在他看來,一切企圖幹擾自己全身心投入于鬥争事業的東西——盡管它們有時來源于自己的內心深處,都可以被稱之為阻礙發展的“敵人”。
既然是敵人,李昭旭就必然要以強硬的手段去對付它們,和自己做鬥争,這是他的原則
,“在家國大義面前,兒女情長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李昭旭似乎已經做下了最壞的打算,真到了那個迫不得已的時候,他已經準備好和江衡一同犧牲了
“只要能換來國家的安定,換來人民的幸福,換來千百年間無數仁人志士所渴求的自由與平等,即便是飛蛾撲火,摔個粉身碎骨,我也無怨無悔。“
1872年12月10日,李昭旭所率領的“第三部隊”正式向洛香城進軍。
洛香城的社會基礎狀況相當複雜,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治安很差
在洛香城的東部,居住着土生土長的陵山國人,他們的祖輩們在幾千年前就已經定居在這裏,世代繁衍生息,是洛香城中最為安分的群體
居住在城西的,則是永緒國的移民,他們也都是在許多年之前就因為戰亂或是災荒等原因逃離自己國家,形成了一個團結的集體,也還算是安居樂業
只是,那些世代居住在本地的陵山國人,總對這些外來移民有些各種各樣的偏見,他們稱永緒民族為野蠻民族,是社會公序良俗的破壞者,有宗教信仰的陵山國人對他們的偏見更甚,
“念初派”和“熙文派”的教義沖突,讓一些極端虔誠的信徒們對“異教徒”恨之入骨”。
永緒民族雖然算不上那些偏見施加者們所诋毀的那樣野蠻,卻也不是個多麽安分的民族,他們武德充沛,崇尚戰争與力量,總以為可以憑借武力去解決一切問題,就連永緒國“熙文教派”的兩位主神一一百結姬和應離神君所象征的事物都是戰争、破壞與複仇
可以說,在洛香城中,若是有陵山國人和永緒國人起了沖突,十有八九是那個永緒國人先動的手,而且最後打贏的那個,也大概率是永緒國人。
久而久之,這兩個民族之間的關系就變得有些劍拔弩張,互相敵視,彼此嘲諷,矛盾沖突頻繁,
然而,和城南的樊澤族人相比,永緒國人已經算是很安分溫和了。
樊澤族人不是某一個固定國家的國民,他們不平均地分布在各個國家當中,又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間受到各個國家的驅逐,到處流浪,居無定所。
他們遭到如此看似不公的對待,卻幾乎完全是昝由自取。
在兩千多年前,确實有那麽一個叫作大樊國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國民也确實是無惡不做,行徑相當惡劣
他們素質低下,幾乎沒有任何道德底線,他們“擅長”經商”,用假冒僞劣的産品去欺騙外來客商,崇尚“武德”,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偷去搶去掠奪。
他們貪得無厭,到處發動戰争,他們性情兇殘,在屠戮平民的時候連三歲未滿的孩童都不放過,簡直是窮兇極惡、毫無人性。
這樣一個兇惡而貪婪的民族,已經成功引起了各個國家的共同憤慨,讓那些本來各自為營的國君們團結在一起,放下舊有的矛盾,冰釋前嫌,一致對外,戮力對付這個共同的敵人
于是,很快的,在良心未泯者們的協力推動下,大樊國終于被滅國了。
國家沒有了,這些失去家園的樊澤族人只好四處流率逃亡,企圖融入到其他國家的社會中安居生活
然而,這群毫無道德底線的人就像是一幫兇殘的野獸,到了哪個地方,就會攪的那裏雞犬不定,民不聊生,他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為了獲取利益而不擇手段,常常被稱為當地一害。
久而久之,那些真正渴望安居樂業的本國居民乃至于他們的官府甚至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都對這一恐怖的民族惱恨不已。
平民百姓将他們稱作社會的敗類,不肯與他們共同進行生産勞動,甚至連民間繪畫作品裏的妖魔鬼怪們都長着和樊澤族人如出一轍的綠色眼睛,其怨憤與惱恨之甚真真是可見一斑。
官府也将他們視作危害治安的毒瘤,若是樊澤族人犯了罪,對他們的懲罰可是要更重一等,古往今來,幾乎所有能被稱為“明君”的皇帝的“光輝履歷”之中,都必然會存在着“抵禦樊澤族人入侵”這一偉大成就。
“衆生平等,樊澤族人除外。”
“每一個樊澤族人,從生下來,就是有罪的。”
很多以“心懷天下蒼生”著稱的古代先哲,都對樊澤族人産生着較為極端的偏見和仇恨心理,甚至将他們排除在“人”的範籌之外。
“衡,你說他們樊澤族人,真的像人們說的那麽壞嗎”李昭旭早已聽聞過樊澤族人的惡劣名聲,卻因為沒有親眼見過而不敢妄下定論。
“可能吧,雖然那些描述他們罪行的東西可能确實會有些誇張的成分在,那些樊澤族人,他們的信仰從一開始就是有悖于社會公序良俗的,我從前在教會的時候就聽說過。
樊澤族人信奉的那個東西,根本就不能被稱之為‘神”,他就是上古時期一個兇殘好戰的君王,不知怎的就被他們給捧成神了。
要是說我們陵山國的念初教派是統治階級杜撰出來的,他們的“大樊神教”簡直就是杜撰中的杜撰,。
在他們的教義當中,殺人就是做善事,剝奪他人生命就是積累功德,只有做了足夠多的“善事”,他們才有資格成為“神”的子民,得到進入“天堂”的路引。”
“這……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一向見多識廣的李昭旭也不由得被吓了一大跳,“殺人就是做善事”……這分明是邪/教啊!”
“是啊,他們已經信了這個邪教兩千多年了。”
“兩千多年,唉,這兩千多年,得有多少無辜的人死在他們手上!”
“昭旭,我有一句話,不知道當講不當講。”
“請講吧。”
“其實,我覺得這些樊澤族人對社會的危害,以及這個社會對他們的歧視本來就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惡性循環。
樊澤人的宗教信仰固然是錯誤的,有害的,帶有邪/教性質的,應該受到抵制,但他們的族人,尤其是那些年幼的孩子們,他們難道一出生就有宗教信仰嗎事實定然不是如此.
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他們卻根本意識不到這一點,他們把樊澤人當作天生的壞種,戴着有色眼鏡去看待所有的樊澤人,認為他們沒有一個是好人,早晚要危害社會。
在偏見和歧視當中長大,這些樊澤族的孩子們定然會對這個社會産生深深的仇恨,從而将希望寄托于極端的宗教信仰,企圖通過多做“善事”來讓自己取得進入天堂的資格,不斷地做出報複社會的事情。
很多孩子本來立志要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好人,卻被那些強加于自己身上的标簽給壓垮了。
在一次次的碰壁中,他們也逐漸喪失掉了成為好人的信心,他們自暴自棄,自甘堕落,最後真的活成了‘标簽’上面那個十惡不赦的樣子,徹底不可救藥了。
社會越是不願意接納他們,他們就越想要報複這個社會,他們報複社會的手段越是極端,社會就越是排斥他們。
久而久之,一個惡性循環就這樣産生了 ”
“衡,你說的很對。”李昭旭長嘆一口氣,神色凝重地說,“這确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的情況可能要比原來行好一些,畢竟啊,有再經緯那麽一個罪大惡極的人坐在“上面”禍國殃民,還有那麽多恬不知恥的權威派反動分子在那裏狗仗人勢,作威作福。
所有的人民群衆,不分國籍民族,都身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只要他們不是葉澤霖那樣不知變通的頑固分子,估計都會放下成見,一致對外。”
“這些也難說,千百年以來根深蒂固的東西,不是那麽容易就能改過來的,它總需要時間,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唉,但願他們能明白誰才是自己真正的敵人。”
和“桃源”外的大多數城市一樣,洛香城裏的“權威派”走狗們也是相當氣焰嚣張,在城中橫行霸道,燒殺搶掠,逼迫得那些遭受鎮壓的真理主義者們只好退居到主城區以外的鄉鎮地帶,甚至是環境極其惡劣的偏遠山區,
他們保存着自己的實力,厲兵秣馬,枕戈待旦,等候着反攻的時機。
,在城郊一座荒僻貧瘠的小村莊中,李昭旭親切地會見了洛香城“真理協會”的總負責人張銘君同志,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唉,李同志你們應該知道的,自從那個蔣經緯把軍隊調到這邊來,我們同志們的日子就一天苦似一天,城裏到處,都是那夥無惡不作的匪徒,逼得我們一退再退,只能待在這個破地方
我就想着,從前那段激情澎湃的歲月一一也就在不到一年之前,它怎麽就一去不複返了呢
那個時候啊,我們同志們一起包圍警察局,攻與市政府…真是令人懷念啊!
幸好啊,現在你們來了,我們同志們的好日子也跟着一起來了,咱們一起打跑那幫狗腿子,把被他們搶走的東西搶回來!”
“放心吧,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他們現在就是再猖狂,也狂不了多久了!”
李昭旭和張銘君在那裏熱火朝天地讨論着,江衡就開始東張西望了起來。
他們所在的“議事廳”相當簡陋,是由村裏一座荒廢的祠堂改造而成的,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夏天漏雨,冬天漏風。
靠着議事廳的牆根,擺着着幾十張破舊的凳子,有的還是缺胳膊少腿的殘次品,同志們坐在凳子上,圍成一個大圈。
江衡注意到,在那些有權進入“議事廳”的深受張銘信任和器重的同志當中,竟然也有幾個樊澤族人的身影。
那是江衡第一次見過真正的樊澤人,她從前對這一民族的了解,基本只是來自于前人的記述和那些偏見色彩過于濃厚的古代書籍。
事實上,樊澤族人的外貌根本就不像古籍中所記載的那樣兇狠醜惡,“有豺狼虎豹之相”。
相反,他們除了長着綠色的眼睛,五官更加立體之外,和土生土長的陵山國人看上去并沒有太大的區別。
那幾個樊澤人坐在一起,年紀都不過二十多歲,有男有女,個個文質彬彬,有君子風度,顯得知禮且優雅,在他們綠寶石一般的瞳孔之中,閃爍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光芒。
“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團結的人。”張銘君這樣說。
“張同志,你做的很對。”江衡由衷的贊嘆道,“破除民族/歧視是歷史的必然,那些窮兇根惡的權威主義者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也許在過往的千百年中,陵山、永緒、樊澤等各民族的沖突一直在永不停息地發生着,讓一面又一面的圍牆橫亘在人們的四周,阻礙着各民族間的和平溝通與平等交流,讓溝壑愈來愈深,偏見與仇視愈演愈烈,社會治安愈來愈差。
現在,有了蔣經緯這麽一個共同的敵人,有了真理主義這樣一個共同的信仰,多年以來堅冰般固不可徹的隔閡正在逐漸消融,化作一片溫暖而柔和的春水,源源流長,生生不息。
他們似乎不再是一群為自己的利益而相互争搶掠奪的分散個體,而是真正團結在了一起,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一—自願為人民付出一切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