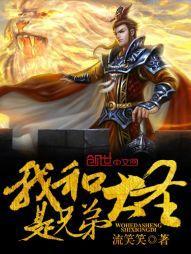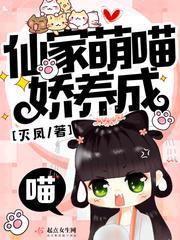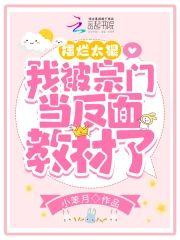第77章 章節
不由己地帶上了祈求的色彩。
孟劍卿嘆口氣:“殺我的任務也敢接,當真是後生可畏啊。也不想想,不管你們成不成功,皇上不殺你們,卞白河也得殺了你們,免得傳出去折損了皇上的威望。我只奇怪,為什麽不派那些約定的信使來行刺,至少不會讓我一見是你們來送信就覺得不對頭。”
他後來才知道,卞白河的确曾經下令叫那些信使來行刺,但是在兩名信使因為不敢領命而被處死之後,其他十人都聞風而逃。
孟劍卿不再看這兩人的臨死情狀,召來衛士,宣稱這兩名信使是假冒的刺客,拖下去立刻處斬;錦盒與腰牌燒毀深埋。
他在受命組建魚腸軍的時候,便與建文帝有過約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現在他不過是暫時停戰休整而已,建文帝就這樣忍耐不住了?還是別人忍耐不住了,一定要将這支他花了一年時間精心訓練的軍隊拿到手,成就自己的功業?
要接管魚腸軍,只殺了他還不行,還得殺了雲燕嬌。
雲燕嬌現在住在廣平府李克己的學政衙門,幫着李克己的夫人用範福運來的糧食施粥赈災。
如果雲燕嬌也遇刺,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保兒已經被石敢峰救出,建文帝感到控制不住他們兩人了,才會做出陣前換将的決定。
魚腸軍是對外的利劍,卞白河是對內的利劍——只可惜他還不是自己的對手。
真想不到,無論什麽樣的帝王,到頭來都少不了錦衣衛,即使不叫錦衣衛這個名字。
孟劍卿忽地一怔。
還有一種可能讓建文帝想要收回魚腸軍:石敢峰營救保兒失敗,保兒現在已經死了,建文帝手中沒有了人質。
他霍地站了起來。
在帳中來回踱了幾步,深吸一口氣,孟劍卿重新鎮定下來。
石敢峰的消息會首先送到雲燕嬌那兒,他還是在這兒等候為好,以免在路上錯過。
Advertisement
他對石敢峰應該有這個信心的;畢竟也打了十幾年的交道了。
雲燕嬌在掌燈時分悄然來到,孟劍卿正在巡視軍營,通報的衛士将雲燕嬌領過來之後便躬身退下。
四下無人,他們站在後營的一片小土坡上,雲燕嬌輕聲說道:“保兒這會兒已經送到我哥哥那裏了。”
他們對視一眼。現在孟劍卿可以毫無牽挂地執掌這支魚腸軍了。
仰望夜空,月寒風冷,鬥轉星移,明白無誤地宣告又一個冬季到來。
與道衍的三月之約将到之時,局勢突然大變。
建文四年正月,燕軍進入山東,繞過守衛嚴密的濟南,破東阿、汶上、鄒縣,直至沛縣、徐州,向南直進。而燕軍已過徐州,山東之軍才反應過來,南下追截。
很顯然,燕王是要放棄在山東、河北一帶的争城逐地,孤軍深入,直取應天。
初聽到這個消息時,孟劍卿覺得很不可理解。
燕王置山東于不顧,孤軍南下,建文帝只需堅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師會合,山東方面則截斷燕軍的補給線和退路,那樣的話,燕王必定腹背受敵、處境極其危險。
以燕王的能征善戰,怎麽會犯這種錯誤?
孟劍臣和公孫義本來已經被調回塞北鎮守,此時又随燕王南下,經過廣平府時兩人笑嘻嘻地跑去給雲燕嬌拜年,還将與他們已經混熟的李漠也帶了去,似乎一點也不擔心後路被切斷的可能。廣平知府明明知道這三個人是燕王愛将,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由着他們來來去去;也是,誰沒有三親六戚來着?他自己的兩個兄弟,一個在南軍,另一個就在燕軍,私下裏也不是不往來的。
孟劍卿握着送上來的這份情報,望着夜空出神。
孟劍臣将李漠帶去見雲燕嬌,想必是別有用意吧。李漠跟着孟劍臣嫂子嫂子地叫,孟劍卿再想對付他的時候,心裏多少會猶豫一下。朱家叔侄這一仗遲早會打完,親友之間,總得留點情面,日後才好相見。
究竟有多少人,也抱着這樣的心思,覺得這是朱家叔侄的家務事,與自己無關?建文帝發出的勤王诏書,又有多少将領是真心奉诏、全力迎戰?
說到底,誰來坐那個位置,與他們有什麽關系呢?他自己不也慢慢生出了這樣的想法嗎?燕王孤軍南下,賭的不就是這一份人心?
一旦燕王兵臨城下,究竟會有多少人倒戈相向?
他想起楓林濃霧中明遠那蛇一般陰冷詭異的聲音。是那個人所制定的方略嗎?道衍與他訂下三月之約,是因為對明遠的運籌帷幄深具信心嗎?
他們都是身在局中的人,也許惟有明遠那樣冷眼看世道的人,才會清醒地看到這一盤争霸天下的棋局的關鍵在哪一處。
那深遠不可測的夜空,深遠不可測的天意,一度離他似乎只隔着一層濃霧,伸手可及。
然而至此,孟劍卿清楚地知道,天意高難問。
功業與榮耀,才智與運道,總輸它,翻雲覆雨手。
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無論它如何翻雲覆雨,他總要牢牢握住手中的刀,握住這柄魚腸劍,才能在這種種風雲變幻中,握住自己的命運。
【十三、】
六月初三,燕軍自瓜洲渡江,鎮江守将降城,燕王率軍直趨金陵,發诏稱“願與天下共治之”,六部官員聞之默然。十三日燕師進抵金陵金川門,守衛金川門的李景隆和谷王為朱棣開門迎降。燕王進入京城,文武百官紛紛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擁戴下即皇帝位,是為明成祖,年號永樂。而燕師入京之際,宮中起火,據傳建文帝在大火中不知去向,但對外只能定稱建文帝葬身于火中。
建文帝這樣的結局,難免讓孟劍卿對寧衡生出種種懷疑。
永樂帝擔心建文舊臣心懷叵測,重立錦衣衛以偵查鎮撫,任命燕王府舊屬紀綱為指揮使,前任錦衣衛千戶高平與孟劍卿為同知。
高平早在靖難之役初起之時便已效忠于燕王,功勞卓著,對他的任命,燕王舊臣并無異議,然而孟劍卿坐觀成敗之後又坐收漁利,難免讓燕王舊臣與建文遺民都極其不滿。
印信是由永樂帝親自交給他們三人的。紀綱與高平退出去之後,孟劍卿被單獨留了下來。
永樂帝打量着垂手肅立在面前的孟劍卿:“沈光禮原來交給你負責的是哪些事情?”
孟劍卿答道:“卑職原來所辦的案子,主要是與各地魔教餘孽和地方叛逆有關;沈大人後來又将講武堂與海上仙山的事情交待給了卑職的,除了這三件事情之外,并無專管。此後因為錦衣衛衙門裁撤,卑職無處交割,所以相關檔案都還收在卑職前幾年所管的庫房中,暫時封存。”
他交割庫房時,給那批檔案加了封條,接管庫房的古百戶還一直沒敢去碰這些檔案。
永樂帝沉吟着,過了片刻才說道:“這三件事,你還是接着管下去。”
沈光禮的安排,必有道理,還是不要輕易變動為好;而且,在他看來,孟劍卿也不是那種公私不分的人。
追查建文帝真正下落的事情,并沒有交給他。孟劍卿的心中,不由覺得略略一松。
永樂帝又道:“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也交給你辦。”
他招一招手,一直低頭守在陰暗處的兩名小內監,快步走了上來。
永樂帝道:“這兩個小內監,人還算機靈,就交給你調教。”
孟劍卿轉眼看那兩名內監,約略猜到,這兩人只怕正是當初從建文帝身邊逃往北平、告知燕王應天城中虛實的那兩名內監。
洪武帝鑒于前代宦官專權之禍,曾在宮中立下鐵牌,不許內監識字參政;建文帝禀承祖訓,對宮中內監,也極是苛刻。不過這兩名從未讀書識字、外貌柔弱的小內監居然有膽色出逃北平、并用應天城防虛實作為投靠燕王的晉身之階,倒真讓孟劍卿暗自吃驚,當真是人不可貌相,在這樣一個世人鄙視的陰暗角落裏,竟然也會生長出如此強悍的心靈。
永樂帝登基以來,論功行賞,連這兩個膽色過人的小內監都沒有落空。
但是孟劍卿心中忽地一怔。
永樂帝要獎賞這兩名小內監,本是情理中事;但為什麽偏偏要選擇這樣一種方式?要知道孟劍卿所走的道路,并非一條康莊大道,很多時候都有性命之險。
他略略側過頭看一看永樂帝,永樂帝在微笑,看不出特別的表情。
然而那微笑是對着那兩名小內監的。
于永樂帝而言,相對于帶着太多洪武朝的印跡、不能自由出入禁宮的錦衣衛,這些效忠于他的、聰明能幹的小內監是更熟悉更親近也更值得信任和重用的人。
孟劍卿已經嗅到了權力更替之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