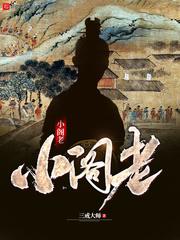第19章 荀诩調職
一直到邁進丞相府之前,荀诩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諸葛丞相居然會忽然召見他這個官秩只有兩百石的小吏,而且是在一場充滿了惡意的評議之後,這讓荀诩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對于蜀漢的官員來說,諸葛丞相是一個需要仰視的存在,他們或多或少對這位蜀漢的實際統治者有一種崇拜心理。諸葛丞相的超凡氣度、才華和人格魅力讓他不僅是一位強勢的領袖,還是一尊神秘的大衆偶像。
荀诩跟随着姜維穿過丞相府的院子,沿着嚴整的桑樹林邊緣朝裏院行進。在軍正司的地下室憋了一整天,荀诩覺得現在丞相府的氣味格外清新;不時還有陣陣夜風吹過桑樹林,将桑樹葉的清香拂入過往行人的鼻子裏。
姜維在一間毫不起眼的屋子前停住了腳步,轉身對荀诩做了個手勢:“荀從事,丞相就在裏面,請進去吧。”
荀诩表情僵硬地看了姜維一眼,不安地深吸了一口氣,推門走了進去。以前他曾經在集會上見過諸葛丞相,不過那都是遠遠觀望,像今天這樣單獨一對一會面還是第一次,他有些緊張。
屋子裏比他想象中要簡樸,屋內的裝潢和荀诩的房間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地上和書架上堆放的絹帛文書與竹卷比靖安司多出數倍,而且毫不淩亂,每一份文件都擺放得十分整齊,一絲不茍。在這一大堆文書之間,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正披着素色袍子批閱着文件,他身旁的燭臺裏滿盈着燭油,說明已經燃燒了很長時間。
“諸葛丞相。”
荀诩屏住呼吸立在門口,恭敬地叫了一聲。老人擡起頭來看看荀诩,将手裏的毛筆擱下,抖抖袍子,和藹地笑道:“呵呵,是孝和呀,進來吧。”
諸葛丞相的聲音很低沉醇厚,象是一位寬厚長者,讓人很容易就産生親切感。荀诩原本緊張的情緒稍微放松了一點,他朝前走了幾步,在諸葛亮下首的一塊絨毯上跪好,雙手抱拳。
“謝丞相。”
“噢,不要叫我丞相,我現在只是右将軍。”諸葛亮伸出一個指頭,半是認真半是玩笑地提醒荀诩。
自從去年第一次北伐失敗以後,諸葛丞相主動上表自貶三級,從丞相降到了右将軍,行丞相事。但蜀漢大部分人包括荀诩都固執地仍舊稱他為“諸葛丞相”,在他們心中,“丞相”這個詞已經從普通稱謂變成了一個特定稱謂,與“諸葛”是牢不可分的。大衆的這個習慣即使是諸葛亮本人也無法改變。
“是,丞相。”
荀诩恭順地低下頭,“諸葛将軍”這四個字他無論如何也叫不出口,實在太別扭了。諸葛亮聽到以後,露出孩子般無奈的表情搖了搖頭。荀诩看到諸葛亮沒什麽架子,覺得自己心情多少有些放松了。
諸葛亮從案下取出一根幹淨的白蠟燭續接到燭臺之上,屋子裏一下子亮堂了不少。他今天剛剛從戰情已經穩定的前線趕回南鄭,只比荀诩到達丞相府的時間早三四個時辰左右。這位風塵仆仆的丞相絲毫不見倦意,他示意荀诩坐近一點,語氣親切,像是在閑聊一樣:“今天的評議,真是辛苦你了。”
荀诩不知道諸葛丞相的用意,于是謹慎地回答:“接受評議是每個官員應盡的義務。”
Advertisement
“呵呵,他們是否對你諸多刁難?”
“有那麽一點吧,我想可能是誤會。”
諸葛丞相“唔”了一聲,習慣性地扇了扇鵝毛扇,隔了一段時間才繼續說道:“這一次的評議,是軍方的強烈請求,靖安司前一段時間的工作引起了軍方的反彈。就我個人而言并不希望輕易對高級官員進行評議,不過律令所在,我亦不能違反。我這一次叫你來,是希望你不要對這種例行程序存有太多芥蒂。”
“多謝丞相關心。”
“你知道,身為領導者,我必須尋求某種程度的內部安定,這種安定往往是需要付出犧牲的。”諸葛丞相的表情很安詳,他瞥了荀诩一眼,“這一次是你很不幸地成為了這種安定的犧牲品,你要怪就怪我吧。”
荀诩沒說話,他對諸葛丞相這樣的态度心存驚疑。這究竟是開誠布公的真誠,還是某種暗示?
“我對此感覺到很抱歉,因為我知道你是無辜的,但我必須批準他們這樣做。”這位蜀漢丞相的聲音轉為低郁,臉上露出歉疚的神情,“你知道,一國的丞相不那麽好當,他沒法讓所有人都滿意,但必須得讓大部分人滿意。”
荀诩看到諸葛亮斑白的兩鬓與清瘦的臉頰,知道他并沒有誇大任何事實。但荀诩沒有想到這一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人物居然會向自己這麽一個小官員道歉,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愣了好半天,他才結結巴巴地表示:“諸葛丞相,我……我确實沒能阻止圖紙的洩露,這是我的失職,沒什麽可辯解的。我會對這一次的失敗負起責任。”
諸葛亮聽到這句話,欣慰地點了點頭:“孝和,事實上我一直在注意着你的調查工作。這一次的失敗是非戰之罪,你的實際能力我很清楚……或者說,我非常贊賞。這也是我把你找來的原因:我希望你能明白,評議對你的結論只是行政結論,并不代表我對你的真實評價。”
“……”荀诩一時不知道該怎麽回答才好,不知道為什麽,他一直以來所承受的壓力與委屈一瞬間從內心底層翻騰出來,然後立刻被融化在一種激動中。
“有人認為你有青銅般的意志,我完全同意。有頭腦、有洞察力、能吃苦、富有激情、寧可死也不放棄,靖安司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
諸葛亮誠懇地說道,同時平靜地注視着荀诩。每一句都是對荀诩心理防線的一次巨大沖擊,他甚至有點想哭。
“希望今天的評議不會動搖你對漢室的信心,漢室的複興仍舊需要你。”
這是今天第三次諸葛亮使用“希望”這個詞,對此荀诩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只是拼命咬住嘴唇不讓自己落淚。真沒出息,他自己在心裏想。
諸葛亮輕輕嘆了一口氣,手中的鵝毛扇仍舊不急不徐地搖動着。他不喜歡這種公開申斥私下安慰的方式,但卻不得不有所妥協。荀诩是這樣,楊儀和魏延也是——為了能讓蜀漢有限的人才發揮最大效能,諸葛亮必須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系與政治蛛網上保持平衡才行。
這時候外面的夜霧少許散去,萬籁俱寂,丞相府周圍一片幽靜,只有打梆巡更的聲音偶爾傳來。荀诩已經有十幾個時辰沒有睡覺了,但他絲毫不覺得困。
這時諸葛丞相覺得氣氛有些沉重,于是便轉換了話題:“為了給軍方一個交代,我會把你暫時調去東吳去擔任駐武昌的情報武官。”諸葛亮捋了捋胡須,對荀诩做了個寬慰的手勢,“你別當這是左遷,就當是休假吧,江東的氣候比起漢中可好太多了。等事情平息以後,我會再把你調回來。”
“東吳啊……我知道了。”
荀诩很高興諸葛亮把話題轉到了實質性的問題上去,否則他不保證自己不會失态地哭出來。即使內涵不同,荀诩也不希望和他的上司楊儀做同樣的事。
“東吳那些人一向都不可靠,最喜歡搞小動作。你去了以後,可以協助管理一下那裏的情報網,不能指望那些自私的家夥主動提供情報給我們。”
“明白。”荀诩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的情緒恢複平靜。
“調令我已經叫伯約去處理了,你最早後天就可以起程。去之前先回成都看望一下你的家人。你兒子多大了?”
“才五歲,名字叫荀正。”
“呵呵,好名字,等這孩子長大,相信已經是太平盛世了。”
“一定會是的。”
“很好。如果沒有其他的事的話,你回去休息吧。”
諸葛丞相揮了揮鵝毛扇,把眼睛合上,示意他可以走了。但是荀诩沒有動,諸葛丞相再度睜開眼睛,略帶驚訝地問道:“孝和,你還有什麽事麽?”
“是這樣,丞相。”荀诩站起身來望望屋外,神情嚴峻地說,“在我離職之前,我必須向您彙報一件事——我已經交代給我的部下了,不過我想還是當面跟您說一下比較好。”
諸葛丞相用雙手擠壓了一下兩邊太陽穴:“哦,你說吧。”
“這一次靖安司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漢中內部有一名高級卧底。”
“哦?”諸葛亮放開雙手,擡起頭來,原本有些倦意的眼睛又恢複了精神。
“敵人對南鄭內部相當熟悉,而且數次洞徹靖安司的行動,這全都是因為那名奸細的緣故。根據五鬥米教徒的供認,那名奸細的代號叫做‘燭龍’。關于他的一些疑點我已經專門撰寫了一份報告,您可以去找靖安司裴緒調閱。”
“就是說,這個叫燭龍的人你現在還不知道具體身份?”
“是的。本來我打算立刻着手調查這個人,但現在不可能了。希望丞相能提高警惕,以免讓他對我國造成更大損失。”
“我果然沒有看錯你,呵呵。”諸葛丞相站起身,滿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知道了,我會派專人去處理這件事,你放心地去吧。”
荀诩這時才得以從近處端詳諸葛丞相,他清瘦的臉上浮現出淡淡的暗灰色,兩個眼袋懸在眼眶之下,眼角的皺紋一直延伸到兩鬓與白發接壤。荀诩能看出在他容光煥發後的疲憊,這個瘦小的身軀承載着整個蜀漢,又怎麽會不疲憊。
“那我告退了,您多注意點身體。”
荀诩在內心嘆息了一聲,深深地施了一禮,然後退出了諸葛丞相的房間。
三月二十七日,前司聞曹靖安司從事荀诩正式調職。
荀诩離開南鄭的當日,正是報捷的漢軍部隊入城之時,所有的人都湧到北門去觀看入城儀式。成蕃負責城防,無法抽身;而狐忠又必須陪同姚柚與馮膺出席,結果到冷冷清清的南門來送荀诩的只有裴緒和阿社爾兩個人。
“荀從事,想不到你竟然就這麽走了。”
裴緒有些難過地說。而阿社爾在一旁憤憤不平地嚷着:“你們中原人真奇怪,肯幹活的人就是這樣的報應嗎?”荀诩伸手截住阿社爾的抱怨,搖頭示意他不要再說了。
“高堂秉現在怎麽樣了?”荀诩問,如果說這一次的行動有什麽和丢失圖紙一樣讓他懊悔的,就是高堂秉的受傷了。
阿社爾抓抓頭皮,回答說:“目前他病情穩定,不過身體還比較虛弱,我們第五臺的人正輪流看護着他。”
“呵呵,我已經離職,現在可沒有第五臺這個編制了。”
“不會不會,我們幾個都一直以在第五臺為榮哩。”阿社爾拍拍胸脯,“要是哪一天您回來靖安司,我們第五臺全體人員一定尾生抱柱恭候大駕。”
旁邊裴緒聽了撲哧一樂,無可奈何地對阿社爾說道:“喂,你先搞清楚尾生抱柱的意思吧,不要亂用成語。”阿社爾趕緊哈哈大笑,說不清楚是解嘲還是掩飾自己的尴尬。荀诩對阿社爾說:“平時多讀讀中原典籍吧,我剩下的書你可以随便拿去看,有什麽不懂的就問裴都尉。”
阿社爾悻悻地捏着兩只大手的指關節,小聲道:“我更願意與高堂兄切磋搏擊之術啊,他的五禽戲我還沒學全呢。”
現場送別的感傷氣氛因這個小插曲而變得淡薄了一些。
“好了,時間差不多該起程了。”荀诩看看天色,将身上的包裹擱到旅車上,“你們兩位就送到這裏吧,靖安司的工作千萬不要松懈。”
“請從事放心。”兩個人異口同聲地答道。
荀诩沖他們抱了抱拳,轉身登上旅車。前面車夫一聲呵斥,鞭子在空中甩出一聲脆響,兩匹馬八足發力,車輪發出咯拉咯拉的聲音,整輛大車緩緩地駛出了南鄭南門。與此同時,在南鄭城的北邊發出一陣喧嚣的歡呼聲,漢軍的第一波騎兵已經披紅挂綠地開進了城中……
荀诩日夜兼程,從漢中南部翻過大巴山,取道嘉陵江南下劍閣,進入蜀中平原,在四月四日的時候抵達了成都,見到了已經闊別兩年多的妻子與兒子。
他在成都陪自己的家人一起享了一段時間的天倫之樂,每天就是和兒子一起讀讀書,釣釣魚;幫妻子修繕一下漏雨的屋頂,還用自己的俸祿給她買了一支銅簪與一套蜀錦裙。這一段時間可以算得上是荀诩擔任靖安司的工作以來難得的空暇時光。有時候,他坐在家中的門檻上望着自己的兒子嬉戲,甚至慵懶地想就這麽過一輩子也不是件壞事。
有一次,他兒子荀正舉着一個風車跑到他面前,抓着他的袖子問道:“爹爹,你去那麽遠的地方,到底是去做什麽呀?”
荀诩先是愣了一下,然後無限慈愛地摸摸荀正的腦袋,回答說:“爹爹是為了漢室的複興。”
“漢室複興?那是什麽?”小孩子似懂非懂。
“唔,就是大家生活變得比以前好了。”
“那,到那時候,爹爹你就能每天都陪我玩了嗎?”
“是呀。”聽到自己父親肯定的回答以後,小孩子歡喜地跑出院子,蹦蹦跳跳地大叫:“娘,娘,我要漢室複興!漢室複興以後爹爹就能天天回家了!”荀诩望着他的背影,唇邊露出一絲微妙的笑意。
五天的假期飛也似的過去,到了四月九日,荀诩不得不告別家人,踏上前往江東之路。
他首先從成都接受了新的官職,一共有兩個,公開身份是撫吳敦睦使張觀手下的主薄;另外一個不公開身份則是司聞曹江東分司的功曹。
蜀漢與吳兩國同為抗禦曹魏的盟友,都在對方首府設立了“敦睦使”這一常設職位,用以維持雙方的日常外交聯系。而敦睦使所在的辦公機構敦睦館則成為雙方外交人員活動的基地。兩國的政策變化以及外交文書都是通過敦睦館來進行傳輸;當有高級別的大臣互訪的時候,敦睦館也做為駐跸之地,比如蜀國丞相府的參軍費祎在出訪東吳的時候就都住在這裏。
而敦睦館的另外一個職能,就是以外交身份做掩護進行情報活動——這可以理解,蜀漢與吳都沒有天真到認為對方會将所有的事都告訴自己,于是他們喜歡自己動手搜集。這就是司聞曹江東分司的工作。
荀诩從成都出發以後,先從陸路趕至江州,然後乘坐“敦睦館”專用的外交木船沿長江一路東進,終于在四月十七日順利抵達了江東都城武昌。
這一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天上無一絲雲彩,江面能見度很高。懸挂着蜀漢旗幟的木船緩緩地駛入了位于武昌西側的牛津。這裏是外交船只專用的港口,所以裏面毫不擁擠;木船輕松地穿過幾道水欄與灘壩,穩穩地停靠在一處板踏前面。
“荀大人,可以下船了。”船夫一邊抓着鎖鏈将鐵錨抛到水下去,一邊沖船艙裏喊道。
很快從船艙裏走出來一位面色蒼白的中年人。荀诩從來沒暈得這麽慘過,雖然他是長沙人,但很小就去了益州,沒什麽機會坐長途的船運。這一次在長江裏幾天幾夜的漂流,讓他差不多吐完了胃裏所有的東西,那滋味簡直就是生不如死。
他晃晃悠悠地邁過踏板,身子一擺,差點掉進水裏,幸虧被迎面來的一個人攙住,這才幸免遇難。
“您就是荀主簿?”
來人問道,他說話帶一點成都口音,荀诩有氣無力地點了點頭。這個人将荀诩小心地攙扶到碼頭上來,荀诩兩腳踏到堅實的土地上,這才多少感覺到有些心安。他擡頭仔細打量來者,這是一位面色白皙的年輕人,兩條細眉平直而淡薄,看上去溫文儒雅;他身上的舊藍布袍已經洗得有些發白,但十分整潔。
“荀主簿,是張觀大人派我過來接您的。”年輕人對荀诩說,他的聲音不高也不低,“我叫郤正,字令先,目前在敦睦館擔書令。”
荀诩想拱手作答,但腦子還是渾渾噩噩的。郤正從懷裏掏出一粒草綠色的小藥丸遞給荀诩,笑着說:“您別擔心,一般第一次坐船來東吳的人都得暈一次船,我給您預備了醒神丸,吃一粒頭就不暈了。”
荀诩接過小藥丸吃下去,藥丸散發着清香,還沒來得及落入胃裏就在喉嚨中直接化掉了。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真的有效,他的頭疼果然減輕了。
“這是吳國的藥坊專門配的,他們的醫生水準不錯。當年如果曹操手裏有這個配方,赤壁之戰就不會輸的這麽慘了……您這邊走,馬車在這裏。”
郤正很健談,從一見面就開始喋喋不休地說起來。荀诩剛吐得稀裏嘩啦,沒力氣跟他聊,只能慢慢朝着車子走去。到了馬車前,郤正架住荀诩肩膀把他擡了上去。這時一名吳國的邊境小吏走了過來,指着荀诩對郤正說:“這位大人還沒登記呢。”
“外交人員,已經知會過你們上司了。”
郤正不耐煩地擺了擺手,潦草地接過毛筆在小吏的竹簡片上簽了字,然後也上了車,讓車夫往武昌城裏開。
一路上郤正興致勃勃地給荀诩介紹着沿途風景與吳國風土人情,荀诩斜靠在馬車上,右手抵住太陽穴,皺着眉頭向兩側勉強望去。與漢中貧瘠荒涼的山地不同,江東這裏一路放眼看過去全是綠色,路旁種植的全是垂柳,正逢四月,春意盎然。遠處水道縱橫,頭戴鬥笠的漁夫撐着一葉扁舟縱橫其間,頗有情趣。就連呼吸入鼻的氣息都濕潤綿軟,比起漢中粗砺幹燥的寒風舒服許多。
大約跑了半個時辰,馬車來到了武昌城前。城門上方的兩個镏金大字反着陽光,格外醒目。守城士兵遠遠看見馬車上高高懸起的蜀漢敦睦使旗號,連忙将城門打開,馬車毫不停頓地穿過城門,駛入城中。這是吳國對敦睦館的特別優待,以此來表示對蜀吳兩國友好關系的重視。
敦睦館位于武昌中央偏北,就在內宮城宣陽門側旁不到兩裏的地方,是一棟相當豪華的宮殿式建築。當年在彜陵之戰以後,諸葛丞相與吳主孫權有意重新結為同盟,于是彼此向對方派出了鄧芝與張溫兩名使節。孫權為了表示誠意,特意在武昌為鄧芝的來訪建了一所新居,後來這座建築就被當做敦睦館來使用,成為蜀人在江東的一處活動基地。
馬車抵達了敦睦館前面停住,荀诩已經恢複了幾分精神。郤正跳下車,指揮幾名仆役把行李搬運下來;荀诩自己扶着把手也下了車,恍惚中看到館中走出幾名身穿雜色錦官服的人。為首之人見到荀诩,立刻熱情地抱拳相迎。
“荀主簿是吧?我是撫吳敦睦使張觀。”
出乎荀诩的預料,張觀看起來年紀并不大,可能比自己還要小上幾歲,白淨圓潤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皺紋,保養得相當好;郤正看上去也頗年輕,不知道是不是這江東氣候養人的關系。
“真是抱歉,失态了。”荀诩不好意思地說道,右手還是頂着太陽穴不敢松開。
“呵呵,我剛到這裏的時候,也是一樣。”張觀寬慰他說,然後指了指旁邊一個穿着黃袍子的長髯男子道:“這一位,是吳國朝廷專門負責與我們敦睦館聯絡的秘府中書郎薛瑩薛大人。”
“薛大人,幸會。”
“荀大人不必多禮,您初來鄙州,風土尚不習慣,應當多休息。我回頭去叫宮裏的太醫給您診治一下。”薛瑩說話聲很細,帶有沛郡的口音,态度和藹。張觀在一旁不禁笑道:“薛大人,我的主簿才來了不到一天,你就急着把他送去醫館啊,這就是東吳待客之道麽。”
“蜀中多疫氣,不清掃一下怎麽行。”薛瑩毫不客氣地回擊,兩個人随即哈哈大笑。
蜀吳兩國使臣素來有相互嘲諷的傳統,張溫訪蜀的時候與秦宓辯論過,張奉使吳的時候與諸葛瑾拿對方的國號開玩笑,鄧芝甚至當面嘲弄過孫權,這也算得上是兩國關系融洽的一個證明。從薛瑩與張觀剛才的對談就可以判斷出,蜀漢與吳關系仍舊處于黃金時代。荀诩想到這裏,心中一寬,沖薛瑩拱了拱手。
這時郤正已經将行李弄妥,張觀見狀對薛瑩說:“我晚上設下宴席為荀主簿接風,薛大人請務必出席呀。”薛瑩搖了搖頭,擡頭看看天色回答說:“最近朝廷裏比較忙,我恐怕是無法出席。我看就等荀主簿身體恢複一點,我再來盡盡地主之誼吧。”
薛瑩說完,走到荀诩前做了個抱歉的手勢,然後告辭離去。張觀、荀诩與郤正看着他離開以後,三個人走進了敦睦館的大門。
館裏一進門是一間寬闊的廳堂,兩邊各立着一只銅制仙鶴香爐,鶴嘴中袅袅地飄着青煙;廳堂擺放着一尊青銅牛方鼎,鼎上方懸挂着用篆書寫的“敦睦和洽”四個字,落款的赫然就是東吳重臣兼書法名家張昭。
仆役們見三名官員已經進來了,于是走過去将大門轟的關上。張觀示意郤正等人離開,然後笑眯眯地對荀诩說:“荀功曹,蜀中一切安好?”
荀诩注意到了這個稱呼的變化。對外他是敦睦館的主簿,而實際上卻是司聞曹江東分司的功曹。張觀這樣稱呼他,意味着接下來就是涉及到情報領域的對話了。張觀在擔任撫吳敦睦使的同時,也是江東分司的從事,算是荀诩的上司。
荀诩簡單地彙報了一下成都和漢中的情況。張觀把右手搭到銅鼎上,忽然饒有興趣地問道。
“您以前是在漢中的靖安司工作吧?”
“正是。”荀诩聽到這個問題一愣,難道張觀也知道了漢中的那件事?
“呵呵,漢中靖安司是對內,而我們敦睦館是對外,兩者工作性質不同,要面對的麻煩也不盡相同。”張觀換了一副嚴肅的表情,“若是粗心大意,可是會引發外交上的大亂子。”
“唔,多謝提醒,我會格外留意的。”
“您也許早就知道,但我還想再強調一下。外交無小事,任何不當舉動都有可能對兩國關系造成損害。”張觀說到這裏,拿眼神瞟了一眼大門,問道:“剛才那位薛大人,你覺得人怎麽樣?”
荀诩想了想,謹慎地回答:“人還不錯,不過我總覺得似乎隔着一層什麽東西。”
“呵呵,不愧是諸葛丞相身邊的人,果然敏銳。”張觀贊許地點了點頭,“薛瑩這個人與我私交很好,是我在東吳最好的朋友,以前我們還是同學。但從外交和情報方面來說,他卻是我們敦睦館最麻煩的敵人,絕不可掉以輕心。”
荀诩點了點頭,外交無私交,這一點原則他是知道的。諸葛丞相有一位親生兄弟諸葛瑾就在東吳任高官,但他們兩個在代表兩國交涉的時候也都是一切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基本,絲毫不攙入兄弟感情因素。
“吳國人比較怪,他和我們、魏人的思維方式與行事風格都不太相同。你既然來這裏從事情報工作,就必須對此有所了解。”張觀說到這裏,忽然感慨道:“時間長了你就知道了,別看蜀、吳一團和氣,實際上武昌地下的情報戰不比漢中或者隴西輕松多少。要知道,有時候盟友比敵人更頭疼。”
“比敵人和盟友還難纏的大概只有自己人了。”
聽到荀诩的話,張觀理解地點了點頭,用手按住上翹的嘴角,笑道:“我大概知道為什麽荀功曹你會被調來江東了。”對此荀诩報以一個苦笑,什麽都沒說。
“至于這邊的基本情況,你可以去找郤正了解,他一直負責日常事務,不過……”張觀看看門口,用手掩在嘴邊低聲道,“這個家夥正義感太強了,有點不知變通,跟情報部門格格不入。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我明白了,我會盡快開始熟悉武昌的情報網絡……”這時荀诩忽然将眉頭擰成一團,表情也變的古怪起來,“只是……”
“只是什麽?”張觀露出好奇的表情。
荀诩慢慢地從肺裏吐出一口飽含江南水氣的氣息,用右手習慣性地捏了捏太陽穴,略帶狼狽地伸出左手:“能再給我一片醒神丸嗎?”
接下來的幾日,荀诩一直在郤正的幫助下對整個吳國國情、政局現狀、經濟政策、軍事體系、民計民生等諸方面進行考察,以試圖對這個位于長江南岸的國家建立起一個初步的印象。與此同時,荀诩還頻繁地出現在各個東吳大臣的宴會之間,與吳人進行交談,了解他們的想法。期間他還受到了孫權的接見,并得到一塊玳瑁殼作為賞賜。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荀诩心中原本抽象的東吳變得豐滿實在起來。他在一封寫給裴緒的信中這樣寫道:“……在經過兩次權力轉移與數十年相對安定的統治以後,江東政權自孫堅時代培養起的那種銳意進取的氣勢已經被和平銷蝕得所剩無幾。歷史原因與地理原因的雙重影響令東吳君臣滋生出一種從外人視角來看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們很驕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以被稱為自大——從吳主到最基層的平民普遍認為任何針對東吳的軍事行動都是不可想象的。他們的想法有其歷史淵源,孫權即位以來曾經遭受過來自曹魏與我國的數次大規模攻擊,但最終都成功地将其順利擊退,這些勝利都是間接或者直接得益于長江。在我與吳人的交談中可以發現,長江作為天塹的存在從地理上與心理上都對他們有着深刻的影響。長江的安全感削弱了他們對外界政治變化的敏感程度,使之對現狀很滿意,并相信這種狀況會一直持續下去。
“諷刺的是,作為一枚銅錢的兩面,這種封閉式的茍安心态不僅帶給吳人優越的安全感,也成為了他們向外發展的障礙。與輝煌的防守戰相比,東吳對外用兵的記錄慘不忍睹,要麽是完全的失敗——比如建安十九年的合肥之戰;要麽是戰略意圖十分混亂——比如建興六年的石亭戰役,從戰術上來說陸遜将軍無懈可擊,但在戰略上東吳除了消耗了大量物資以外,絲毫沒有收益。我想這可能是肇始于東吳将領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東吳的南部疆土與我國南部局勢類似,廣泛分布着松散的蠻族部落,相當一部分東吳将領就是靠鎮壓蠻族來積累資歷。因此東吳的軍事行動呈現出鮮明的讨蠻式特色:缺乏一個大的戰略構想,只确立無數短期戰略目标,而且他們樂此不疲。這與我國明确的戰略目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也正因為如此,東吳君臣很明顯抱有一種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态,這導致武昌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始終缺乏一個明晰的定位。他們将自己視做一個獨立政權,但又向曹魏與我國稱臣,暴露出武昌視自己是一個相對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割據政權的不自信;而每當稱臣這一議題進入到實質操作階段的時候,武昌又立刻退回了自己最初的立場——和他們的軍事行動一樣飄忽不定,沒有指導性的原則。讓所有人,甚至他們自己都無從捉摸。
“這種對外消極對內自大的心态終究讓東吳的小圈子化更加嚴重,在我接觸過的吳國臣子當中,大多數人在表現出對東吳獨立意識的強烈自滿。究竟這會引導我們這個可敬的盟友走向一條什麽樣的軌道,接下來的發展趨勢實在是令人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