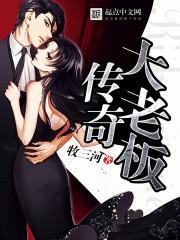第4章 盜亦有道(四)
馬三元和陳大貴兩人再次被關入了柴房,顧岳卻被關進了堂屋東側的小廂房裏,門外與窗外都有人看守。小廂房裏,有桌椅有床帳,牆角熏着纏了菖蒲的艾草,氣味不那麽熏人,青紗帳裏還擱着把大薄扇,顯見得是格外的優待。
顧岳沒說什麽。他現在也知道了,劫匪對着有大筆贖金可拿的肉票,那是真當金娃娃一樣捧着,更何況這張鬥魁似乎還很有抱負、很想拉攏他的樣子。
第二天上午,張鬥魁帶着那個山猴兒,還有另外六名劫匪,找了一杆竹涼轎将顧岳捆上去擡着,押了馬三元和陳大貴,離開了那個小山村,走了好幾十裏的山路,太陽西斜時,轉到了山林更深處的另一個小村裏。村落前的池塘邊,另有一條小路,曲折延伸,消失在山林中,不知通往何方。池塘邊的大柳樹下,坐着個瘦骨伶仃的中年男子,穿一身洗得發白的青布長衫,有一下沒一下地搖着手中的白折扇,帶着一臉高深莫測的微笑看着他們這一行人。
顧岳一見這人,腦子裏便跳出“師爺”二字來。
果然,張鬥魁搶前幾步,拱手道:“莫師爺,辛苦了!”
莫師爺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折扇一收,微笑點頭:“大哥也辛苦了。”
随即看向剛剛從竹涼轎上放下來、但還是戴着鐐铐的顧岳,笑容變得極是和藹可親愛:“這就是顧小哥?坐,坐,坐下來談,咱不跟那幫土匪計較。”
顧岳毫不在意地在他對面的石頭上坐了下來。
張鬥魁嘿嘿笑着,帶了其他人先走了。
顧岳這才發現,原來那莫師爺的身後,老柳樹的粗大斜枝上,還躺着個人,想來是這師爺的保镖之類的人物。
莫師爺敲着折扇,感慨不已地說道:“莫某當年,家破人亡,無路可走之時,受張大哥活命之恩,因此立下誓言,此生一定要為張大哥找一條出路。”
顧岳詫異地打斷了他:“殺人放火受招安?宋江可沒什麽好下場。”
莫師爺噎了一下,很快又呵呵笑道:“這可說不好。放在古時候,走了這條道,能做宋江都很難得了。如今可不一樣,關東那位張大帥,還不是胡子出身?現今可是實打實的東北王,誰又能奈何得了他?”
顧岳抿一抿嘴,一時之間,找不到反駁的話。
莫師爺拈着稀疏幾縷胡須,得意洋洋地說道:“莫某仔細研讀了張大帥的生平,然後為張大哥定了三條錦囊妙計。”
顧岳忽然有些想笑。他發現面前這位莫師爺,做派顯然是學戲臺上的諸葛亮,只是怎麽看怎麽像照虎畫貓。
莫師爺等着顧岳追問是哪三條錦囊妙計,等了好一會,不見顧岳有所反應,只好笑眯眯地自己接了下去:“張大帥當年,雖然投身綠林,但是規矩守得好,口碑好,人緣好,所以才能得了八角臺當地鄉紳與商會的引薦,和官府搭上了線。張大帥又是個識時務的精明人,趁着盛京将軍‘化盜為良’的東風,順水推舟,招兵買馬,作了官軍的管帶,就此平步青雲,一路高升。所以,莫某為張大哥定的三條錦囊妙計,第一條便是:守規矩。守好了規矩,三教九流,才肯放心和你打交道。”
顧岳心中若有所動。
昨晚閑談時,馬三元和陳大貴提起張鬥魁這夥劫匪時,的确也說到了這件事情,正因為此,張鬥魁在大明山周圍三縣的口碑都挺不錯,至少不是最招人恨的那一夥,很多人還覺得,給張鬥魁交買路錢也不壞,總比被其他劫匪搶光甚至殺光要好得多。大明山中和山腳下的那些村子,因為得了張鬥魁的庇護,免了匪害,更是将這夥劫匪看成半個自己人了。
莫師爺瞄着顧岳嘆氣:“也就是顧小哥這樣外鄉回來的人,不知內情,才會和張大哥的手下鬧出誤會來。”
顧岳忍不住捏了捏鐵鏈,提醒自己不要沖口便反駁莫師爺的土匪道理。
他清了清因為久不說話而有些啞的喉嚨:“第二計,又是怎樣?”
莫師爺:“這第二計麽,便是廣結善緣。”
顧岳立刻想起他們改道茶山村的原因,不無鄙夷地打量着莫師爺:“聽說你們前些日子才剛劫了省府某位要員的親戚,招來剿匪的軍隊,所以才離開大明山逃到這邊來?這也叫廣結善緣?”
莫師爺笑得越發得意:“這善緣可不好結,那些貴人,見多識廣,什麽巴結的招數沒見過?因此莫某只好別出心裁、出出奇兵了。俗話說:不打不相識。咱們送了十幾個別處捉來的毛匪外加七箱土鴉片,給奉命進大明山剿匪的那位蔡團長作見面禮,那位蔡團長不費半點力氣便得了軍功和財物,很是領情,願意繼續和咱們打打交道;省府那位原籍衡州的高督察的門庭,有名難進,多少送禮的都被扔出來了?咱們要不是有這個誤劫了高督察親家公的機會,還真摸不着門檻。借了賠罪的理由,咱們送到高府去的禮,雖說并不比別人豐厚,因着讓高督察大有顏面,到底還是送進去了,聽說高督察挺滿意的,覺得咱們識時務會做人,尤其是對高督察很有敬畏之心,賠罪賠得有誠意,可以另眼相看一下。”
顧岳瞠目以對。
這可真是出奇制勝的廣結善緣法。
他覺得自己對面前這個鄉下私塾先生一般毫不起眼的師爺,也應該另眼相看一下。
顧岳想一想,問道:“既然已經和那位蔡團長搭上線了,怎麽還不回大明山?”
莫師爺搖頭嘆氣:“交情不夠啊,再說了,總不能趕在蔡團長退兵之前就回去,要給蔡團長面子不是?”
免得蔡團長對上頭不好交待。
莫師爺繼續搖頭晃腦地說道:“咱們雖然算是搭了幾條線出去,但是要謀出路,還遠遠不夠,也就能說幾句話而已。顧小哥出身不凡,路子廣,有幸相識一場,今後還要麻煩顧小哥多多關照了。”
顧岳看看自己手上與腳上的鐐铐,再看看莫師爺。
有這麽請人關照的嗎?
莫師爺一點也不難為情地嗬嗬笑,又搖起了折扇:“縛虎不得不急,還請顧小哥不要見怪才是。”
顧岳盯了他一會,問道:“要我做什麽?”
莫師爺刷地收了折扇,鄭重一揖:“不敢有勞,只是想請顧小哥寫兩封信。”
兩封信,一封當然是給顧家,另一封自然是送往衡州,衡州駐軍之中,頗有幾位雲南陸軍講武堂畢業的學生。莫師爺大概說了一下意思,這兩封信,當然不是索取贖金,而是客客氣氣地拉一下關系。
顧岳垂下眼簾,許久不曾說話,莫師爺詫異地看着他,不明白這樣兩封信有什麽不好寫的,用得着這樣猶豫嗎?
顧岳似乎是下定了什麽決心,終于開口說道:“莫師爺,衡州那邊的信,需要斟酌。我要知道,那幾位學長是哪一期哪一班畢業,籍貫和從軍經歷,才能決定這封信應該送到誰的手裏,不然的話,恐怕适得其反。”
莫師爺呆了一呆,折扇也忘記搖了:“這個……”
顧岳:“先父生前,是顧品珍将軍的參謀,曾經與顧将軍聯宗,因此我向來稱顧将軍為伯父。去年二月,顧将軍驅逐唐繼堯,就任滇軍總司令,唐繼堯不聽中山先生的勸阻,勾結滇南巨匪吳學顯,卷土重來,顧将軍及其僚屬于今年二月在天生橋戰死,先父也在其中。顧将軍曾任雲南陸軍講武堂監督,唐繼堯也曾任教官,在學生之中,都極有威信。如今唐繼堯重新主政雲南,我的學長們,對此各有意見。所以,莫師爺,你最好先打聽清楚衡州那幾位學長與唐繼堯的關系如
何。”
莫師爺張口結舌。他沒想到,原以為顧岳是個金娃娃,誰知道背後還有這麽大一樁麻煩事。
可唐繼堯就算是雲南王,也是天高皇帝遠,李家橋的顧家可是近在眼前。
這麽一想,莫師爺立刻又堆起了笑容:“據莫某所知,衡州那個師裏面,共有五位顧小哥的學長,哪一期沒能打聽出來,但都是湖南人。鄉裏鄉親的,誰管那雲南都督怎麽樣呢?顧小哥盡可放心。”
莫師爺只差拍着胸脯打包票了。顧岳想了一想,覺得莫師爺這番話挺有道理,但還是仔細問清了那五位學長的籍貫,最後選了一位醴陵籍的程旅長,不只因為這位程旅長現在的職位最高,也因為顧岳恍惚記得,顧品珍和父親都似乎曾經提起過這位程旅長,評價頗佳。
給顧家的信,收信人是顧岳的伯父顧韶韓。顧岳寫得很簡潔,先是說明自己的身世:本名顧仰岳,考入雲南陸軍講堂時,改名顧岳,父名顧品韓,今年初戰死,故而自己獨自返鄉;之後說明,返鄉途中,與大明山頭領張鬥魁有誤會,故而需要顧家派人來,商量如何化幹戈為玉帛。
給那位程旅長的信,顧岳開篇便說明自己是雲南陸軍講武堂第12期丙班的學生,陽縣李家橋人氏,返鄉投靠親族的路上,與張鬥魁的手下發生沖突而失陷于大明山,不打不相識,覺得張鬥魁其人,重諾守信,頗有忠義之心,淪落草莽,很是可惜,如今國家多難,張鬥魁既有報國之心,程學長能否納入麾下?張鬥魁及其屬下二百餘人,既可為國效力,也可保境安民,程學長此舉,于鄉梓之地也功莫大焉。
寫完之後,天已将黑了,莫師爺派人連夜将信送了出去,為免顧家和那位程旅長根本不接信看信,給顧家的信還附了顧韶韓寫給顧岳父親的一封信的信皮,給程旅長的信則附了一本雲南陸軍講武堂的教材《地形學》,算是一個憑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