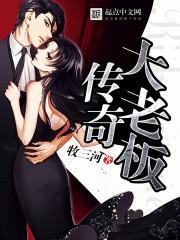第11章 七月流火(一)
作者有話要說: 七月流火,語出《詩經?國內?豳風?七月》,意指大火星西行,天氣轉涼,不過後世多誤以為意指暑熱。《七月》一篇,述寫農家全年勞作不息之艱辛:歲寒至春耕;蠶桑;織布制衣;獵取野獸;收拾屋子過冬;為公家采藏果蔬及造酒,為自家采藏瓜瓠麻子苦菜;鑿冰及年終燕飲;等等。
本篇寫暑日收割,俗稱“農忙”,故以“七月流火”命名。
至于“悠小孩”的風俗,來自于某次短期培訓時和一位滄州學員的聊天。滄州此地,武風隆盛,傳統時代有“镖不喊滄州”之說。流風所及,即便是家庭婦女,也浸潤極深,如魚在水中而不自知,夏夜乘涼,悠小孩習以為常。筆者直接借用過來,特此說明并致謝。
一、
夕陽堪堪落到清江河畔那株兩三人都合抱不過來的老柏樹的樹梢上,暑氣遠未散盡,岸邊的草地上鋪滿了短褂褲衩,一群半大小子脫得精光,在樹蔭下那道水流平緩的河灣裏撲騰,也有水性好膽子大的,游到了河道中央,更有一二佼佼者,迎着急流在兩岸之間游了個來回,得意洋洋地向同伴炫耀,嘻笑打鬧之聲,遠遠地隔了竹林也聽得清楚。
何思慎帶着顧岳從竹林中穿出來,走不上幾十步,便到了江邊。五六個孩童,各騎着自家的水牛,從他們前頭經過,往江中去洗澡,一邊走一邊好奇地轉過頭來打量一襲長衫的何思慎,還有明顯不像當地人的顧岳。一個年紀稍大的很快認出了何思慎,吓得趕緊從牛背上滑下來,慌慌張張地鞠了一躬,大聲喊道:“何校長好!”
何思慎當年十六歲便以陽縣頭名考中了秀才,整個衡州都轟動了好些時日,都說若不是廢科舉了,這何家老三說不定可以一路考上去,中狀元都是不好說的事情,柏樹灣周圍幾個村都引以為榮。科舉一廢,何思慎腦子活絡,知道世道變了,便跑到日本去留學,學的是師範,回來之後在柏樹灣辦了個新式小學堂,前些年又做了陽縣高等小學堂的校長,陽縣人都尊稱他一聲“何校長”。這可是陽縣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柏樹灣的人,一提到“何校長”,也覺得自己倍有臉面。
那最先認出何思慎的孩童,去年剛剛入學啓蒙,年初随着家中長輩給何思慎拜過年――這也是柏樹灣近些年興起的風俗了,但凡上柏樹灣小學堂念書的學生,總得到何家拜個年,以示不忘本源之意。
其他幾名孩童也跟着慌亂地跳下牛背來鞠躬問好。何思慎微笑着揮手示意他們自去玩去,看他們急急走遠,才轉向顧岳道:“這幾個都是清江河這邊杉山鋪那個村子的。”
顧岳有些驚異:“姑父都認得出來?”
何思慎笑道:“其實我只認得去年上柏樹灣小學堂念書的那一個,不過另幾個應該都是一個村子的。”他略略解釋了一下那個拜年的新風俗。顧岳若有所悟,不覺有些感慨地道:“我們一位教官說,法國有位不世出的名将叫做拿破侖,初初帶兵的時候,兩萬人的軍隊,他不須幾日,便能叫得出其中數千人的姓名,所以能夠讓将士在短短時間裏便聽命效死。姑父是不是也認得出你所有的學生?”
何思慎笑而不語。
說話之間已經到了河堤上,放眼望去,沿着堤岸往上游走一裏來遠,河對面便是那株老柏樹,柏樹灣之名,便因河灣畔這株據說已有八百歲的老柏樹而來,再往上游走半裏許,河道狹窄處建了一座石橋,這便是李姓一族當年捐建的那座橋了,李家橋之名也因此而來;過橋之後,不過一二裏,一片起伏平緩的小山坡上,圍了兩人多高的石牆,石牆外緊挨大門的路邊,有一個數畝大的池塘,塘邊綠樹成蔭,一大群白鵝啞啞嘶叫着在塘中游來游去;石牆內房屋錯落,多是瓦房而非茅屋,略略估算一下,足有二三百棟,這樣的規模,說是村落,其實比起顧岳途中所見的許多大鎮來,也不遑多讓。山坡北面,隔了大片稻田,不過幾裏路開外,已是巍峨群山,想來便是大明山的支脈,清江河的一條支流,當地人叫做小清江的,自群山之中蜿蜒流出,圍着那片山坡繞了好幾個彎,才在石橋上游不遠處曲折彙入清江河。
以顧岳的眼光來看,這片村落,背山臨水,居高臨下,控扼着整個開闊平坦的河谷,當真是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即便是池塘中那群一派田園風光的白鵝,也莫名地讓顧岳想到,據說家鵝比狗還要警覺,是天生的哨兵,而且成群結隊游于水中,偷襲者想摸哨都沒法摸。
夕陽之中,河堤上長衫飄飄的何思慎極是惹眼,河中那群戲水的少年,嘻笑聲不知不覺便停了下來,一個個光溜溜的,不敢站起身來鞠躬,只伏在水中大聲喊“何校長好!”大約自己也覺得尴尬好笑,參差不齊地喊完之後,又笑嘻嘻地鑽進水裏游到稍遠處的小叉灣裏,半藏半露地探着頭向這邊看。
何思慎眼力很好,一眼掃過去,便提了一個人出來:“李長庚,過來!”
那群少年哈哈笑着,将剛剛從河對岸游回來的一個同伴推了出來,又有人伸手從河岸上的草地上勾了條褲衩下來,那少年爬上這邊堤岸的同時,已經快手快腳地套上褲衩,一身濕淋淋地站到了何思慎和顧岳面前。
何思慎道:“這是你大姑姑家裏的老三李長庚,這是你小舅舅的獨子顧仰岳,比你小五個月。”
這幾句話卻是分別對兩個人說的。
顧岳自覺地叫了一聲“長庚表哥”,李長庚很自然地回了一聲“仰岳表弟”,顧岳有心想糾正一下,自己的名字其實是“顧岳”,但是心念只動了一動,便壓了回去。
在路上何思慎已經明白告訴他:回到李家橋,他就是顧仰岳;要做顧岳,且待他日。
李長庚手長腳長,看身量已是個魁梧大人,面相上卻還帶着幾分憨氣,抓抓頭,笑着說道:“大舅舅家裏明天清早開鐮割禾,從外頭請了十個幫工,都住在家裏,今晚肯定是收拾不出地方給仰岳表弟住了,表弟今晚就住我家吧。”
顧岳沒太聽明白這個安排,想着自己應該住伯父家,沒床鋪的話,在地上攤個草席便可以了,不必要去麻煩姑父家,這樣想着,便說了出來:“我打地鋪沒關系,我們操練和行軍時還總在野地裏睡。”
李長庚認真地道:“我們這兒不興打地鋪。”
顧岳茫然不解。何思慎笑着解釋道,李家橋地近清江河,地氣濕熱,又多蛇蟲,因此哪怕三伏天,也不興席地而卧,總要架塊床板、挂頂蚊帳,以免暑氣入體又或者招惹蛇蟲。顧岳的父親,堂兄弟族兄弟衆多,不過親兄弟也就他和長兄顧韶韓兩人,再有兩個姐姐,小的一個嫁了何思慎,大的一個嫁到了同村的李家。顧韶韓家裏既然不好收拾住不下,顧岳自然應該住到李長庚家裏去――不跟着何思慎一道住,卻是因為,何思慎當初辦柏樹灣小學堂的時候,為了籌款,将家裏分給他的房子和地都賣了,帶着家小住到了學堂裏,後來就任陽縣高等小學堂的校長,便搬家到了縣裏,李家橋這邊,若無要事,只在過年時回來祭祖拜年,借住在何思慎的大哥家中,倒不好叫顧岳現放着李長庚家不住,卻跟着何思慎一道去何家大伯那兒借居。
顧岳聽着何思慎耐心仔細的解釋,心裏難免有些別扭。這是他的故鄉,但許多人事都需要有人為他解說。
經過石橋時,李長庚指着上游支流彙入清江河處的那片三角地,說道:“仰岳,那塊地就是你大伯家裏的,河泥淤積出來的,肥得很,又向陽又臨水,每年都要比我們村其他地塊早熟好幾天。”
果然,那塊三角地中的稻谷已經金黃燦爛,周邊的田地裏,稻谷卻還帶着點青綠。
李長庚又道:“明天開鐮,我們家也要去幫工。”他忽然遲疑了一下,“仰岳你會割禾吧?”
農家七月無閑人,何況還是個無病無痛的精壯半大小子。
顧岳心裏“咯登”了一下。他還從來沒有下過地,一時間不知道如何回答。
何思慎會意地笑了起來,拍拍他肩膀:“不要緊,學一學就會了。”
李長庚立刻拍胸脯打包票:“我一定快快教會仰岳表弟!仰岳表弟你只管放心吧!”
顧岳僵着臉,應也不是,不應也不是。
李長庚的态度太過自然,仿佛顧岳一直生長在這裏,中間出去讀了幾年書,現在只不過是重回故地,種種人事,随手撿起來便是,不須刻意經營,已然熟悉親切。
還有,明天開鐮割禾……顧岳覺得自己肯定要讓人看笑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