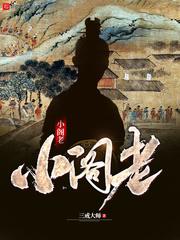第17章 (1)
北京城裏這幾天人心惶惶,一陣說南方軍已經打到滄州了,一陣說東北又運過來幾千名奉天兵和幾車皮的軍火,甚至還有傳聞說在天津寓居的溥儀請來洋人,又組了個八國聯軍在天津衛登陸,氣勢洶洶奔北京來複辟帝制——總之什麽離譜的說法兒都有,加上那一陣皇煞風刮得邪性,老百姓們都心驚膽戰。這個惡五月有點惡得過火了。
方老山回城時天色已經擦黑,他沒走大路,沿着胡同邊踅着穿行,看見人影就趕緊矮身縮在牆角,生怕碰見熟人和奉天兵。熟人怕借,奉天兵怕搶,這年頭兒還有誰的命比自個兒的更重要?
方老山是個老北京,這些年見識過不少戰亂,經驗豐富,知道一旦打起仗來,最怕的就是饑荒。所以他這次一聽又要打仗,連忙出城,從附近農家弄了兩條大蘿蔔、一捆青菜,還有兩條比指頭粗不了多少的河魚,拿麻繩串起來拎在手裏。真要打仗封城,這點東西勉強夠一家人撐幾天了,方老山心裏這才多少踏實了點。
眼看快到家門口了,方老山忽然看到前頭似乎有個人影,晃晃悠悠往這邊走過來,走路姿勢忽高忽低,特怪異。方老山一驚,心想不是碰見胡同兒串子了吧?老北京傳說,死在外頭的人想回家,可人已沒了記性,只能在胡同裏穿來穿去。行人若是碰到胡同兒串子,不能跟它說話,低頭過去就成,不然它跟你回去,那就釀成大禍了。
方老山也趕緊把腦袋垂下來,屏住呼吸往前走。兩人很快走了個對臉兒,對方忽然發出一聲低吼,伸開胳膊,朝着方老山抱過來,吓得方老山扔下手裏糧食,轉身就跑,這人在後面追了幾步,“噗通”一聲栽倒在地。
方老山回過頭來,看見他摔倒在地沒動靜了,才壯着膽子回來。他蹲下身子,伸手去摸了一下脖頸子,還帶着熱乎氣,才确信這不是鬼,是個活生生的人。他見這人沒什麽聲息,不由升起一股貪念,如果把這身衣服剝了賣到成衣鋪裏去,也能換點酒錢。
方老山猶豫了一下,正要伸手過去,這人卻突然把腦袋擡起來,吓得他哎喲媽呀一屁股坐到地上,硌得生疼。
這人是個年輕後生,只是面如死灰,神色枯敗。他喘息着張嘴道:“老伯……把這個送到清華學校,給許一城。”方老山看到他手裏是一張薄薄的白紙,上頭還沾着鮮血,不敢去接。那人流露出懇求的神色:“有重謝,重謝……”他身子一掙,似乎要強調。方老山趕緊說老弟我給你叫醫生去吧,那人說:“一定要送到,不然來不……”話沒說完,他支持不住,再次倒在地上,沒了聲息。
忽然胡同那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人數不少。方老山一激靈跳起來,顧不得多想,一把将紙從他手裏扯出來,朝自己家門跑去。他急急忙忙開了鎖鑽進去,輕輕關上門板,從門縫處偷偷朝外望去。
幾個人影從遠處快步走過來,看穿着都是奉天兵的模樣,但動作麻利得多。其中一人掏出手電照了一遍屍身,又朝附近照來照去。這人身材高長,殺氣騰騰,方老山吓得矮了半截身子,大氣都不敢喘。那人蹲下身子,在屍身上搜檢一番,起身跟周圍人輕聲吩咐了幾句——用的居然還不是中文——然後把屍體擡起來,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方老山覺得脊梁骨都是冷汗,他低頭一看,才發覺自己剛才扯得太快,那白紙居然只剩下半張,吓了一跳。他還指望拿這個去清華換報酬呢,趕緊展開看看,這半張紙是張信箋,上頭是一個手寫的潦草“陵”字,字旁邊拍了一個血紅色的手掌印,五指痕跡清晰可見。這紙的下半截應該還有字,估計被剛才那些人帶走了。
方老山十分懊惱,早知道就不用使那麽大的勁兒了,也不知這半張紙頭能不能換錢。他輾轉反側了一宿,越想越可惜,到了第二天中午,他還是決定去清華學校碰碰運氣。
北京城內外風雨飄搖,此時的清華校園裏也是一片混亂。幾個懶散的士兵靠在校門口的沙包前,無精打采地扔着骰子。幾個長衫男生打起白色橫幅,慷慨激昂地向圍觀的人訴說着什麽革命道理;一群女學生則手裏捧着書行色匆匆;一地的碎紙和小旗,無人打掃。
方老山問了一圈,總算打聽清楚許一城是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院有自己的專屬建築,在未名湖以東,是一棟西式風格的二層小白樓。廊下圍着一圈灌木叢和各色花草,牆上攀着歪歪斜斜的莳蘿與爬山虎,那是前幾日大風留下的痕跡。
他受人指點,找到底樓的一間辦公室,一進門就吓了一跳。屋子正面牆上貼着一張人體解剖圖,桌子上還擱着一個骷髅頭。四周堆滿了石片、陶器、照片和各種洋文書籍,還擱着有不少奇怪的工具。一個人正伏在案前工作,聽到他進來,擡起頭來,和顏悅色地問他有什麽事。
“我找許先生、許一城。”方老山點頭哈腰。那人說我就是。方老山連忙說有人托我給你送一封信。許一城放下鋼筆,投來疑惑的眼神。方老山也不客氣,把昨晚遭遇講給許一城聽。
Advertisement
許一城聽完以後,眉頭微皺,問他那個人是什麽相貌。方老山說:“瓜子臉,高鼻梁,兩個眼睛分得很開——哦,對了,額頭特別寬。”許一城眼神一動,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照片,問方老山認不認得出來。方老山一看照片,是張合影,上頭有十來個人。他找了一圈,指着其中一人道:“對,對,就是這個人。”許一城閉上眼睛,輕輕吸了一口氣,端着茶杯的手在微微顫動,良久,才艱難地開口說道:“東西呢?”
方老山從懷裏把那半張疊好的白紙拿出來,卻沒遞過去。許一城知道他的意思,扔給他一把銅元。方老山眉眼喜笑地把銅元接過去,數了數,看了看許一城臉色,趕緊又裝出沉痛神情,把信紙恭恭敬敬擱到桌子上。
許一城把信紙展開一看,不動聲色地問道:“他臨死前還說了什麽?”“沒有。”方老山回答。許一城又扔過去幾枚銅子兒,方老山接了錢,這才開口道:“他說一定給你送到,不然來不及。”許一城又問:“來不及什麽?”方老山愁眉苦臉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許一城眼神一凝,方老山吓得連連擺手:“我是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哇,他說到一半就斷氣了……”他見許一城表情晦暗,又關切地湊過去,“他是您朋友?”許一城輕輕點點頭。
方老山不吭聲了,他默默地把錢收起來,準備告辭。許一城忽然開口道:“能不能請你準備香燭,在他死的地方幫我燒點紙錢?”方老山連聲答應下來,他現在只想盡快離開,不太敢去直視許一城的眼神。等走出研究院的大門口,他才松了一口氣,攤開手掌數了數錢,眉開眼笑地朝家走去。
方老山不知道,許一城始終在他背後注視着他。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未名湖的小路盡頭,許一城這才收回視線,回到辦公室。他緩緩拉開一把木椅坐下去,半張信箋捏在手裏,心中如同沸山煮海。
死者叫陳維禮,是他的至交好友。兩人都對考古有興趣,志同道合,無話不說。後來陳維禮去了日本留學,兩人已經多年不曾相見。許一城萬萬沒想到,當年的碼頭告別,竟成了永別。
許一城閉上眼睛,好友的音容笑貌,宛然就在眼前……陳維禮是個充滿理想和幹勁兒的年輕人,一心要開創中國考古事業。他曾經對許一城說,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效仿大英博物館建起一座中國自己的博物館,将古董商手裏的寶貝都放進裏面去,留給後世子孫看——放在故宮就很好!談起這個夢想的時候,陳維禮雙目閃閃發亮,像是父親在談論自己最自豪的孩子一樣。
可惜這個夢想,陳維禮再也看不到實現之日了。他的生命,在狹窄的北京城胡同深處,被永遠定格在了二十九歲。
最初的悲傷過去之後,許一城的心中,慢慢浮上無窮的疑惑。
陳維禮究竟什麽時候回北京的?為什麽不主動聯系他?更重要的是,從方老山的描述來看,陳維禮應該是被人追殺滅口的。為什麽他會被追殺?殺他的是誰?為什麽?
許一城重新睜開雙眼,仰起頭來,試圖透過天花板去想象陳維禮所面臨的危險境地。他在生命最後的時刻沒有為自己求救,而是設法把這張紙送到數年未曾謀面的好友手裏,發出最後一聲呼喊:來不及了——他知道,以許一城的性情,一定不會置之不理,一定會竭盡所能把這件“來不及”的事替他辦完。
這是最深沉的信賴,也是最沉重的囑托。那張紙上到底寫的什麽事情,讓陳維禮連自己的生死都不顧,也要把它送出來?直覺告訴許一城,此事絕不會是什麽私人恩怨。以陳維禮的性情,這一定是件大事,且是件極兇險的大事。
許一城捏着這半張紙,如逾千斤,不禁喃喃自語道:“維禮啊維禮,你到底遭遇了什麽?”
許一城的指尖輕輕摩挲着紙面。如果當時方老山把整張紙都取回來的話,說不定會有更多線索。現在只留下一個沒頭沒腦的“陵”字和五個指頭印,別說替陳維禮完成遺願,就連搞清楚發生什麽事情都很難。
忽然,許一城的指頭停住了,雙眉微微一動。
這是一種厚信箋,紙質綿厚密實,表面光亮,适合鋼筆書寫,一摸就知道是洋貨。許一城的指頭很敏感,很快就摸到紙上有一片凹凸不平的地方,似乎是上一頁紙寫字留下的壓痕。
許一城推開窗子,把這半張紙對準太陽,眯起眼睛仔細觀察了一陣。他又從筆筒裏取下一根鉛筆,拿刀削尖,輕輕地用側鋒刮着紙面。很快,一個奇妙的标記出現在許一城的眼前,風、土兩個漢字上下摞在一起,“風”字的外圍和“土”字的最底一橫稍微做了彎曲變形,恰好構成一個圓圈。
風土?
許一城盯着這一個标記看了一陣,再拿起鉛筆,繼續刮起來。很快在這個标記旁邊,鉛筆刮出來一片淺灰色的圖,線條分明,應該是一把中國寶劍的輪廓素描,不過只有從劍頭到劍颚的一半——其他部分估計在失落的另外半張紙上。
這半把寶劍的造型也頗有些奇特,似乎被畫過兩遍,可以勉強看到一截筆直的劍身和一截略顯彎曲的劍身,兩段劍身交疊在一起,好像重影一般。似乎畫手拿不定主意,先畫了一遍直身,又改成彎身。
再仔細一看,上頭似乎還有龍紋。可惜這片痕跡實在不重,看不出更多細節。
血手印、“陵”字、風土印記和寶劍素描,這幾者之間到底有什麽聯系呢?許一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這裏最容易追查的,應該是風土印記。這個标志一看就是經過專門的美術和幾何設計,應該是某一個機構的專用公章,曾經在這張信箋的上一頁用過印,用力稍微大了點,紙又很軟,所以在下一頁留下一道輕輕的痕跡。如果能找到這個印記的來歷,那麽陳維禮書寫信箋的地點,也就呼之欲出了。
許一城取來一張北京地圖,以陳維禮死去的胡同為圓心,用圓規劃了一個圓。方老山曾經說過,陳維禮臉色很差,說明以他的身體狀況,跑不了多遠,活動範圍只可能在這個圓圈之內。而且這種信箋紙相當高級,國內用得起的人不多,一般只有使館、洋行之類的地方才會用,這就進一步縮小了搜索的範圍。
做完這些工作,許一城拉開抽屜,将那一套海底針取出來。這是沈默送給他的,用來酬謝吳郁文的事,算是相當重的獎勵了——微妙而有意思的是,沈默寧可私下裏把這套家寶送他,也不肯當着族人的面公開褒獎,個中意味,難以言明。
許一城從海底針裏抽出一柄小鏟,在一塊木牌上刻上“陳公維禮之位”幾個字,然後恭敬地擺在桌前。他點起兩炷香,直起身子,兩個大拇指交抵,八指交攏,拜了三拜,手背翻轉,再拜三次。
這是江湖上的規矩,叫作生死拜,也叫托孤拜,相傳是諸葛亮在白帝城傳下來的。在墳前做如此祭拜,表示生者願不惜一切代價完成死者遺願,托孤一諾,九死不悔,手背翻轉,以示不負所托之意。說來也怪,許一城剛一拜完,窗外一陣大風吹進屋子,霎時四處被吹得嘩嘩響動。那木牌晃了幾晃,居然面朝着許一城倒了下來。
許一城嘴唇一顫,連忙伸手扶起木牌,雙目含悲,卻不見半點淚光:“維禮,我不知你因何而死,也不知道殺死你的是誰。但你臨終前來找我,自然有你的道理。人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待之——為兄這兩行清淚,待得為你昭雪之時,再灑不遲!”
風說停就停了,屋中立時一片寂靜。
陳維禮死去的地點是在西城大麻線胡同附近,前後都是敞亮大街,附近都是繁華之地。商旅雲集,南北商鋪連成一大片,就連洋行也有那麽十幾家,其他各色娛樂銷金場所更是鱗次栉比。不過最近因為戰亂的緣故,好些鋪子都緊鎖大門、上起門板,生怕被敗兵波及了,放眼望去十分蕭條。
許一城離開清華,以大麻線胡同為圓心,沿着劃定的範圍走了幾圈,一無所獲,別說那個标記,就連帶“風土”二字的招牌都沒一個。那些洋行他都一一拜訪過了,也沒什麽可疑之處。許一城拿着這圖形問了幾個路人,都說沒見過。
五月天氣說熱就熱,許一城走得有些乏了,想找個茶館歇歇腳,喝幾口茶。他一擡頭,忽然把眼睛眯了起來。原來不知不覺,他竟走到了大華飯店。這大華飯店在四九城很有名氣,是專門給洋人住的高級旅館,裝潢設施據說請的都是紐約來的設計師,連“大華飯店”四字都是用霓虹燈勾出來的,一到晚上花花綠綠的格外耀眼,是遠近一景。
許一城看到有幾個穿西裝的東洋人走出飯店大門,沖送別的人連連鞠躬——不用說,這一定是日本人。看到他們,許一城心中不由得升起一陣懷疑。陳維禮之死,許一城一直疑心與日本有關系。那印記是“風土”二字,而國外仍舊使用漢字的,只有日本一國。何況當初陳維禮出國,正是在早稻田大學就讀考古系。
這附近沒有其他日本機構或商鋪,如果說能和日本人扯上什麽關系的話,那就只可能是住在這家大華飯店的客人了。
他信步走進旅店,徑直來到櫃臺前。接待見他西裝革履,氣質不凡,趕緊過來招呼。許一城懶得跟他廢話,把一枚銅元“啪”地扣在臺面上,用手攏住:“你們這裏,最近住了什麽日本客人?”
接待大概早就見慣了這種場面,笑眯眯地把賬本往上一搭,另外一只手在賬本下把銅洋迅速摳走:“最近政局不太穩當,來的人少。現在住的只有一個日本考察團,東京帝國大學的,個個戴着厚底眼鏡。”
“哦?”許一城眉頭一皺,“他們是來做什麽的?”
接待沒回答,只是把賬本磕了磕臺面。許一城又遞過去一枚銅元,他才說道:“聽說是來中國考察啥古跡的,我幫他們扛過行李箱,中間掉地上一次,裏頭裝的全是地圖。”他一指,“喏,那位就是團裏頭的教授。”
許一城順着他的視線望去。大華飯店一層是個咖啡廳,裏頭靠窗的沙發上坐着一個穿和服的日本人,對面坐了個戴瓜皮帽的中國人,唾沫橫飛地跟他白乎着。
許一城悄悄走過去,看到原來兩人玩賞的是一把竹杖。這把竹杖高約七十公分,粗細恰好一掌可握,竹節稀疏,上面還綴着如同淚痕一樣的紫斑。最奇的是,每一節上的竹面有微微凸起,如同佛面一樣。一根竹杖分了五節,就是五個佛面,倒真是件精致的奇物。
那位日本人頭很大,脖子卻很纖細,寬闊光滑的額頭向前凸起,發際線卻拼命靠後,讓他看起來總是一副把身子前探的好奇姿态。他雙手捧着那把竹杖,厚厚的鏡片後眼神略顯呆滞,不知是被震驚,還是心存疑慮。
那個中國人說:“您盡可放心,我騙誰也不敢騙大日本帝國的教授呀。這湘妃佛面竹杖,可真是一件稀罕物。您看見那上頭的紫暈了沒?那是極品湘妃淚竹,幾百年也長不出一根來……”那人正說到興頭,聽到旁邊傳來一聲嗤笑。他側臉看到許一城在旁邊似笑非笑,大為不滿,揮了揮手說:“快走開!”
許一城沒理他,對那日本教授道:“這位先生,你可要上當了。”那人大怒:“你扯啥呢扯?”許一城也不客氣,拿起那杖,拿指頭點了點竹面上的紫暈淚痕道:“這淚斑可不是長出來的,是點出來的。新竹剛生時點了幾處苔錢封固,長成以後用草穰洗下苔錢,斑點就出來了,是不是?”
那人一時語塞,嘴裏卻不肯服輸。許一城道:“真正的淚痕,深入竹質;點出來的淚痕,浮于竹皮。咱們打個賭,我把這竹杖撅斷了,看它的斷面有沒有紫暈。如果是真的,我照價賠償;如果是假的,咱們去日本大使館說個明白,如何?”
那人連忙轉臉對那日本教授道:“您可別聽這小子胡說,他懂個屁,我可是出身五脈。五脈您聽過嗎?明眼梅花……”
那位教授擡起手,把竹杖雙手奉還,用生硬的中文道:“佛面杖,俗稱定光佛杖,宋代産于龍岩、永定、武平等地。蘇轼曾經送過一杖給羅浮長老,留下兩句詩,‘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
龍岩、永定、武平在福建,自然跟湖南的湘妃竹沒什麽關系,這位教授言辭暧昧不願直言拒絕,就背誦佛面杖的典故,等于是委婉地回絕了。許一城和那男子都沒料到,這個日本人漢學功底如此深厚。他雖沒有鑒別淚痕的古董知識,但靠着精熟典籍,從另一個角度點出了破綻。
那男子面色一紅,二話不說,拿起竹杖轉身就走。臨走之前,他還狠狠瞪了許一城一眼,呸了一聲:“不幫中國人,反倒幫日本人,狗漢奸!”許一城一時有些哭笑不得,不過也沒去追究。這種騙子太常見了,專門在高級旅店附近混,拿假貨哄騙外國人。
日本教授起身鞠躬致謝:“我正發愁如何讓他離開,您能來幫忙真是太好了。”
許一城心想這個家夥倒真是個老實人,對騙子也這麽彬彬有禮。他擺手笑道:“沒什麽,我這個人見不得假物,所以一時沒忍住,不知有沒有打擾到您。”日本教授雙手遞上一張名片,名片頗為樸素,上面只有四個字:“木戶有三”。許一城把名片收好,雙手抱拳:“不好意思,我沒名片。我叫許一城,在清華學校讀考古。”
聽到考古二字,木戶有三的眼神倏然亮了起來。他熱情地請許一城在對面坐下,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起考古的事情來。原來木戶有三是東京帝國大學的考古學專業教授,這次和其他幾名學者受邀加入支那風土考察團,準備考察中國西北一帶的古代遺跡,三月下旬剛到北京。因為政局動蕩的緣故,暫時還沒出發。
一聽到“風土”二字,許一城心中一跳,連忙拿出謄畫的那個風土标記,木戶教授一看就點頭:“沒錯,這是支那風土研究會的标記。”
“那是什麽團體?”
“是一個基金會,和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東亞考古學會、東亞文化協會差不多,致力于挖掘、保存和研究東亞地區歷史的學術團體。我們這次考察活動能夠成行,全靠了他們的好意資助。”
這就對了,許一城心想。陳維禮使用的信紙,是這個考察團從日本帶來的,上面留下的印痕,則是贊助者支那風土研究會。
如此看來,陳維禮的死,以及他舍命要傳遞出的信息,恐怕和這個考察團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
許一城表面上沒說什麽,心中一陣冷笑。日本人從甲午開始,就垂涎着中國的文化。這些年來,打着考古旗號來中國的日本人如過江之鲫,不是盜掘墳墓遺址就是搜購古籍文物,幾乎都成了公開的秘密。這位木戶有三教授是個書呆子,可他所在的這個考察團,動機就未必純潔了。
“你們這次的考察對象,是古代的陵墓墓葬嗎?”許一城問。在陳維禮那張紙上,唯一可辨認的字,就是一個“陵”字。以日本人的貪婪程度,恐怕這是最吸引他們的東西。
木戶教授絲毫都不隐瞞:“是的,我們希望至少能有一次挖掘考察,最好是漢墓或者唐墓。”
許一城忍不住道:“你們不覺得這是一種偷竊嗎?”
木戶教授很奇怪地看着許一城:“許君你問這樣的問題可真是太奇怪了。我們的挖掘完全合乎學術規範,這些都是東亞歷史的寶貴財富,如果我們不盡快,你們中國的軍閥會把它們徹底毀掉的。”
“可這歸根到底還是偷竊。”
“歷史可不是某個人、某個團體或國家的專屬物,它屬于全體人民。讓懷有感激之心的學者來研究,結出碩果,總比毀在那些貪婪之徒手裏要好,這就是我的想法。”
許一城盯着木戶教授,後者的眼神沒有絲毫愧疚,也不含任何貪婪。他意識到,木戶教授是真正意義上的那種學癡,在這個人心目中恐怕沒什麽民族、政治的概念,只有自己的研究課題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許一城果斷換了話題。他是五脈出身,又受過正規的學術訓練,見識和學識都很豐富,兩人聊得特別投機。許一城想到信箋上那半截劍影,便有意把話題往劍器身上引,木戶教授恰好畢業論文就是這個主題,興致更濃,談了許多古代日本和中國鑄劍工藝的差別。許一城便旁敲側擊地詢問,這次支那風土考察團是否和什麽中國寶劍有關系。
木戶教授聽到這個問題,歪着腦袋思考了一陣,然後搖頭:“團裏沒有這樣的專題規劃。不過我曾經對這類課題做過淺薄的研究,如果這次考察碰到劍器類文物的話,應該會讓我先稍微過目,我想是這樣吧。”他說的時候,頭朝後微微仰起,雖然口中謙遜,神情裏卻帶着遮掩不住的傲氣,在這個專業領域,他在考察團裏應該是最資深的。
許一城心中一動,把那張紙上的重影形狀随手畫出來,找了個借口請教。木戶教授沒什麽心機,他覺得許一城是同行,就知無不言,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和盤托出,全無隐瞞。他告訴許一城,劍身彎曲這種情況,在許多文明裏都能看到,比如日本刀、蒙古刀和波斯彎刀。不過中原樣式的劍颚配彎曲劍身這樣的形态,他還沒看到過。
許一城盯着木戶教授半天,認為這人很真誠——或者說很單純——不會說謊。那把劍的素描,應該不是出自他的手筆。這就奇怪了,木戶教授明明是考察團裏的劍器權威,可他居然全不知情。
想到這裏,許一城不經意地問了一句:“木戶教授,你是否認識一個叫陳維禮的人?”木戶有三一愣,立刻露出惋惜神色:“陳君啊,我知道,他是這個考察團的翻譯。可惜昨天突然去世了。我聽團長堺大輔說是吸食鴉片過量,哎,真是可惜,他可是個很優秀的年輕人。”
吸食鴉片過量?許一城眉頭一挑。好一個借口!外國人眼裏,中國人無人不抽鴉片,捏造死因總是這個。他又問道:“那麽他的遺體現在哪裏?”木戶教授想了想,回答說:“今天早上應該是送到日本使館去了,堺團長親自送去的。”
按照法律規定,陳維禮是中國籍,意外死亡,理應交由京師警察廳來處理。日本人卻把陳維禮的遺體特意送進使館,一定是有什麽緣故。
許一城本來想再詢問一下,木戶教授卻突然站了起來,對許一城道:“團長回來了,你可以直接問他。”
四五個日本人正好走進飯店,為首一人寬肩闊面,下巴奇厚,兩道濃眉始終絞在一起,如同頂着一個墨團。木戶有三起身喊了一聲:“堺團長。”堺大輔看了眼許一城,問他是誰,木戶有三道:“他叫許一城,在問我陳君的事情,您比我知道得清楚,正好跟他說說吧。”
許一城暗暗叫苦,這位木戶教授真是成也實誠,敗也實誠。
昨夜方老山目睹了一夥神秘人把陳維禮的屍體擡走,那半截留在手裏的紙肯定也被他們收繳。那夥人一定知道,有人拿走了上半張紙。木戶教授這麽一說,這不明擺着告訴人家,紙在我手裏,我是來查陳維禮死因的嗎?
本來他還打算旁敲側擊,不動聲色地通過考察團裏的其他人來打探,現在倒好,直接被木戶有三給出賣了。
果不其然,一聽到陳維禮的名字,堺大輔雙目爆出一團利芒。他打量了許一城一番,用中文問他和陳維禮什麽關系。許一城只得回答:“我是他在北京的朋友,他約我今天來大華敘舊,可一直沒出現,我過來找找看。”堺大輔将信将疑,開口道:“很不幸,陳君昨晚吸食鴉片過量,已經去世。我們剛剛把他的遺體送到日使館,等到屍檢結束後,我們會通知他的家人。”
“屍檢不應該是京師警察廳來做嗎?”許一城問。
堺大輔不屑道:“你們中國的屍檢水平太低,根本沒法信任。再說我們現在想找警察都找不到。”
這倒也是事實,現在從吳郁文以下,警察廳所有人都惶惶,機能趨于癱瘓。
許一城知道這一下子打草驚蛇,讓對方起了疑心,沒法繼續試探下去了。于是他又敷衍幾句改日吊祭的客套話,借故離開。木戶教授聊得意猶未盡,他扯住許一城袖子,說中國有這種見識的人實在太少了,想約個時間去清華拜訪。許一城猶豫了一下,在堺大輔的注視下,還是把地址留給了他。
在離開大華飯店時,許一城注意到堺大輔身後站着一個人,一直冷冷地注視着他。這家夥穿着中式長袍,能看到衣下微微隆起的肌肉,脖頸粗大而精悍。許一城與他擦肩而過,突然身子一矮,這家夥便迅速避讓,然後立刻恢複成平常站姿。
許一城沖他笑了笑,指了一下自己皮鞋,意思是我只是系一下鞋帶。在這個人冷峻的目光注視下,許一城緩緩步出大華飯店,頭也不回,一直到走到大街上,才長出一口氣,發覺脊背一片冰涼。
許一城很确定,這一定是一名軍人,只有軍人才有這種內斂洗練的殺氣和迅捷動作。
事實很清楚了,陳維禮這次來北京,是以支那風土考察團翻譯身份出現的。他發現了什麽事情,情急之下扯下一張支那風土研究會曾用過印的信箋,從大華飯店逃出去,結果在半路不幸遇害。
東京帝國大學、支那風土研究會,說不定還有日本軍方的影子,許一城覺得這件事越發蹊跷,也越發兇險。如果調查繼續深入,他所要面對的,恐怕将會是一個組織健全的龐然大物,而他這邊甚至連報警都沒人理睬。兩相對比,強弱極其懸殊。
可是,那又如何?
許一城擡起頭,看到一排烏鴉從頭頂飛過,好似天空裂開了一道細小的黑色縫隙。他咧開嘴,露出一個自信而堅毅的笑意,擡起雙手,拇指相抵,八指交攏,對着天空拜了三拜,手背翻轉,再拜三次。
托孤一拜,九死不悔。
許家之人,許下承諾,就絕不會中途而廢。
這一天注定無法平靜。當許一城返回清華學校時,他驚訝地發現,房間裏兩位年輕的客人等候多時了。
一個是劉一鳴,一個是黃克武。兩人本來笑嘻嘻的,看到許一城進門後臉色凝重,一時都有些尴尬。許一城問他們怎麽跑來清華,黃克武一推劉一鳴,讓他說。劉一鳴推推眼鏡,把來意說明。
原來他們兩個到這裏,是為了吳郁文那件事兒的一點餘波。
那天在吳郁文的宅子裏,正德祥的王老板捐了一千五百大洋,換回來一個泥金銅磬,內裏還镌着一圈梵文,形若蓮花。當時是藥慎行親自掌的眼,雖未标定年代,但不會早于乾嘉。乾嘉到民國沒有多少年頭,銅磬本身也不算罕有,不值多少錢。王老板安慰自己,反正是花錢消災,真的假的無所謂了。
他把這木魚拿回家以後,随手擱到佛堂前。他的大太太篤信佛法,正好用得上。可當天晚上就出了一樁怪事。有個老媽子起夜時,聽到佛堂裏咯咯作響,她探頭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