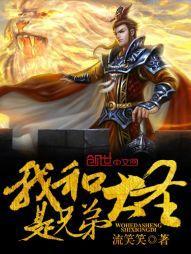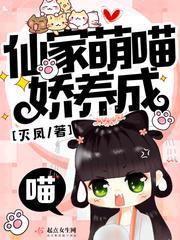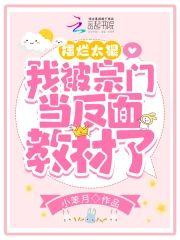第26章 (1)
天明後,二人又再縱馬飛奔。想到一清神通廣大,再如何潛蹤匿跡,也未必能躲過他的追蹤,二人索性不加在意,只在全力趕路之餘,四下探查下一清的蹤跡。
可血尊就如同融化在風中的一縷陰魂,只是綿綿不絕地纏繞着他們,卻不讓他們看到。
這般日夜兼程地趕路,不止一日,終于到了均州。
遠遠地,又見到了萦青嵯峨、連綿起伏的武當山,蕭七忽然間便有了種想哭的感覺。
自己繞了個圈子,又回到這裏。
人生何處不太極,或許人生的每次出發,不過是從起點繞個圈子,再奔向起點吧。
這又有些像老子所說的“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我們辛辛苦苦,不過是做了個紛紛擾擾的芸芸亂夢,再風塵仆仆地歸根複命。
只可惜,綠如卻再也不會回到這起點了,便如太極圖的兩條陰陽魚,自己和她分別站在一個魚眼上,卻已陰陽兩隔。
朱瞻基也是如此,好在他跨過了自己的太極,由陰至陽,找到了自己的平衡。而一粟,這個圈子繞得更大,多少年了,他終于回來了。
轉頭看一粟時,見那張普普通通的面孔竟也抽動了幾下,蕭七不由問:“老道士,這些年,你有沒有偷偷回來過?”
“來與不來,都是一般,”轉眼間,一粟又變得淡漠如水,“山還是那山,水還是那水!”
蕭七嘆一口氣,不知這是一粟故意遮掩之語,還是他真的已修成古井無波的境界。
他轉頭四望,輕聲道:“我們已經到了,那一清呢?”
“我知道他在,只是我們看不到,”一粟嘆了口氣,“我們都為玄武之秘而來,他一定會現身的!”
風塵仆仆地入了山,又風塵仆仆地趕到了武當山南岩紫霄宮,蕭七的心不由揪到了嗓子眼。
“蕭師兄,你終于趕來啦。掌教真人還好……”服侍一塵的小道士明虛見了蕭七,喜不自勝,“就是近日身子違和,老愛靜卧長睡。師父師伯們都說,掌教在練蟄龍睡呢!”
聽得小道士明虛的話,蕭七又驚又喜:“莫非也是靠着那蟄龍睡,掌教真人已控住了毒傷?”
“是啊,看氣色,掌教真人跟沒病一樣,只是不願說話。老人家說了,除了蕭師兄或是柳掌門回來,誰也不見!”小道士口中滔滔不絕,疾步引着他們趕往方丈室。
才行到方丈室外小院的門口,便聽院子內傳來一聲輕嘆:“你竟是……小師弟?我知道你會回來,只是沒想到,這一天要這麽久。”正是一塵掌教的聲音。
蕭七的心突地一顫:“掌教真人竟這般厲害,怎的知道是一粟回來了?”猛一回頭,才發覺一粟早已不在身邊。
卻聽一粟的聲音已在院內響起:“我這副容貌,當日二師兄便沒認出來,還是你厲害啊,難得啊,當真難得。”
不知何時,一粟竟已搶先進了小院,這人的身法當真猶如鬼魅。蕭七急忙飛步趕入院內,見一粟正輕輕摩挲着一口荷花缸的缸沿。
“果然,這裏的一切還是先前的樣子,這缸內的荷花還是當年師尊親留的種子啊。”一粟的聲音卻有些冷飕飕的,“連大師兄你,竟也能茍延殘喘到今日,也是一奇!”
蕭七聽他出言不遜,不由勃然大怒:“臭一粟,你說什麽?”心內卻想,“怪不得他得知掌教真人中毒之事後并不上心,莫非他竟和掌教有什麽舊怨?”
“上善若水,我常常坐在這裏看水看花。”一塵并不以為意,目光已凝在蕭七臉上,“蕭七,看來太子他們總算平安進京了。”
一塵淡然端坐在樹陰下,除了面色有些蒼白,幾乎看不出異樣。
“是,這一路有許多兇險,但太子還是如願進了京城,天下大局已定!”蕭七心中有悲有喜,聲音都有些抖了,忙搶上去跪倒在地,“師祖,你老人家的毒傷都好了?”
一粟卻嘆道:“差得遠呢,大師兄的蟄龍睡到底不算精修,只是控住了血脈,卻不能解毒,只是使毒力不顯而已。” 蕭七的心陡然一沉。果然只聽一塵笑道:“确實差得遠。老道也只是以真氣裹住了毒性而已,眼下便跟個廢人一般!”一塵的笑容還是那樣深邃而平和,揮手命蕭七起身,“咦,難得啊小七,你竟似煉通了中黃大脈!”
蕭七苦笑一聲,不知是否該把自己被一粟強行試手的遭遇告訴掌教,只得含混着道:“想必是弟子機緣巧合吧。”
一塵瞥了眼一粟,似乎察覺到了什麽,拈髯微笑:“甚好,甚好。綠如怎麽還沒有回來?還有蒼雲,他遠赴京師,聽說遇到了一些麻煩。你見過你師尊了麽?”
聽得綠如二字,蕭七便覺心頭被一把無形的錐子刺中,不由仰頭望向院後的那排翠竹,恍惚中他覺得少女還會從那地方蹦蹦跳跳地走出來,亦喜亦嗔地喊他“蕭七酸”。
怕給掌教看出端倪,他急忙咳嗽一聲,垂首道:“綠如還有些事,據說殿下要向她……請教琴道。師尊一切都好,但弟子想,他會留在大內,待京師大局安穩後,才會啓程回山。”
“蒼雲無事那便好。”一塵舒了口氣,又搖頭道,“可綠如萬不能留在皇宮的,她是個野丫頭,怎受得了那多拘束。過兩日你定要趕回去,無論如何将她拉回來。”
“是……弟子遵命!”蕭七伏下臉去,眼眶卻已紅了。好在這時候那小道童明虛已将兩盞熱茶遞了過來。他急忙裝作喝茶,不敢擡臉。
“大師兄知道麽,二師兄也要來了。”一粟的眸子緊緊盯住一塵。
一塵深邃的目光居然沒有任何波瀾,淡然道:“他要去便去,要來便來,這都是他自家選的路……”
一粟森然道:“當真是二師兄自家選的路麽,當初你不逼他下山,他能有今日?”
蕭七心下疑惑:“這臭一粟,他在玄武閣碰到一清時吓得要死,也不敢相認,怎麽這時候倒替一清出頭說話?”
“你苦修五岳真形圖,将容貌變成這般,想必是怕一清尋你去讨要天樞寶鏡吧?”一塵悵然望着一粟,“你如此怨我,決計不是為了一清,而是為你當年被師尊遣出武當時,我沒有勸阻!”
一粟顫聲道:“難道不是麽,我是師尊最小的弟子,但往往一年到頭極少得到他的指點,我悟道最勤,常閉關苦修,對玄武之秘也極是癡迷,卻在武當山大修即将功成時被他無端遣走。這難道不是你的功勞?”
一塵嘆道:“所以你奉師命下山雲游後,一連數年,也不肯回來……”
“其實二師兄也是個可憐人!”一粟眼中罕見地湧出些酸楚,“早年時你跟着師尊忙碌教務,我跟着二師兄的時候久些,難免情義重些。後來靖難之役,他下了山,我還曾偷偷去看他……”
忽然間,一粟的臉孔扭曲起來:“哪成想,正看到他在戰陣上殺人,遠遠的,我見他已變成了一把劍,在戰陣中滾動,每次光芒一閃,就有人頭落地,滿地都是血,比初春剛破凍的溪水還多。我吓得要死,不,這不是我的二師兄,再不是了。我逃得無影無蹤,再不想見他。那個性子沉默的二師兄死了,變成一個殺人無數、嗜血殘暴的血尊。”
蕭七也是一陣冰冷,還是個少年時,他便在武當山上聽說過山河一清的傳說,他是那樣可怕,又是那樣傳奇。但能将他朝夕相處的小師弟吓得亡命奔逃,那種殺氣,不知該是何等的駭人。
一塵苦笑搖頭:“你說對了四個字,一清确是‘性子沉默’,但寒冰下面就是烈焰,心魔早已進入他心底了,遲早有一日要生根發芽。記得當年師尊讓我們各選一門深修,我選了太極,以無為之法入道。你選的是玄真,形神歸一,道化天機。一清則選了最難的劍仙之道。但修煉劍仙得了卻俗緣,不問世事。偏這一點他做不到,幾次被師尊發現後呵斥。最終他獨自下了山,跟官府走得那般近,大開殺戒,竟成了‘血尊’。”
一粟始終目光陰沉地逼視着一塵,森然道:“再後來,永樂十九年,在朝廷遷都北京之前,朱棣發覺一清與他二子漢王過從甚密,唯恐他助漢王謀亂,命東廠督主栾青松親自安排,用一杯無色無味的‘參合蠱’将他麻翻,一囚數載……有時候我常常扪心自問,那個沉默而和藹的二師兄,為何會變成這樣一個殺人不眨眼的血尊?這都是大師兄的功勞啊,你将我和二師兄都擠出了武當,當真費了不少心機吧?”
蕭七再也忍耐不住,圓睜雙眸,厲聲喝道:“我沒見過你那沉默和藹的二師兄,我只見過殺人不眨眼的血尊。我只知道,他殺了綠如,還有管八方、董大哥,許多人都死在他手下!”
他心內憋悶已久,這一喝幾乎要将滿腹的憤怒傾瀉而出,聲音震耳欲聾。那小道士明虛吓得一個哆嗦,手中端着的茶盞失手落下,跌得粉碎。
一粟的眼神一顫,臉上也不由露出一抹黯然。一塵則大張老眼,手指着蕭七,顫聲道:“你……你說什麽,綠如她怎樣了……”
蕭七“撲通”一聲跪倒在地,號啕大哭:“掌教真人,弟子無能,沒有看護好綠如。她為救太子,在井陉關……遭了一清那老賊的毒手!”
一塵沒有言語,古井無波的目光卻突突波顫起來,驀地張口,“哇”地吐出一口鮮血。蕭七更覺痛徹心肺,忙搶上去扶住了掌教,想開口相勸,但淚水已如決堤之潮般湧出。
“一清呢,”一塵拼力抑住悲痛,沉聲道,“他現在何處?”
一粟道:“他跟你一般,也是中了萬蛇屍心,但他蟄龍睡的功夫更霸道,競能死裏逃生。不似你這般,幾十年功力都耗在這上面了吧?”
蕭七心中再震,更覺凄然:“怪不得掌教真人的中氣不足,原來真氣都被這怪毒耗去了。”他生怕一粟趁機偷襲,忙橫身站在一塵身前。
一粟不以為意地喝了口茶,冷冷道:“二師兄跟了我們一路,想必你不久便能見到他了。”
“他此時上山,必是為了那玄武之秘吧?”一塵緩緩閉上雙眼,長嘆道,“沒想到江湖上的一個傳說,竟成了你們幾十年的心結。”
“傳說,你竟說玄武之秘是傳說?”一粟的聲音似笑似哭,“那師尊為何要造出這武當雙寶?”
一塵默然無語。
一粟又緩緩嘆了口氣,道:“你說得是,這玄武之秘成了我的心結,悟不透,這輩子我就翻不出這個天地去。記得先師将天樞寶鏡給我時,只說了一個字,悟!可寶鏡太過偏門了,我苦參了這多年,還是悟不透,直到蕭七、綠如給我送來了玄武靈壺。果然啊,靈壺寶鏡是一對珠聯璧合的異寶……”
一塵道:“這麽說,你竟參破了那幾句話?”
“那幾句話?看來師兄真的是知道的。”一粟的眸子灼灼閃動,在院內悠然踱步,“太極之源,九霄之閣,合一最上,九五之化!由太極之源悟出陳抟的無極圖,九霄之閣是司天臺內的玄武閣,那的石碑背面也有一張無極圖,正面則是五岳真形圖。合一最上,五岳真形圖正指在無極圖第三層,由此指向武當山的‘天人合一最上之地’——這地方是哪裏?”
“了不得,你竟悟出了這麽多!”一塵淡淡地望着他,“那這天人合一之地,到底是哪裏?”
一粟仰頭望天,一字字道:“便在這紫霄宮所在展旗峰腰的太子洞!”
蕭七一驚,不由擡頭望了身後的展旗峰,冷笑道:“紫霄宮,太子洞,你又在信口胡言麽?”
“知道你掌教師祖為何移居紫霄宮靜養麽?”一粟瞥了眼蕭七,冷冷道,“只因這紫霄宮所在負陰抱陽,為風水福地,而整座紫霄宮的建造擺設,成天人合一之境,納天地太和之氣,宛然便是一幅道家修真的秘圖。”
“整座紫霄宮竟是道家修真的秘圖?”蕭七更是一震,這紫霄宮他自幼進出千萬次了,還頭次聽得這種說法。
一塵卻微微點頭,淡然道:“你能看到這一層,已是不易。”
一粟道:“司天臺的五岳真形圖,其實另有一層密意,這五岳的古本圖形,是自上而下俯瞰所得。武當山的‘天人合一最上境’,也需有此大手眼。若從上向下俯瞰,紫霄宮的形狀,便如一個展臂挺立的道者,正坐于武當山展旗峰正中線上。山門外南有五老峰,北有青羊峰,兩峰相交于此,恰似抱于丹田前的兩手,這丹田所在,便是紫霄宮。紫霄宮左側之山名青龍背,右側之山名白虎垭,此宮左降青龍,右伏白虎,這‘降龍伏虎’正是內家修煉的第一步……”
“了不得,竟看破了司天臺五岳真形圖的用意!”一塵的目光溫和起來,猶如年長的兄長看着自己最幼的兄弟。
一粟冷哼一聲,在院中緩步而行,侃侃而談:“整座紫霄宮的建築,其實是暗喻道者的修煉,其禹跡池、龍虎殿、紫霄宮正殿,由下至上,分別暗喻修煉之下丹田、龍虎交媾之象和中丹田。而最上方父母殿之上的太子洞,相傳為真武祖師爺在少年時的修煉之地。
“太子為少年之相,用活潑之少年以喻易動之心神,這太子洞便喻指上丹田泥丸宮。”
蕭七聽得呆了,這些山水宮觀,他終日朝相習以為常,聽得這一粟說出這些講究,細思果然如此,不由對這老道更多了幾分佩服。
“天人合一,在何處合一?”一粟終于頓住步子,目光灼灼地望向一塵,“必須是在泥丸宮!泥丸宮又名‘天谷’,為百神所會,與天地相往來者,便是此地,太子洞這裏,也是‘合一最上’之地。”
一塵道:“大有道理,那‘九五之化’呢?”
“參不透!”一粟的臉瞬間僵住了,道:“我來這裏,也是想向你讨教這最終的玄機。”一塵緩緩搖頭:“這最終的謎底,你知道了,也是無益。”
“師兄,你還當我是當年的那個小孩子?我千辛萬苦地趕回來,就是要破解這天大機密,可你還是當年那副模樣。”一粟臉上仍是那副千年不變的無憂無喜之色,但言語中已顯見郁怒,“你的毒傷,我有六成把握治好。你如實說了,我也絕對不為難你!”
“我以為你早該悟了,沒想到還沒有!”一塵搖頭,“既然如此,我們就去那裏看看。蕭七,你過來背我。”
一粟的眸子幽幽閃爍:“難得,掌教師兄終于肯說出這千古之秘了。”
“掌教真人,咱們何必怕他?”蕭七只覺全身氣息鼓蕩,自覺中黃大脈打開後,內功突飛猛進,這時自是頗不服氣。
“不是怕他,其實這一日也是你太師祖定下的,終究該讓他明白。”蕭七見一塵目光堅毅,不敢違背,俯身将他背在了肩頭。
一塵命小道士明虛不得聲張,只在院內守候。三人如飛般出了偏院,直向紫霄宮最高處的父母殿行去。
路上不時碰到進出的道人,衆道人見了掌教真人均是站住了斂衽問詢,一塵則一一含笑回禮。
由父母殿左首的偏門行出,一塵在蕭七背上指點路徑,三人轉個彎子,便到了太子洞左近。
“便是這裏了。”一塵手指前方一座青塔,“那便是‘九五之化’。”
那竟是一座道士塔,孤零零地聳立在洞前下坡的平緩之地。
塔邊都是茏蔥綠樹,暮風低回,山坡間樹搖枝晃,如無數青玉起伏,近處張三豐祖師練功時所遺的八卦臺泛出淡淡銀光,遠處群山間翠木凝碧,紅牆如帶,丹閣如點,在西斜的夕照中映出萬千明媚。
無盡的蒼翠斑斓中,最獨特的就是這座道士塔,它寂然屹立,仿佛與四周萬物巧妙地融合,卻又傲然聳峙,似乎四周的天地山林都是為了襯托它的存在。
“這是一座新塔,年歲并不久遠啊,在我離山時,肯定是沒有的。”一粟撫摸着塔壁,細細端詳着塔上的銘文,“明賢道人,這明賢道人的名字怎麽這般熟悉?”
“龍紋?”一粟忽地一驚,側頭望向一塵,“這雕飾,有些像是龍啊?”
這座塔氣象不凡,蕭七也曾見過多次,因這地方來得較少,也就一直不大在意。這時近前細瞧,果在不起眼的塔基處看到兩條似龍非龍的雕飾。
塔這種建築,是随着佛教傳入中原的。梵語稱塔為“浮屠”,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中所提的浮屠,就是佛塔。佛教的葬俗便是為圓寂的高僧建塔安葬,至宋元之際,也有道士羽化後建塔安葬。這便是道士塔,只不過在中原仍較為罕見。
蕭七依稀記得武當山五龍宮左近的山裏,有武當宋代名道孫寂然等幾座道士塔,但這地方為何會冒出如此一座氣象奇特的道士塔?此事他從來沒細想過,這時聽一粟說起了一個“龍”字,頓時心中一動:道士塔本是墓塔,在墓塔上雕龍刻鳳,可着實了不得。
“不錯,這座塔也只建成四五年吧。”一塵悠悠嘆道,“永樂帝大修武當山,用了十四年,這座塔其實是在快竣工前才始修建。那時候,你早已離山而去。你們再猜猜看,這裏面,到底是誰?”
一粟的身子突地一顫:“明賢道人,我想起來了,那是個很怪的疤臉人,半邊臉被燒過似的,獨自居住在南岩的後山。師尊曾對他極是照顧,卻又不允我們去看他……”
“你終于記起來了。”一塵的目光愈發深邃,“還記得他的年紀嗎?”
一粟道:“當真不好說,看起來像是年過花甲,但看他筋骨肌膚,又似是年歲不大。”
“他的年紀确是不大,但心境卻已如百歲老人。”一塵一字字道,“只因,他是一位被人逼下皇位的天子!”
蕭七和一粟盡皆低聲驚呼起來。一粟嘆了聲“是他”,蕭七則直接脫口呼道:“是建文帝?”
那些年間,被逼下皇位的天子只有一人,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朱允炆。靖難之役的終結,是南京皇宮的一場大火,那之後,建文帝神秘失蹤,神通廣大的朱棣花了整整二十六年時光,依舊無法尋到他的蹤跡。
“果然與建文皇帝相關!”一粟的目光恍惚起來,喃喃道,“記得當年碧雲先師只是透露出一丁點兒消息,沒想到竟是真的!”
那日在玄武閣,他化名為蒼涯子時,故意在朱瞻基面前提及建文帝,只是借機察言觀色,推斷出這位公子哥的身份而已,實則當年他雖從碧雲先師的口中探出了一點建文帝的影子,但一直沒有對此太過上心。
這時見一塵微微點頭,一粟陡地雙眸一亮,道:“建文帝竟是他?他竟來到了這裏,埋骨在武當山上?”他追問連連,目光悵然,仿佛穿透了時光,忽地頓足道,“是啊,明賢……賢明,怪不得他要用這道號,怪不得他跟我說話時的腔調,都是怪怪的……”
蕭七卻道:“怎麽可能?聽說那時候燕軍兵臨城下,建文帝大勢已去,幾乎是孤家寡人一個,又怎能從南京千裏迢迢地逃到武當?”
一塵嘆道:“憑他一人自是不成,可不要忘了,碧雲師尊那時候正在南京城。”
“碧雲真人?”蕭七又是一驚,“原來是太師祖護着他逃出來的。”一粟也恍然道:“罷了,能将建文帝從南京救出來,也只有師尊有此手段了。”
蕭七忍不住問:“掌教真人,為何太師祖要救建文皇帝?”
這也實在是個天大的疑問,道家人物該當逍遙世外,而那時候“武當三奇”中的“山河一清”正在燕王之子朱高煦帳下效力,聲名初露的柳蒼雲則在燕京守護燕王的世子朱高熾,偏偏這武當上一輩的當家真人碧雲祖師競反其道而行之,在危急中救走了建文帝。
“只因武當道法獨有的忠義慈悲!”
一塵的目中流露出崇敬之色,悠然道:“《北極真武佑聖真君禮文》有雲‘忠孝仁義如有失,無邊罪業實難逃’,武當道法頗重忠孝仁義。當年碧雲師尊曾與洪武太祖交厚,太祖臨終前曾對他有過托付。故而靖難之役最後半年,碧雲師尊恰在京師。最終皇宮火起時,他憑着絕世身手,趁亂救走了建文帝,也算了卻一段忠義往事。”
“原來如此。九五之化,便是這位九五至尊的羽化之地!”
蕭七也悵悵地吐了口氣。歷時四年的靖難之役,建文帝被自己的親叔叔朱棣趕下了皇位,而在不久前,這千裏亡命之旅,朱瞻基卻突破了親叔叔漢王的重重劫殺。
這幾乎就是大明朝的太極,輪回了一圈,好在結局也如太極的陰陽兩儀般截然不同。
一粟的臉色陣青陣白,緩緩道:“永樂帝明察秋毫,武當收留朱允炆這等天大的事,他一直不知麽?”
“武當山方圓八百裏,連許多武當門人都不識得這道人,永樂皇帝遠在天邊,又怎能盡知?”
說到這裏,一塵頓了頓,又悠悠嘆道:“但世間沒有不透風的牆,何況永樂先帝還有無孔不入的錦衣衛。據說,這也是永樂帝大修武當山的緣由之一,他派遣隆平侯張信、驸馬都尉沐昕等幾大親信來把總提調,隆平侯張信曾多次返京密奏,便是密報尋訪建文帝的訊息。只是碧雲先師當年百計遮掩,使得他們誤以為建文帝藏身在武當山支脈的房縣,直到建文帝安然辭世,那已是永樂十九年的事了……”
建文帝,大明朝的第二任皇帝,他的下落,實則是這二十多年來,大明朝最大的機密。
靖難之役中慘敗于自己的親叔叔之手,原本是大明正統的建文帝就在皇宮的一場大火中下落不明,屍骨無存。 相傳他被大火燒死,又相傳他化為神秘僧人,游走于吳越一代,甚至相傳他遠遁南洋藏身……可最終的結果竟是他化名明賢道人在武當山以天年而終。
“永樂十九年,”蕭七屈指算了算,“這位建文皇帝去世時的年紀也不大吧,還不到五十歲?”一塵道:“他心境衰苦,又怎能長壽,能在武當山善終,已是大幸。”
“不可能!”
一粟大叫起來,繞着羽化塔亂轉着,叫道:“決計不可能!流傳千年的玄武之秘,怎會是這簡簡單單的廢帝之墓塔?”
“我的話還未說完,建文帝死後埋骨于此,乃是永樂帝的旨意,而此事又與玄武之秘有萬千千連!”
“什麽,”一粟不可置信地盯着掌教師兄,“太宗皇帝竟知道了建文帝的下落……此事怎的又與玄武之秘有關?”
一塵微微一笑:“一粟,據你所知,玄武之秘到底是什麽?”
一粟陡然愣住,玄武之秘到底是什麽,這是他數年來苦思的謎題。他曾在玄武閣中滔滔不絕,但此時在大師兄面前,千言萬語一起湧上,反而不知說什麽是好。
一塵緩緩道:“世人以訛傳訛,以為玄武之力是一門橫行天下的玄奇武功。只有武當嫡傳弟子和皇室的緊要人物才知道,玄武之力是天地間起自北方的一股博大弘力,大到可以扭轉乾坤,幹系國運……這些你都是了然于胸的,但當年永樂帝朱棣大修武當山,還有更深的玄機和更可怕的故事……”
他的聲音陡然消沉下來,蕭七和一粟都靜靜地望着這位武當掌教,他們知道,他要說出的,也許是大明朝最大的機密。
“當年靖難之役時,永樂帝朱棣身邊有一位能人姚廣孝,此人亦僧亦儒,一身奇術卻得自道家。他和洪武爺朱元璋身邊的奇人周颠一樣,都是天下僅有的精通玄武秘術之人。姚廣孝有個道家弟子,曾在武當山修煉。這位弟子曾向朱棣進言,說他曾服侍過三豐真人,在三豐真人的丹房中見過他手書的一本《武當玄武秘策》。此書所述的,乃是三豐祖師的奇想:以武當山為根基,以道教宮觀環山擺布,造一座道家山河法陣,以獲玄武之力。那時候朱棣剛剛登基,正是躊躇滿志、萬機待理之時,聽得這話大喜若狂,忙去請教姚廣孝,追問在武當山獲取玄武之力的法陣秘要。
“姚廣孝聞知後大吃一驚,只因玄武秘術歷來有‘法不輕動、術不妄用’的嚴規。他對朱棣苦心規勸,暫時讓朱棣息了這念頭,回去後将那弟子重重呵斥了一番,将其逐出了京師。只是,這件事猶如一粒種子,既已播在了永樂皇帝的心底,終究有發芽的一天。永樂十年,經過十載的文治武功,大明國力大振,永樂帝再也按捺不住這念頭,終于按着當年那道士所描述的《武當玄武秘策》的情形,開始大修武當山。”
“原來如此!”蕭七沉沉地嘆了口氣,這時才知道永樂帝和玄武之秘的全部緣由。
“按着朱棣的盤算,能主持此項重任的,唯有兩人,一是三豐祖師,二便是他亦師亦友的老友姚廣孝。但三豐祖師仙蹤不定,苦尋無果,姚廣孝又稱病不出,只是全心監修《永樂大典》。無奈之下.永樂帝便召來了天下最著名的數位道家高人,以咱碧雲師尊為首,更有不少大明朝天學的精英,一番籌劃之後,便要大修武當山……”
聽到這裏,一粟不由沉吟道:“如此說來,師尊果然洞悉玄武之秘?”
一塵搖頭道:“師尊身為當時三豐祖師在世的首要弟子,自是責無旁貸,但他接下這重擔,還因他是武當高道,這興修道觀、大興武當之事,也是他的畢生宏願。朱棣秉承了其父親的性子,朱元璋削弱相權,直接掌管六部,以求江山千秋一統。朱棣則要更進一步,利用天學與天地溝通,以求獲得玄武之力,不但江山永固,更要長壽不衰。因這玄武最早的來源是北方七宿,形狀如龜蛇合一,龜蛇皆為長壽神物,故而玄武也為司命之神。當年太宗皇帝也想借玄武之力,獲得長生不老之境!
“那時他下了數十道聖旨,譬如,要匠人們對武當山‘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動’,連一石一木,都要從川陝等地辛苦運來。在朱棣眼中,整座山已如同有了智慧的神物,每座宮觀的營建,都要與峰巒岩澗的雄偉浩瀚、深幽峭拔,完全融為一體,這便如同一座調動天地山河之力的道家法陣。
“只是,人力有限,天道難尋,這座玄武法陣實在太過艱難。慢慢的,連朱棣自己也覺出了艱深,便又遣人苦尋三豐祖師。他甚至在三豐祖師當年的結廬之地重建了遇真觀,虛席以待真人歸來。只可惜,三豐祖師一生不朝天子不見君,索性揮袖長往,不知所終,連師尊都見不得他一面。武當山九觀、九宮、三十六庵堂等漸漸成形,但以之作為‘萬萬年與天地同其久遠’的仙家勝境則有餘,以之為調動玄武之力的法陣則不足。
“一晃到了永樂十六年,避居武當的朱允炆患了重病,久醫無效,身子日漸衰弱。碧雲師尊開始憂心忡忡,常對我說,朱棣喜怒無常,務必早作防備。果然,在這一年,發生了讓太宗皇帝朱棣傷心至極的大事,他平生唯一的朋友和第一謀士姚廣孝病逝于慶壽寺。朱棣為之辍朝三日,傷恸郁悶至極。朱棣原想軟硬兼施,逼姚廣孝出山挂帥,将武當玄武法陣建好,但姚廣孝這一去,他終于知道,他這套武當玄武法陣,只怕要功虧一篑了。
“太宗皇帝苦悶至極,脾氣變得暴躁異常,派遣出更多的人來打探三豐真人和朱允炆的下落。師尊見勢不妙,便将剛剛造好的天樞寶鏡交到你手中,命你下山……”
“永樂十六年……”一粟身子一顫,雙眼發直,顫聲道,“不錯,我就是在那一年,被師尊遣下山去的。他更命我不到新帝登基之時不得回山,那時候我心中憋悶得緊。原來如此,原來師尊是要……”
“師尊是要保全你!”一塵悠悠嘆了口氣,“咱們師兄弟三人,他獨獨選中了你,命你持寶下山,實是別有深意,對你也是最為看重!”
一粟似乎想到了什麽,雙腿發軟,“撲通”一聲,頹然跪倒在地。
“又拖了三年多,那時候北京新皇城已建好,南方的武當大修在師尊嘔心瀝血的督建下也進展神速,但太宗皇帝的脾氣卻越來越暴躁。先是外出查訪朱允炆下落的人一無所獲,惹得他大發雷霆,後來便因玄武法陣難有寸進,朱棣一氣之下,便将數十名查訪建文帝的大小官吏和十幾個修建武當宮觀的工匠名道盡數打入了錦衣衛大獄。
“那時候朱允炆已是病入膏盲了。師尊自是不忍這麽多匠人、道士和官吏因武當而獲罪,便只身趕赴京城面聖。在朱棣面前,師尊向朱棣獻了一計:此時武當山九觀、九宮、三十六庵堂已初具雛形,但只差最後一招,無法獲取玄武之力;可若是就此放棄,便功敗垂成,大為可惜,不如順勢而為,借山河法陣的玄武之力将北水地煞鎮住,使大明今後再無北方邊患之憂……”
“不錯不錯,”一粟喃喃道,“按道家學說,玄武為北方之神,北水地煞為北方之氣,也歸玄武掌管。”
一塵點頭道:“正因這北水地煞也是玄武之力的一體同氣,這座武當玄武法陣雖不能構造玄武之力這股天地間的本源巨力,但鎮住北水地煞還是綽綽有餘。朱棣雖不能與天地同壽,但若由法陣之力鎮住了北水地煞,使江山永固,那也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師尊此計一獻,朱棣龍顏大悅,他是殺伐果決之人,知道此時只得退而求其次,便下令放了十幾名高道。只是,奉命搜尋朱允炆下落的幾十名官吏仍要遭殃……”
一粟悚然一驚,道:“師尊競在朱棣面前,直承他救走建文帝之事了?”
蕭七的心也驟然緊起來,這朱棣性情暴戾,天下知名,當年一怒之下,曾将建文帝的心腹方孝孺誅了十族,而碧雲師祖救走建文帝這天大之事,不知該讓他何等震怒。
“在永樂大帝面前坦誠此事,須得有絕大的勇氣,更須有絕大的智慧。”一塵的老眼中隐約有淚光閃動,“果然,師尊跟他說了當年救走建文帝的舊事之後,朱棣暴跳如雷,定要将師尊治罪。但師尊不卑不亢地說,他當年這麽做,是因玄武神帝曾化為蕩魔天尊之相,托夢傳命,他也是奉了神帝之旨行事。朱棣性子多疑,聽後只是冷笑不語,顯是全然不信。
“師尊不慌不忙地又說,只不過那時他并不知道神帝為何要他這麽做,直到此時方明白神帝的良苦用心和深遠用意。當日真武神帝是以蕩魔天尊的戎裝相在他夢中化現,喻示此事與護國相關。果然,若要以玄武法陣鎮壓北水地煞,須得擇出陣眼之地,在其上建塔,塔中葬一位九五之命的極貴之人。原來真武大帝的神意如此深遠,竟早就知道了今日之局。”
蕭七忍不住嘆道:“妙不可言,朱棣一生最信真武祖師爺,太師祖這番言論将祖師爺搬了出來,他必然信了吧?”
“朱棣仍是将信将疑,當下便命見過建文帝的親信随碧雲師尊趕回武當,驗明真身。那親信趕到武當時,朱允炆已是奄奄一息了,回光返照之際,倒是喝出了此人的名字,命他回複朱棣,他無顏去見太祖洪武爺,死後就葬在武當山。朱允炆死後,朱棣一樁天大心事已了,便命碧雲師祖找尋陣眼。正如師弟你的推斷,這座武當玄武法陣的引人注目之處,便是紫霄宮,最緊要處,便在此處……”
一粟望着那氣象沉渾的道士塔,喃喃道:“不錯,此地緊挨着真武神君自幼的修煉之地太子洞,又與三豐祖師所建的八卦臺相鄰。神帝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