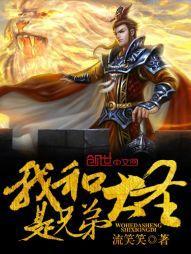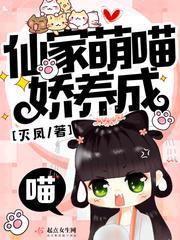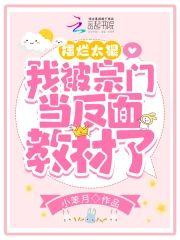第29章 (2)
府大街”邊緣的這座荒僻王府。
王府內只有兩個老仆常年在此打掃,疲憊的漢王沒交代幾句話,便昏昏沉沉地在房內睡去。
轉過天來,他們便聽到了悠揚的鐘鼓聲。
朱高煦一骨碌爬起,悵然踱到面向皇宮方向的大廳內,大開了門窗,側耳傾聽着。顧星惜也覺出了異常,跟在他身後,默然不語。
“新帝登基了!”
朱高煦眼望着九重大內方位,微笑起來:“這應該是禮部安排的大典,聽這禮樂,似乎他們正依次在大內的太廟、社稷壇祭告……這天下,已是朱瞻基的了!”
顧星惜不由幽幽嘆了口氣,心中也是百味雜陳。
“星惜,你相信宿命麽?”朱高煦的聲音中滿是壯志難酬的惆悵。
顧星惜苦笑一聲:“星惜是個小女子,自然是信命的……”
一縷鑽心的酸痛淌過心間,許多話她無法說出口。曾經有個讓她傾心的俊逸少年,為了自己甘願抛棄一切,但自己卻忍痛離開了他,只為了心中的仇恨。眼下,自己卻護着這大仇人滿城躲避追蹤,這難道便是自己的宿命?
“本王給你說個故事吧,這是真事,聽說過浦子口之戰麽?”
“自然知道,那是千歲平生得意之戰——靖難之役最後的關鍵大戰,永樂皇爺率軍進逼長江,卻在浦子口遭遇大敗,千鈞一發之際,是千歲舍命率兵沖殺,挽狂瀾于既倒。”
“我要告訴你的,便是那次大戰的秘密。那時我的父王在浦子口初敗之後,心灰意冷,更畏懼難以跨過的長江天塹,幾乎便想議和北撤。恰好在那時候,我率領一隊生力軍趕來。我記得當時,天上的日頭被雲彩掩得只剩下一線金色,就跟你的眉毛一樣細,殘陽周圍的雲卻極紅,仿佛神機槍爆開般燦爛。父王拍着我的肩頭說,高煦,你哥哥自幼多病,我指望不上他了,一切只能看你了,這就是你的宿命!”
“宿命!”朱高煦苦笑起來,“你知道麽,天地良心,在父王說那句話前,我真的沒什麽遠大志向,那時候大哥早已是世子。他待我很好,一直在燕京坐鎮,而我則在父王身邊沖殺。可父王說那句話的時候,周圍那麽多的大将和護衛都杲住了,他們都聽個滿耳,我覺得那一刻他們望着我的目光都很奇怪,似乎連風聲都靜了一小刻。然後我的血便沸騰了,提槍上馬,率領一清等精銳沖入敵陣,為我的宿命而戰。”
“原來如此,”顧星惜不由嘆了口氣,“自你父王說了那句話後,千歲才升起……遠大志向?”
“不,在那之前,我本來沒什麽野心,在父王說了那句話,經歷了那場大戰後,”朱高煦頓了一下,才一字字道,“我依舊沒什麽野心!”
顧星惜一愣,愕然望着他。
“可當時父王是在大庭廣衆之下說的,所有燕軍親信都聽個滿耳。那一場大戰,更因我的奮勇沖殺,父王終于脫險。在他們眼裏,我已是秦王再世。從那時起,我便再沒有退路了,也就是說,我的宿命在二十八年前便已注定。星惜你說,到了這時候,我還有回頭之路麽?”
顧星惜心底也響起一道沉冷的低嘆:是啊,我們都已沒有了回頭路,在你當日盛氣淩人地打死我的父親時,我的宿命便已定下。當你揮起鐵錘時,在你錘下掙紮的,都是有兒有女的活生生的人,但在你眼內,他們都是蝼蟻。
她的心紊亂無比,這一刻,她竟完全看不透自己的心。
她有些無奈地揚起頭,朝曦已變成了緋紅色,漫天雲彩褪去了那種沉沉的鐵色,變得火紅斑斓,大明京師千家萬戶的窗棂上都浸染了一層燦爛的霞彩……轉年八月,備受心魔煎熬的漢王朱高煦終于倉促起兵,朱瞻基則早已籌劃細致,決定親自率兵禦駕親征。
大明宣德元年八月辛未,宣德帝朱瞻基将朱高煦的大逆之罪奉告天地、社稷諸神,随即親率大軍數十萬進發樂安。數日間,便以摧枯拉朽之勢擒獲了孤立無援的朱高煦。
大明朝,開始邁向仁宣之治的巅峰期。
(全文完)
後記,玄武天機的圓與缺
關于《玄武天機》,在當時完稿後,許多感想已經寫在了《玄武天機的機緣》一文中,但現在第三卷刊印,熱心的編輯還是希望我再唠叨幾句,那就再信馬由缰式地唠叨幾句吧。
先說說閱讀體驗。小說類型不同,閱讀的感覺是不同的。我的小說讀者,以《雁飛殘月天》等大長篇培養的受衆最多。不同于《雁飛》那樣的成長型作品,《玄武天機》屬于懸疑型,代入感肯定不如大長篇,所以希望讀者們不要抱着《雁飛》那樣的代入感去看。這裏沒有少年一戰成名,沒有奇遇連連,沒有盟會奪魁,反而是更加真實的世界,兩個男主角,無論是蕭七還是朱瞻基,都很不如意,甚至連他們的愛情,都充滿着苦澀。這種真實的世界,包括文化和歷史的真實,才有更加綿長的力量,也是我希望讓讀者們細心品味的樂處。
新武俠寫了這麽多年,慢慢地發現,文化味道濃郁深長的小說其實最難寫。我比較欣賞丹布朗的作品,也一直希望能寫出那種懸疑背後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支撐的故事,除了驚險曲折的武俠情節,還要有更多的歷史、宗教、哲學等“文化養分”。
當日接受十堰市電視臺采訪的時候,我曾說過,像武當山這樣,融會了自然旅游勝地、道教玄武法脈的發源地、皇家護國道場、內家拳發源地等自然、文化、武術、歷史等多種元素交融一處的地方,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動筆之初,我就希望,寫武當的題材,不要僅僅拘于武林題材,陷于門派之争,而要有更大的“野心”。
《玄武天機》應該是做到了這一點。這也是我希望本書能帶給讀者的閱讀體驗:更加廣大的江湖視角,盡量真實的武學闡述,重新解讀的歷史事件,古樸玄奇的道教文化,深妙圓融的太極哲學,還有,比懸疑更加詭異的人心。
是的,人心。
當朋友們全部看完這個小說後,會明白我在最初的《太極之道,人心之旅》中所說的話,“玄武天機,其實寫的是一次人心之旅”。最大的秘密,在于人心,人心的多變也帶給懸疑小說無窮無盡的變化。當然,《玄武天機》雖然有懸疑也有推理,但總體上看,大多只是制造一種氛圍,并沒有做過多的渲染,如果裏面的人喋喋不休地追問:“請問,木衛被殺時,你到底在哪裏,誰能給你證明?”那小說不但變了味,而且會削弱我要表達的文化和哲學。
月有陰晴圓缺,任何一部作品寫完,相信作者都會覺得有圓滿處,有缺憾處。本文的缺憾在于對“太極之道”的演繹,因為故事所限,表達還是有些淺顯了。
太極之道講究舍己從人,随曲就伸,順勢而化,看似被動卻又時刻掌握主動,這種深藏在太極武學背後的太極哲學,其實才是傳統文化精華中的精華。在小說中,我曾借蕭七之口說出,太極之道較之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更加高妙;而小說整個主幹,千裏追殺中五行鐵衛的連環秘殺和朝廷抑武策的失敗,則反襯出太極之道的高明圓融。不過這終究是一篇武俠小說,因為不想表達得過于“着相”,所以沒有過多用力,事後想想,還是有些未曾盡言的缺憾感。
雖然有缺憾,但整體上這部作品是我非常滿意的一部作品。因為一直以來就想寫一部道教文化、歷史疑雲、解密懸疑類型的武俠作品,卻總感覺缺少一個點,最終是在武當山,找到了這個強大的支點。另外,我的小說,除了三四萬字的中篇,就是大長篇,這種二十多萬字的篇幅,正好是填補了作品的一個空白。
不知不覺,寫武俠小說已經十多年了,這是一個比較吓人的時間長度。十多年間,江湖劇變,出版環境、雜志市場、網絡環境乃至電子閱讀的市場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激變,甚至,連當年最年輕的武俠小讀者們都步入青年了,武俠小說創作所面臨的環境真的是愈發山窮水惡了,每一個武俠原創作者的內心深處都會有種彷徨茫然。
好在,當前,我最後已完稿的作品是《玄武天機》,假如要畫一個階段性句號的話,《玄武天機》無疑是一部能讓我安心的作品。
最後說一聲,那些不屈不撓的鐵杆讀者,比如百度“雁飛殘月天”貼吧上的吧友們.比如那些在微博和論壇上發評論支持《玄武天機》的讀者們,在此一并致謝,你們的鼓勵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
王晴川于2014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