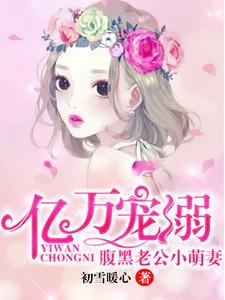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26章 章節
自在自己的崗位上獻出一份力量。
成員來自于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博士、碩士和本科生,行業內有影響力的工程師和設計師。
姜怡所在的是新聞收集整理組,面對網上海量更新的數據,以充分的耐心和責任感投入到疫情信息的搜集整理、核實等方面工作,整合各地衛健委發布的數據,持續建立高顆粒度疫情數據庫,以供全球研究團用于科學研究。
說起來複雜,不過是跟随着前人的指引“抽絲剝繭”,一步步細化,得到最終的可靠數據。
第 26 章
物資倉儲室裏,江海月皺着眉頭。
随着臨床一線病人源源不斷送到醫院,發熱科、呼吸科、隔離區這些地方,每天防護物資消耗巨大,供應壓力過大,醫療防護物資已經出現緊缺。新的物資還沒過來,不得已之下,是不是可以緊着臨床人員用,後勤人員、非重點防護區域或是可以尋找替代品?
她急沖沖拿着自制的兩個防護面屛,跑去找休息室裏的周廷。“周廷哥哥,你看看這種防護面屛,可不可以分給非重點防護區域使用?”
周廷明顯神情疲憊,撫了一下額頭,“我看一下,”材料用的是原有的電話本塑膠套、松緊帶、泡沫條、雙面膠和訂書機等,可以将整個頭面頸部遮罩起來。
他暗自盤算,這次病毒主要是經過呼吸道的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塑膠防護面罩配合口罩使用,的确可以起到隔離飛沫效果,且透明不影響視覺效果,節省了大量護目鏡。
“你讓院感科檢查一下,是否符合臨床标準,或許可以給臨床一般區域使用。”
聽完這話,江海月開心了,眼神流露出興奮的光,轉身就要走。
周廷無奈喊住了她,“等等,這種事情,你和主任報備一下,讓他們來牽線。”這個妹妹啊,國外呆久了,于人情世故不夠通透。
他低頭笑了笑,想到了心上那個可愛的姑娘。
那頭,姜怡也很忙,她被網上形形色色的新聞惡心到了。
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而疫情下的衆生百态,更是牛鬼蛇神出沒。
Advertisement
謠言滿天飛。有人趁機發國難財,藥品價格飛升;有人熱衷于造謠,制造恐慌;有人搞起污名化,對W市人或者鄂籍人員調笑、歧視;有人造謠“貓狗會感染病毒”,就有不少人把自己養的貓和狗摔死了。
志願者群裏憤慨不已,對制造恐慌的人、無知的人厭惡十分。只能抓緊時間該科普的科普,該舉報的舉報。
幸而,政府重拳出擊,打假、通報批評、對違法分子該拘留的拘留,該入罪的入罪。
在技術人員的支持下,實時辟謠科普網站終于做了出來,“s市傳言封城”,假。“吸煙能預防病毒傳染”?胡說!“貓狗不會成為新冠狀病毒的病原體,人與貓狗之間也不會交叉感染”,真!不知那些狠心背棄那些鮮活無辜小生命的人是否會感受到羞愧,悔恨自己對科普的無知、對生命的傲慢。
姜怡知道周廷很忙,待診患者太多,床位緊缺,排查工作困難,大多數患者要等待3-4小時才能見到醫生,每個診室平均接待100多位患者,也就是八九個小時不能喝水吃飯上廁所,還要精神高度集中,做好患者的登記、篩查、診療工作。
偶爾有記者采訪的報道出來,她會如饑似渴在新聞報道中搜索他的身影。她知道,護目鏡、口罩、防護服層層包圍下醫護人員們已無力去分辨誰是誰,往日的同事見面不相識,于是大家都用了粗黑筆在防護服上寫了自己的名字。但姜怡不需要去辨認字跡,只要能看到他,她就能認出他。
記者們很給力,堅持在一線報道,錄制視頻,及時反映一線情況。
姜怡知道,大家都在努力:
她看到江海月教導各個科室人手,用塑料膜、橡皮筋、海綿自制了不少面屏,不好用,但解了燃眉之急。
有個人影在鏡頭裏一閃而過,江海月同他說話,将手搭在他肩膀上,聲音有些模糊,似乎是囑咐他換班好好休息。
是周廷,鏡頭卻一下子被切開了。
鏡頭切回了新聞記者,他慷慨激昂,“數以萬計的奮戰在一線的醫護工作者,累了,困了,就直接在辦公室休息;
他們頂着巨大的壓力,扛着被暴露被傳染的風險,用倒計時的方式與生命和時間進行搏鬥。即便是物資不充裕,沒有條件,創作條件也要上。千裏馳援,迎難而上,無怨無悔。”
姜怡苦笑了一下,又慶幸有人陪在他身邊。
距離周廷出發已經過了兩周,她站在窗邊看天空,今晚的星星很多,室內月光無聲流動。
天色已晚,卻不顯得黑暗,甚至有些亮。她給他拍了一張照片,發送,“今晚有一半星星的天空。”周廷現在在幹嘛呢?在寫病例?在接診?在巡床?不知道他要什麽時候才能看看手機,才能告訴她一天平安。
他看到了,給她拍食堂加餐的湯圓,白色圓碗上放着幾顆橢圓橢圓的圓子,說不出哪個更圓,“而且,星星也好圓。”接着又給她發了一個小視頻,徐皓、海月捧着碗在吃湯圓,他拿鏡頭比着v同她說元宵快樂,黑眼圈有些重,胡子拉碴,精氣神卻不錯。
她低頭笑,為這默契。是呀,今天是元宵了。
希望尚在,這頭有清風有夙願又月光半牆,那頭有湯圓有戰友待凱旋而歸,2020已經過了1/6,盼往後,有伴、有盼、無病、無災。
大災難下,沒有人是旁觀者。沒入局的人也自願入局,做不到袖手旁觀。
小果知道姜怡加入nCoV志願者聯盟後,向她要了聯系方式,申請加入。她本可以加入外聯宣發組,畢竟她熟悉自媒體行業,做宣傳對她來說更為簡單。但是擅長宣傳廣告的人很多,親身在W市的人卻沒幾個。她最終加入了人力資源組,并選擇了孕婦團隊。
疫情擴展如此之快,原本就弱勢的老弱婦孺更是面臨困境。
他們團隊差不多有四五十人,志願者、醫護人員、急需幫助的醫護人員同在一個群。有人負責搜尋信息,關于孕婦的就醫渠道、各個醫院的床位等資料,實時更新。這個過程很難,因為很多電話是打不通的,城市的交通都停了,出行也很難。當然,并不完全依靠志願者,孕婦們也會互相分享信息,互幫互助。
中招的孕婦不在少數,大人或許能撐,胎兒卻過于脆弱,孕婦的健康問題成為一個難題。原本,孕婦的就診流程很清晰:先做血檢、CT,CT顯示感染後做核酸檢測,核酸檢測呈陽性确診,然後聯系醫院。實際操作起來,卻是如此混亂,因為想要确診是很困難的。
政策是核酸檢測确診才能進定點醫院。但凡CT有一點感染症狀,一個普通的省婦幼、市婦幼怎麽敢收治?而很多人CT顯示感染,但核酸檢測是陰性,沒法确診,又不能進定點醫院,就沒有醫院收了。
在這期間,跑來跑去換醫院的過程孕婦等得了嗎?過程中乃至家屬感染風險誰又負擔得起呢?孕婦和家屬都無助, “意外和明天你不知道哪一個會先來。”
這是孕婦的至暗時刻。醫療資源緊張,就診體系混亂。
哭泣解決不了問題,只能盡己所能,他們團隊忙得團團轉。口罩整天沒法摘,開着車在這座空城兜兜轉轉,為孕婦尋求去處。有位孕婦懷孕36周,發燒37.3度,高度疑似患者,亟需就醫。但是市婦幼醫院卻拒診,讓首先得找到接收的定點醫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醫院那邊說她是輕症,不收,怕進去之後反而交叉感染更嚴重。醫院也沒辦法,醫療資源如此緊張,進來後交叉感染導致胎兒不保的例子不少,他們只能出此下策。
她已經見紅了,平常早就該就診留院觀察等待生産,這時候就診渠道沒有打通,只能靠碰運氣的辦法。等待志願者們一個一個醫院打電話去碰,看哪個醫院正好有産房又有病床,而且你又有檢測結果了,把你加進去。
接連打的電話都沒人接,有人接的都是床位已滿。志願者們在群上互通消息,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絕望的情緒蔓延開來。
小果沒辦法了,只得打電話給徐皓,問他能不能幫忙想想辦法。好不容易,得知有個床位,趕緊聯系家屬送過去,在三天後剖腹産,母子平安。
徐皓發信息告知了小果,其實小果已經在群裏得知了,家屬們萬分感激,還給他們發了新生兒的照片,她将照片轉發給徐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