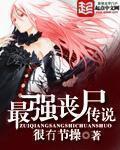第59章 彈劾
且說十四爺,不,應該稱一聲撫遠大将軍回京後,很是熱鬧了幾日,宮裏也屢屢有賞賜。
直到二月十二日花朝節,在這個花團錦簇聽起來流光閑适的一天,有禦史上書,奏‘撫遠大将軍’大不敬一事。
同時,閑言碎語如流水一樣在京城中蔓延開來。
蔓延到什麽程度呢,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二日,第一次有禦史上奏彈劾,二月十五日,各府後宅裏頭都對這件事如數家珍。
宋嘉書知道的就更全面了,不過這回不是弘歷說的,而是著名的李四兒當得報信鳥。
說來,去歲康熙五十八年的前半年,雍親王府當真過得挺順利,比如佟國維去世之事,就很合雍親王府的利益。
別看隆科多跟四爺關系更好,但其生父佟國維,這個分量更重的康熙爺親舅舅,卻是明碼标價向着老八的。他一死,四爺雖然悲痛着去吊唁‘舅公’去世,但心裏還是松了一口氣的,從此後,佟家再無人能壓着隆科多,而隆科多是向着自己的。
不過對福晉來說,這事兒是喜憂參半:佟國維死了,沒人能壓制隆科多,隆科多就越發把李四兒捧了起來。直到年前,佟家後宅唯一能壓一壓李四兒的女人,隆科多的親媽赫舍裏老夫人也去世後,李四兒在佟家,就成為了最光輝的‘女主人’。
如今的李四兒已經不甘于在內宅等着接待客人,而是徹底取代了隆科多的正妻,自己跑出來串門子了。
而且過年的時候串親戚同僚,會見些那些想捧着佟家或是隆科多的官員夫人,已經不能滿足李四兒了,她這回就來到了雍親王府,準備跟雍親王福晉這個‘高級親戚’聊聊天。
福晉:晦氣。
她再沒想到,還得在家裏接見李四兒這種侍妾,這人生簡直是如魔似幻。
再如魔似幻,魔幻現實到了眼前,福晉也得接着。
李四兒是個很愛聊天的人,而且她言談間都是一副親戚的樣子,甚至因隆科多是舅舅,她居然就能跟福晉擺出一點‘舅媽’的架勢,以長輩的姿态關心福晉的身體,給福晉問的臉都綠了。李四兒還繼續問呢:你這臉色怎麽不好。
福晉不肯跟她聊家常了,直接開始倒過來跟李四兒輸出佛法。
福晉在這上頭虔誠多年,實在是深有心得,佛語玄機把個無事無燒香,不知廟門朝哪兒開的李四兒繞的暈頭轉向,深覺得有點話不投機半句多。
于是李四兒打斷福晉的‘論因果報應’,直接道:“聽我們老爺說,上回平郡王妃上門,你們府上是年側福晉和一個格格接待的?”
福晉本來恢複些的臉色又綠了:隆科多你個大嘴巴!怎麽什麽事兒都給個枕邊婦人講!
上回因平郡王福晉之事,四爺還被叫進宮裏吃了個挂落,誰還敢提這事兒。
福晉只好道:“上回是我實在病的起不來,失禮于平郡王福晉了。”
李四兒嗤笑道:“有什麽失禮處?她自己還是個包衣哩,倒是敢挑理。”
福晉險些沒憋死才把‘你連個包衣都不是!’這句話咽回去。
李四兒猶自快活道:“既如此,你且去禮佛,我也不耽擱你,只管叫那兩位接待過平郡王妃的來陪我說說話就完了。”
福晉實在煩的要命:李四兒這人真是沒規矩也沒體統,哪裏有上人家府上跟點菜似的點名讓誰來陪自己說話。
只是李四兒要求了好幾遍,福晉實不能與她翻臉,也實在不想與她說話,就索性真的進去禮佛,讓人去叫年氏和鈕祜祿氏。
年側福晉聽了正院傳來的消息,難得跟福晉心有靈犀:真是晦氣。
宋嘉書聽了此信,倒是真想見見這個把隆科多迷得人頭鬼腦子的李四兒,到底是何等美人兒,于是收拾着就去了。
這一見,又有點失望,雖說李四兒生的确實是姿容秀媚,巧笑麗色,但距離那種能迷得人烽火戲諸侯的美實在也是有差距的。現成對比在這裏,年氏在姿容上就要超出李四兒一截。
那隆科多的表現,真的只能用不知名的真愛來解釋了。
李四兒見了兩人倒是挺熱情和氣,跟兩人分享起了京中八卦。
其實方才李四兒就想說的,但對上烏拉那拉氏那張石像一樣的臉,她就沒有興致。
她能從一個小小的侍婢,到哄得隆科多心裏只有她,便是政治上的智慧她沒有,忖度人心的聰明她是不缺的。
雍親王福晉看不起她,她心知肚明。
所以她跑來欣賞了一會兒烏拉那拉氏不得不敷衍她的樣子。然後又非要見雍親王府的側福晉和格格,把烏拉那拉氏整了個沒脾氣,她就更覺得可樂。
這會子心情好了,就跟人分享起自己新得的消息。
宋嘉書就是這樣聽說了十四爺的八卦。
——
三日前,有禦史彈劾撫遠大将軍“大不敬與僭越”兩條重罪。
起因是藏邊一位小官寫的《告民衆書》,在裏頭稱十四爺胤祯為皇太子,安撫民衆說大清的皇太子會帶領大清皇帝的精兵來拯救我們!
青藏地區自古就與中原地區不太通音訊,甚至語言都不一樣。自然更不了解大清開國後,中央分封的十六等爵位,什麽貝勒貝子的,他們也搞不明白。
而且貝子聽上去就不太威風。
這位八品的小官大約是為了讓人民群衆感受到中央的熱情,所以就直接在輿論上給胤祯升了級,說是皇太子要率兵過來——這樣聽起來,可比一個什麽十四阿哥,或是貝子強得多。
樸素的邊境人民不知道啥貝子貝殼的,但他們知道什麽是皇太子!那就是下一個皇帝啊,四舍五入就是皇帝陛下要來親自來救他們了,一聽這個都振奮了。
這篇《告民衆書》籠絡民心效果很好,傳播效果也不賴,結果就一路傳到了京城。
這算是捅了馬蜂窩了,這些年京城中為了儲位填了多少人命進去?這一看:嚯!咋的十四阿哥,您自己就給自己封皇太子啦?那可不能夠!
原本一個八品邊地小官寫的非正式文書,又是散發給叛軍地區的百姓,可以算是個筆誤。但巧合的是,這位小官作為反準噶爾,挺大清統治的出色當地官員,胤祯還曾經親自接見過他,這可就洗不清了。
誰能證明,這篇《告民衆書》,不是十四阿哥授意的。
雖然這個朝代還沒有從‘農村包圍城市’的先進理論,但是不妨礙聰明人開始揣測十四阿哥想走‘邊地包圍中央’的路線,正在對儲位下手。
有一個上書攪混水的禦史,就有無數渾水摸魚的人。
一時十四爺被彈劾的滿頭包。
李四兒的聲音像甜瓜一樣,讓人覺得聽着就甜脆,她一口氣說完,然後笑嘻嘻的對他們道:“要我們爺說,十四爺也是太不小心了些,這皇太子的話也能亂說?”然後又對年氏道:“聽說年側福晉家裏的兄長也在西北啊,倒是可以問問到底怎麽個情況,總不好冤了誰縱了誰不是?”
年氏根本不想理她。
這事兒跟泥巴一樣,甩脫都來不及呢,她才不能拉着自家哥哥下水。
李四兒見年氏只是淡淡的,就開始扭頭跟鈕祜祿氏說話:“府上四阿哥我也見過一回,我們老爺着實誇呢,說四阿哥聰明懂事,是個好孩子。”
宋嘉書:……我終于知道為啥人人都煩她了。
經過一回賓主不盡歡的交談,李四兒終于從雍親王府走了。
大概是李四兒的為人實在出名,弘歷聽說這件事,還特意回凝心院請安,然後關心問道:“聽說那位李……太太非要見額娘,她沒欺負額娘吧。”
弘歷這句李太太也是有緣故的,在隆科多府上,他下達過一道命令,吩咐下人誰都不許稱呼李四兒姨娘,必須稱呼太太,把還活着的正室給一筆勾銷了。
甚至弘歷等阿哥過年的時候,上門給隆科多這位‘舅公’拜年,隆科多都直接道:“嗯,好孩子,去後頭找你們太太吃果子去吧。”弘歷弘晝這兩個小的這才見了一回李四兒,根本沒見到隆科多的真夫人,也是大開眼界。
總之,隆科多的帏薄不修在京城也是出了大名的,只是他本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就是了。
宋嘉書見弘歷擔憂,就笑道:“還有年側福晉呢,能有什麽事?那位‘李太太’還跟額娘誇你呢。”
說完就看到弘歷浮現出一種跟福晉一樣,一提李四兒就‘牙疼’的表情。
宋嘉書笑眯眯,忍不住揪了揪兒子的腮:“你這孩子,就是太明白了。”弘歷的腮現在也褪了小時候的嬰兒肥,揪起來沒有那麽軟了。
弘歷這兩年難得被額娘揪一下,還有點臉紅。
以至于愣了一下才想起剛才自己要說什麽。他想起在隆科多府上,只見隆科多介紹了一個兒子,就是李四兒所出的玉柱,至于福晉出的岳興阿根本就沒見着,似乎根本不存在似的。
但弘歷曾在岳興阿上來拜見四爺的時候,見過一回這個可憐的嫡子,覺得這位表舅其實是個有才的人,可惜被親爹嫌棄。
宋嘉書認真聽着弘歷的話,見他為岳興阿不平,便安慰道:“弘歷,世人眼裏心裏總有是非對錯,便是一時為了權勢不敢說不敢做,來日若有機會,自會有公道的一日。”
她沒說的是,可惜遲來的公道,是救不了現在的苦難的。岳興阿這個隆科多親生骨肉都這樣,那占着正室的隆科多夫人,不知如今在受怎樣的折磨呢。
母子倆閑話片刻,弘歷知道額娘沒受李四兒的欺負,也就放心的走了。
雍親王府內,宋嘉書是覺得自己活得挺好,沒受欺負。
而在朝廷上,覺得自己受委屈的人很多,頭一個就是十四爺,他覺得自己冤枉透了,被欺負慘了。
他進宮找親爹:“皇阿瑪,兒子實不知這些人是何心腸!生要離間父子之情!”
康熙爺很是安慰了兩句。
可胤祯進宮剖白了自己兩回,見皇阿瑪雖然安慰他,但并沒有下旨申斥責罰禦史們,心裏也打小鼓。
于是也不敢繼續呼朋引伴,在京中招待兄弟故舊了,他上書請求回藏邊去籌備戰事,争取一開春就把拉薩的準噶爾叛軍消滅掉。
康熙爺準了。
十四爺收拾東西也沒用兩天,迅速打馬離開了京城,還不忘帶上一個有點懵的新出爐的達、賴、喇、嘛:怎麽這就走了,我還沒體驗夠京城的繁華呢!
十四爺回來的多威風,走的就有多狼狽,心裏格外氣惱。
他雖托付了八哥九哥,替他查查這是誰要陰他,但心裏也未必全然相信他的八哥。畢竟自己這戰功一出風頭,誰知道八哥九哥心裏有沒有芥蒂,會不會背後捅他一刀。
不知被誰敲了悶棍,十四爺的郁悶就甭提了,進宮辭行的時候,還跟德妃娘娘吐了好大一口苦水,把德妃娘娘聽得心髒疼:她可憐的小兒子,跑到邊疆去吃土喝風,回來還被人坑了一把,這會子只能再趕回去吃苦,德妃心都要碎了。
偏生現在還不敢病不敢叫太醫,怕皇上以為她們母子怨怼,只得撐着。
于是在見了四爺的時候,德妃就把這口苦水和憋屈吐給了四爺,流淚道:“你弟弟去的地方那樣苦,據說水都是燒不滾的,吃個肉都是帶着血的,他何曾受過這樣的委屈啊。況且他又不是去閑着享福的,是去拿命打仗的!偏有那麽些心腸壞了的人,說那些個誅心之言,叫他在京城待不住,這是要咱們母子三個人的命呢!”
德妃淚眼朦胧看着四爺:“當日你既然請旨讓你弟弟去邊地,怎麽如今不肯給他分辨清白呢,你做人親哥哥的,難道看得下去弟弟這樣委屈嗎?”
給四爺頂的心口也疼起來了。
心道:當年我舉薦十四做大将軍的時候,額娘你可不是這麽說的,你不是高興的不得了嗎?怎麽有功勞就是十四自己掙來的,有了錯處就是我的?
四爺看着德妃的淚眼朦胧,心裏真不是滋味啊,額娘怎麽不替自己想想,這樣事關儲位的閑言碎語,他怎麽好出面?他怎麽能出面?他的為難就不是為難嗎?
而且額娘話裏,甚至還有一點疑他的意思,竟是覺得他把弟弟架到了火上。
繼十四爺痛心的離開京城後,四爺也糟心的離開了德妃的永和宮。
——
乾清宮。
梁九功在旁邊不敢出一聲,魏珠也在下頭跪着。康熙爺的聲音沒什麽波瀾:“老十四到驿站了?”
魏珠應了是。
康熙爺也沒問別的,讓他下去了。然後手下的折子,卻是半日都沒有換。
老十四這件事,雖是禦史彈劾,但背後少不了他別的兒子們影子。
這讓他又惱火又心累。
這些年下來,康熙爺不得不面對兒子們并不兄友弟恭這個現實。
康熙爺不由想起去歲,舅舅佟國維離世前的話:“皇上,國本還是要立啊。”
雖然康熙爺對佟國維繼續推舉八阿哥這件事不置可否,但國本要立下這句話還是聽進去的。
是啊,他雖然如今身子骨還硬朗,但到底上了年紀,也該考慮這個問題了。
康熙爺學貫中西,從來清醒的認識自己是不可能達到虛無缥缈的長生,永遠坐在帝王的寶座上。
那麽這個國和家就總要交給下一任的皇帝。
他要在他的兒子裏面挑一個能夠延續他們大清的強盛,滿人的統治的英才,也要挑一個能夠容得下兄弟,保得住他這些兒子孫子的寬厚的繼承人。
康熙爺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
随着十四爺出京,風波流言就漸漸平息下來,一來當事人都跑路了,到底是皇子也不能窮追猛打的,萬一這位将來真的成了皇太子呢?二來皇上肯讓十四子繼續掌兵權,本身就是一種态度,所以大家都收拾收拾停了手,這件事也就暫時性的過去了。
這一年春日,京中花開的極好,據說比往年都要鮮旺許多,看起來是個極佳的年景。
有這樣的好兆頭,康熙爺覺得今歲的戰事一定能順利。
邊疆的戰事還未傳來捷報,雍親王府倒是先有好消息傳入宮中。
四月底,弘時的妾室鐘氏誕下一個男孩,四爺終于做了祖父,康熙爺也添了重孫子一枚。
雖然這不是他第一個,甚至都不是前十名的重孫,但想想雍親王府子嗣的情況,康熙爺還是給了賞賜。
真是不容易啊。
四爺自然更高興了。
皇上給重孫輩的字早就定了永字,并且表示,朕只起孫子的名,重孫子的名,留給你們這個祖父自己取去吧。
于是四爺一高興,孩子洗三就給起名為永坤。這是個寓意極佳的好名字,不單弘時聽了高興,李側福晉更是久違的又起興了不少:弘時都給四爺生下長孫了,府裏別的阿哥還連媳婦都沒有呢,真是給弘時做世子又添一重要砝碼。
唯一遺憾就是這不是嫡孫,而且鐘氏的孩子都生出來了,董鄂氏的肚子卻還沒個動靜。
李氏高興之餘不免把董鄂氏又叫去‘談心。’
她是挺高興,但董鄂氏可不高興,多了個庶子她沒什麽高興處,跟李側福晉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又受了一頓委屈不必提。
過了五月初五端午,李側福晉的興致仍舊不減。
耿氏就來跟宋嘉書吐槽:“瞧瞧前日大夥兒一起吃粽子的時候,李側福晉那個興頭,別說三句話了,半句話都不離永坤,不知道的,還以為那是她生出來的。”
宋嘉書在屋裏慢慢遛彎——端午這幾日粽子吃多了,糯米不太好消化,她就得多走一下。
聽了這話就笑:“俗話說得好,小兒子,大孫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怎麽能不疼呢?”
兩個人正在閑聊,聽見外面一陣喧擾熱鬧。
耿氏一個眼神,青草就出去打聽了,回來後臉上帶着些說不出的表情:“回兩位格格,是年側福晉診出了身孕。”
喜得孫子與年氏再次有孕,對四爺來說,那真是雙喜臨門。
大夫們又集體入主東大院後頭的小屋子,開始為年側福晉保胎。
——
這世上大概是家庭和事業很難兩全。
雍親王府內喜事連連,但對四爺來說,朝上的局勢并不是很好。只因老十四的戰功實在是突飛猛進,朝上立十四為皇太子的呼聲也越來越大。
不知是不是從京裏有點灰溜溜回戰場的關系,讓十四爺心裏憋了一口氣,總之從開春,十四爺就命麾下人出征,直奔拉薩而去。
一路如尖刀入藏,七月份已經傳來捷報,清軍已經成功進駐拉薩,連新的喇嘛都送回布達拉宮裏面了。
康熙爺大喜,對撫遠大将軍的贊揚喜愛溢于言表。
“……撫遠大将軍王知人善任,保舉得賢之所致也。”①
雍親王府的書房,四爺拿着一封信函在看,倒也不是什麽密信,只是寫了些十四入藏的舉動。
其中這句話,就是激動的藏邊人民,在清軍入藏趕走準噶爾部隊後,立在布達拉宮山崖上的碑文。
當然,這回老十四自己也警醒,下頭的官員也不敢再犯錯,沒有再敢刻皇太子這個名號的。
碑文裏頭除了歌頌皇上聖明燭照,別的就是歌頌十四這位大将軍。
經此一戰,十四在戰功上頭,已經睥睨衆兄弟。
四爺将信函擱在桌上,蹙起了眉頭。
若是皇阿瑪真的有意立十四,那就該把他召回來入各部熟悉政務了,就像當年的太子,一般都是皇阿瑪親征,太子監國。一個皇帝,不能不懂戰争,但更不能不懂治國。
八月裏,藏邊更詳細的折子進了京。已經是收拾戰場殘局的折子了:十四爺親筆上書,請教皇上如何撫民,如何處降,如何重整人口不足的鄉鎮。
皇上老懷大慰,在朝上險些笑成了一朵燦爛的花。
果然是朕的兒子!
當日朝上都不看好他出兵藏邊,覺得那裏地少人稀,沒啥産出,而且教派混亂語言不通,可謂化外之地,不如讓他們自生自滅。尤其是剛開始,清兵小敗的時候,朝中不戰更是占了絕大多數。
康熙爺雖是皇帝,但力排衆議也是有壓力的——他也不想晚節不保,在自己執政六十年留下一個大敗。
如今胤祯的大勝,就是再次證明了他作為皇上獨一無二的高絕眼光,給他皇上的履歷裏再增添光彩的一筆。
他自然大樂。
只是此時,康熙爺沒有立刻提筆回複十四的折子,他要看看,其餘兒子面對此事,會有什麽反應。
作者有話要說:
①:清軍成功護送達賴喇嘛進藏後刻在布達拉宮所在山崖上的碑文 :"此皆我皇上乾綱獨斷,離照當空,睿慮殿陛之間,決勝萬裏之外,撫遠大将軍王知人善任,保舉得賢之所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