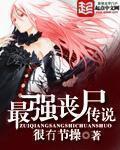第61章 祭拜
且說這會子見阿瑪點了自己的名,弘晝連忙站好些。
弘歷便先道:“回阿瑪,方才我跟弘晝在路上打了會雪仗,故而衣服濕了。因阿瑪處來人找我們,不敢耽擱,就直接來了。”
臨近過年,又剛舉辦完幼子的洗三,四爺心情正大好中。
再看兩個逐漸長成健康活潑的兒子在跟前,心裏更是高興的。
原本還要先板着阿瑪的臉訓兩句,但聽弘歷說兩人打雪仗,倒是觸動了四爺心裏那份兄弟之情,就只是輕輕訓斥了一句就揭過了,只道:“這麽大了,連輕重也不分嗎?自然是身子要緊,先回去換件衣裳,別害了風寒。”
兩人這才回到前院兄弟倆的院落去換衣裳。
弘晝也連忙趁這個功夫,臨時抱佛腳,一路走一路跟四哥念叨了兩句功課,算作複習。
等回了四爺的書房,弘歷和弘晝就聞見姜湯的味道。
四爺還是板着臉,只是點點桌子:“喝了吧。”
兩人就都笑着謝過阿瑪,然後捧着熱辣辣的姜湯啜飲而盡。
兄弟間情分是真的好,還是表面的功夫,對四爺這種‘兄弟關系困難戶’來說,自是能看的一清二楚。
在他看來,弘歷弘晝大概是一同長大的緣故,當真是有種默契的親厚。弘晝喝完姜湯後,弘歷甚至比小太監還能再快一步的,順手就遞過去茶水,讓他壓一壓口中的姜味。而自己板着臉的時候,弘晝則下意識用眼睛去溜弘歷,等着四哥先說話。
四爺看的滿意,想起剛出生的小兒子,就道:“你們也是做哥哥的人了,要好好照顧幼弟知道嗎?以後也要多去看弟弟,陪他玩。”
這會子四爺也忘了,自己少時德妃反複囑咐他,告訴他一定要‘讓着,照顧十四’的時候,他心裏的不平衡。
俗話說得好:孩子們長大了就會變成自己曾經最讨厭的大人。
四爺很不自知的在犯德妃當年的錯誤,或者說絕大部分家長的錯誤——大的當然要讓着小的,便是家長有些偏心小的也是應該的。
弘歷低頭應了,弘晝倒是敢說話,眨着眼睛問道:“阿瑪,七弟才那麽小一個,就跟我胳膊似的那麽大。方才洗三的時候,他除了哭就是睡,眼睛都不睜開,我們怎麽帶他玩啊。”
四爺被他問的頭疼,繼續板臉:“難道要你現在就帶着弟弟胡鬧?自然要等他長大些。”
弘晝是大膽的,見阿瑪沒生氣,就繼續道:“那還要好幾年呢,阿瑪,我跟四哥現在都長大了,阿瑪別只讓我們帶小孩子玩,也給我們點正事做呀。”
四爺:……難道你不是小孩子嗎?
雖然就差半歲,但弘歷已經有了些大人的神态和穩重,弘晝還跟猴兒似的,四爺怎麽也不能把這個兒子看做個大人。
他還沒說話,就見弘歷也用亮亮的眼神盯着自己:“阿瑪,我跟五弟可以幫您做事。”他抿了抿唇有點忐忑也有點不甘似的嘟囔道:“八叔家裏的弘旺堂兄,就比我們大兩歲。我們上回去給三伯和五叔家兩位世子堂兄道賀的時候聽說,八叔家裏籌備賀禮之事,都是弘旺堂兄辦的呢。”
可以說,弘歷雖不是故意,但很精準的戳中了四爺的一個點。
老八的兒子可以,我兒子也可以。
四爺又喝了一口茶,就隔空點了點兩個兒子:“還沒過年,你們倒是都露出長了一歲的架勢來了。也罷,既如此,等正月裏功課不重的時候,你們就好生寫一個時論來。”
然後便對兩個兒子說了千叟宴之事。
“上一回辦千叟宴的時候,你們才兩歲,自然是沒經過見過的,如今你們且先想想,若是讓你們帶着人籌備此事,要怎麽做才順當?”
這差事其實很能考較人,涉及頗廣:大到要收各地州府送上的老年人口的統計、戶部銀兩的籌備;小到各地老人進京九門兵士的調度,車馬的安排,恭賀盛世的賀文種種事情,摻雜在一處。
可謂是從俗務中,可見天文地理人口經濟。
四爺自不指望兩個孩子在這個年紀,就能辦周全的事兒,只是要先考教他們一二,別讀了多年書,跟趙括似的只會紙上談兵,全然不通庶務,一辦差事就漏洞百出才是。
四爺還許了他們:“若是有些可取之處,等明年開春具體辦事的時候,你們就跟着去看看罷。”
明年兩個孩子也十歲了,很到了可以辦差的年齡。
到時候随意塞到一處去,讓他們也經歷些世情。
弘歷弘晝都難掩喜悅,一個抿嘴笑,一個咧嘴笑,都笑着告退了。
四爺看兩個小的歡天喜地走了,就想起弘時來,方才他想找兒子們一并過來問功課,知道弘時往後頭董鄂氏處去了,四爺就沒叫他——這傻兒子難得肯放下小妾去跟正妻一處,四爺也很想抱個嫡孫,就沒打擾他們小夫妻二人相處。
如今小兒子也出生了,要是再來個嫡孫就完美了。
四爺還在這裏暢想兒子兒媳的和睦,而後頭茂昌院的氛圍,跟和睦兩個字可不搭邊,堪稱是很不美麗。
——
弘時來找董鄂氏是說正事的,因大年初二他要陪董鄂氏回去看老丈人。
說起岳父來,弘時就不免嘟囔了一句:“阿瑪自然是偏着東大院,有些壓着我。可岳父怎麽也不給我說句話,只怕他勸勸,皇瑪法也就聽了。”
這給董鄂氏氣的:她阿瑪雖是尚書,但也管不到愛新覺羅家的事兒啊。
要是她阿瑪敢去康熙爺跟前說,你看我是個尚書,這官兒做的不錯,那你給我女婿一個世子吧。以康熙爺的脾氣,她阿瑪保管要涼涼。
董鄂氏惱的不得了,因着自己跟他夫妻情分不太好,所以弘時對老丈人一貫不怎麽親近,你不親近也行啊,但你不能坑你老丈人去找死啊。
董鄂氏怕弘時在外頭真說起這件事,連忙鄭重其事跟弘時講明白厲害。
結果弘時反而臉一紅又一板:“我不過這麽一說,誰要靠着岳父家了?我自家瑪法就是皇上,阿瑪是王爺,倒要靠別人不成?你也是,動不動就拉着個臉,叫人如何說話?”
董鄂氏簡直是欲哭無淚。
弘時還深覺跟媳婦話不投機,就只敲定了時辰就想走,還是董鄂氏為着弘時好,叫住他道:“如今爺也是成親有子的人了,年節下該多與叔伯堂兄弟走動才是,尤其是十三叔府上,阿瑪最重,爺多去走走總沒壞處的。”
弘時擺手:“你不懂。十三叔那裏,走不走有什麽要緊處,倒是今年十四叔回了京,又立了大功,我該多上門去,到底是親叔叔呢。”
董鄂氏不太懂外面的事兒,見弘時不窩在家裏陪小妾,就覺得也行吧,你走去吧,然後問着弘時備禮的事兒。
弘時繼續擺手:“罷了,我去與額娘商議。”頓了頓:“你入門時間短,少做主張,只好好伺候額娘吧。”
再次把董鄂氏氣個半死。
深覺:這日子可怎麽過喲!
弘時出門的時候,就見除了茂昌院外,其餘各處院落,也都有下人在掃放鞭炮落下的碎屑紅紙——今日,是年側福晉剛出的七阿哥的洗三禮,四爺命人在各處門戶前都放了鞭,一為慶賀喜樂,二為鞭炮可驅邪祟。
弘時看着這一地紅紙,想想阿瑪對新出生的弟弟那樣在意,他心裏就不得勁。
且說,弘時同學這會子就不得勁,還不知,他不得勁的日子在後面呢。
——
展眼新歲已至,正月初一。
這一日,所有年滿十五入朝站班領過差事的皇子和朝臣勳貴們皆排的整整齊齊,來與皇上賀新歲。
這是康熙六十年的第一天。
六十為一甲子,多少人都活不到花甲之年,而康熙爺卻已經禦極六十載。
禮部已經做好了準備,在今年,朝中必要有許多慶賀典儀。
然而,就在這康熙六十年的第一天,康熙爺就扔下一個重磅消息。
接受完群臣拜賀,康熙爺便提及,今年自己準備派皇子出關代為祭拜三陵。
且說這三陵,乃是努爾哈赤的福陵、皇太極的昭陵以及清遠祖的永陵。①
因當年大清皇室還在艱難的創業期,在關外游蕩。祖宗死了當然也不能放着等打完天下再埋在京城,自然是就地選址葬了,于是這清三陵就遠在關外。事關祖宗們,皇上自然每年都要親去祭拜。
今日朝上,康熙爺便道,自己如今到底是小七十的人了,今年便準備遣兒子去祭拜先祖們。
朝上先是一片震驚的寂然,之後就不可抑止的如潮般驚動起來。
正所謂,“國家大事,唯祀與戎。”
祭祀之事,在帝王家是具有象征意義的,何況是祭拜大清祖宗這三陵。
十多年前,太子還在的時候,皇上有事不便行,都是太子代祭,如今皇上要命哪位皇子去?
康熙爺好似渾然不知自己說的這些話有多驚人,他老人家安坐龍椅,看了半晌下面的兒子和群臣百态,根本沒有一點民主,讓大家商議的意思,直接就宣布了結果:遣皇四子胤禛、皇十二子胤祹代他老人家祭三陵。
十二爺胤祹在朝上懵了一下,但很快跟所有人一樣,把目光集中在他的四哥,雍親王身上。
朝臣們都心裏門清:十二阿哥的生母定嫔位份平平,十二阿哥本人幼年則是被蘇麻喇姑撫育的,那是為極有智慧的老人。被她撫養長大的十二阿哥,那叫一個安靜随和,不理政事,全身心投身于書畫事業中。
這兩年皇上讓十二爺在內務府辦差事,他也認真幹活,但凡事不湊前。可以說這是個不怎麽出錯,但也絕不算出色的阿哥。
起碼在康熙爺這一堆龍子裏不算出色。
這回十二阿哥明顯就是陪襯的,主祭的必是皇四子。
是雍親王。
九爺在朝上,按序站在他八哥身後,就看到朝服中,八哥的手指蜷曲了一下。
他看着出列領旨謝恩的老四和十二,心裏火燒火燎的。
散朝的時候,許多朝臣看着雍親王的眼神都不一樣了,只是雍親王為人素來冷淡些,不熟的還真不敢上去套近乎。更有許多燒的不是這個竈的臣子更是要先避開他,回頭去找自己燒的‘竈’商議今日之事。
四爺還沒走出多遠,乾清宮的小太監就來請他了。
——
康熙爺這次備的是鹹奶茶。
“坐。”
見老四在下頭請安,康熙爺擺手叫起,指了下首的椅子。
父子二人就祭陵之事說了半晌。當然主要是四爺在說,他方才初步拟定了出行的腹稿,康熙爺半閉着眼睛聽着。
聽老四事無巨細的在下面彙報完,康熙爺才睜眼道:“你從小就這樣,是個操心的命。”
四爺已經習慣了:最近皇阿瑪總是跟他回憶過去。
他也樂得做小時候的四阿哥,做皇阿瑪當時的小兒子。
感慨完後康熙爺,食指點了點桌上的兩個折子:“你瞧瞧這個。”
梁九功悄無聲息的上前拿了折子,再躬身遞給雍親王。
四爺接過來:是年羹堯與平郡王分別上的折子。
折子出自兩人之手,內容卻大同小異。都是上谏請皇上在藏邊設立辦事處。年羹堯則更激進些,直接道:天無二日,藏邊的藏王實沒有必要。不如取消掉,換朝廷官員來此建衙,全方位接管藏邊。
康熙爺見老四看完了,就問道“你覺得如何?”
四爺點頭:“兒子覺得正該如此。”
從前藏邊偏遠,自立為王,算是半獨立。朝廷一時犯不着攻打,也沒有精力去攻打。
可這回不一樣啊,借着打準噶爾叛軍一事,清軍都直入藏邊了,既然軍隊都駐紮過去了,憑什麽要把這一地的統治權再還給什麽當地的‘王’。年羹堯這個提議,也很符合四爺的想法。
康熙爺滿意點頭。
他老人家做了六十年皇帝,又不是做了六十年的慈善家。
這種費勁巴力給別人幹活,還不收工錢,那是不能夠的。
“朕準備設西藏大臣與噶布倫,從前這藏王,就取消了吧。”康熙爺倒是沒取消冊封藏邊喇、嘛的地位和尊號。
實在是已經碾壓了人家的統治,就別碾壓人家的信仰了。一下子壓制的太厲害,只怕出事。
但就算這樣,也得防着戰事再起。
畢竟當日藏邊跟朝廷求助可不是這麽想的。相當于一個人家裏進了強盜,他跑去找強大的鄰居幫忙,那是指望着鄰居仗義出手把強盜趕走的,誰成想這個鄰居确實是把強盜趕走了,然後自己就住下來鸠占鵲巢開始當家作主了,擱誰誰心裏沒有意見啊。
四爺将自己的擔憂略微提了提。
康熙爺很平靜:“所以朕命平郡王繼續駐守藏邊,年羹堯亦是如此。”他頓了頓,目光深邃起來看着四爺道:“還有,朕準備讓胤祯回藏邊去再穩一穩局勢,到底他是皇子,又跟臣子們不同了。”
四爺心劇烈的跳起來。
皇阿瑪要讓十四回去,而并不是讓他入六部學習朝政!
四爺低頭:“兒子們自然一切都聽皇阿瑪的吩咐,各司其職,都是為皇阿瑪辦差事。”
康熙爺不免感慨道:“十四這孩子,是個将才啊,又是你親弟弟,自是不錯的。”
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康熙爺想起了自己的兄長福全。
也想起當年的自己,正是少時登基。論嫡自己不是,論長自己也不是,上頭還有個哥哥福全。這位兄長卻毫無怨言,鞠躬盡瘁的給自己辦事,為人更是謙卑。
甚至年幼的時候,福全兄長就告訴皇阿瑪,自己願為賢王。②
兄長也确實做到了。康熙爺至今想起已然過世的福全兄長還會覺得溫暖,他像一塊可靠的堅石一樣一直在自己身後。
看着眼前老四,想着他與十四一對兄弟,康熙爺不免又想起,康熙二十九年的時候,自己打噶爾丹,也封了福全‘撫遠大将軍’。
簡直像是宿命的輪回。
以後老四和十四,也會做一對自己跟福全這樣的好兄弟吧。
況且他們兩個,又是兄長為皇,弟為王,且是同父同母,自然就更會親密順當。
康熙爺不是不知道十四素日跟老八走的近,但在他心裏,有什麽比同父同母血脈更親近的呢?
到底老四只有這一個親弟弟啊。
——
可見哪怕是至親父子倆人,也沒法心有靈犀。
四爺若是知道康熙爺的想法,只怕要立刻在心內反駁:不,十三才是我弟!
康熙爺讓老四告退後,不免又陷入了對福全的懷念。他起身往暖閣去,那裏挂着幾幅他心愛的畫。
有當年順治爺手把手教他射箭的畫,有親額娘坐在廊下抱着年幼的他的畫,還有一張,就是福全過世後,他命畫師畫了一張,兩人并肩坐在桐樹下的畫。
倒不是福全生前,康熙爺拿皇帝架子不肯一并作畫。而是福全為人很謹慎,再不肯跟皇帝并肩而坐入畫。甚至直到死前,康熙爺去探望他,福全在榻上仍舊自稱奴才。
康熙爺的眼睛有些濕潤。
算來,兄長已經走了十八年了。福全過世的時候,才五十歲。
而自己如今卻馬上要七十歲了。再過些年,他們兄弟終會在地下重逢。
康熙爺的目光再次看向順治爺的畫像,心道:皇阿瑪,兒子做了個好皇帝,來日見了你,自問心無愧!
——
且說四爺雖知道康熙爺的期許,是盼着他跟十四兄友弟恭,做一對親厚的兄弟,然他心裏對十四即将要回藏邊,還是十二分的滿意:快走吧。
心情甚佳的回到了府裏,四爺先去看了看小兒子。
他逗了逗孩子的下巴:“這孩子真是福星。”他才出生,自己就得了出關祭陵之行。
雖說當日皇阿瑪私下暗示過自己的立儲之意,但跟這回在朝上暗示,還是天壤之別的。
年氏在旁笑容溫柔如水:“都是爺多年的苦心,跟這剛出生的孩子有什麽關系?”
四爺倒是認定了:“自是有關系的。”
然後拉着年氏來到桌前:“朕給孩子想了個好名字。”他在紙上寫下‘福惠’兒二字。
年氏神色一暗:“爺,要不還是等種痘後,再給兒子起名字吧。”
四爺知道她是想起了福宜早早有名字,卻又夭折,就安慰道:“這是小名,咱們先自家叫着無妨的。到時候孩子種過痘,我再請皇阿瑪起個大名。”
出生才幾日的七阿哥就有了名字不說,雍親王府更是流傳着四爺的話:這孩子是個福星。
以四爺如今對府裏的掌控,這話能傳出來,自然是他默許甚至樂見的。
——
宋嘉書聽弘歷說起‘阿瑪對七弟真是喜歡,這樣的話都肯說’時,不由一笑。
只誇是福星算什麽呀,四爺也就是如今不能當家作主,等他當了皇帝,誇起人來真是讓人沒眼看。
比如流傳青史,讓後人都不免咋舌的——四爺把他親愛的十三弟誇成“宇宙全人、天神”,那才是四爺的誇人呢。
這會子只說福星二字,實在還算是克制了。
宋嘉書知道四爺的秉性,愛恨十分分明。
于是對弘歷就有些擔心:都是做兒子的,見阿瑪偏心成這樣,想來心裏不好受吧。
看着額娘關懷的眼神,弘歷白淨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額娘,七弟這樣小,又有福氣,我們這些做哥哥的該比阿瑪還疼他才是呢。”
弘歷的神色看起來真誠極了,直到說完才眨了眨眼,母子倆會心一笑。
他知道該怎麽做是對的,這就夠了。
宋嘉書:好的,我不用擔心了。
母子兩人笑過後,宋嘉書又想要囑咐:“還有弘晝……”只怕那孩子直性子,露出什麽形容來。
弘歷都不用宋嘉書說完,一口截斷:“額娘也放心,五弟是天真活潑的性子,但不傻。何況還有我在旁邊瞧着呢,總不會有事。”
這府裏要有一個傻阿哥的話,那絕對不是弘晝。
母子倆邊說話,宋嘉書手上邊翻看着一套冬衣。弘歷便問道:“這是阿瑪要出關,額娘準備的衣裳嗎?”
四爺凡出遠門,福晉自然會給四爺準備行裝。只是福晉在這上頭頗為大度,會各院問問,有沒有什麽要奉給四爺的,一并帶上就是。
福晉這一問,各院真是沒有也得有了,不然顯得多不重視啊。
宋嘉書也帶着人連夜趕了一套衣裳,不出挑也不落後。
她見弘歷問,就點頭道:“是給你阿瑪準備的。”
擡頭莞爾:“年節下,額娘還帶着白寧給你做了一套,在你小書房裏,我都給你打好包袱了,一會兒回前院記得帶着。”
如今弘歷也十歲了,如無意外,是不能在後院過夜了,頂多回來吃個飯請個安。
可宋嘉書還是保留着西邊一側,作為弘歷的起居之所,一點未動。
弘歷笑眯眯:“多謝額娘。”然後起身:“額娘我回去了,阿瑪臨行前只怕還要查我們的功課。”
宋嘉書點頭:“去吧,別太累着。”
——
回到前院後,弘歷打開了彈墨花紋的包袱。
他拿起額娘給自己備的這套衣服,從花紋到針腳甚至是擺放,比起方才額娘要給阿瑪的那一套,明顯的更加精心。
弘歷喜歡寶藍色的衣服,他的手擱在這熠亮的布料上:額娘永遠記得他喜歡的顏色和樣式,也知道他喜歡把領口做的圓松一點,不喜歡板正的卡在脖頸上。
在這金玉滿堂的王府裏,只有他與額娘才是真正的彼此依靠,記得對方。
弘歷收起了這套衣服,繼續去研究千叟宴的舊例流程,這是阿瑪交代的第一件要緊差事。
作者有話要說:
①在山海關關外還有三座,努爾哈赤的清福陵、皇太極的清昭陵以及清遠祖的清永陵,統稱"清初三陵,也被稱為“關外三陵”。
②福全幼時,順治帝問其志,他說:"願為賢王。"。福全也做過“撫遠大将軍”。文中提到的康熙爺跟福全的畫像,也見于清史稿。福全死後,康熙帝特命畫工精繪一張像,為康熙帝與福全并坐于桐蔭之下,示手足同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