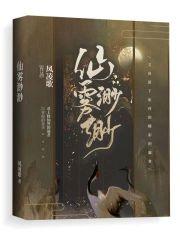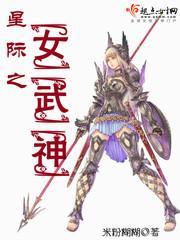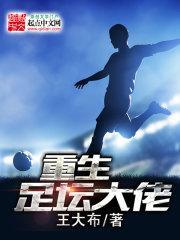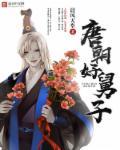第1章 女主出場
②無三角戀。劇情滿點,感情慢熱。
③建議收看時點擊左下角【設置】,将【行距】拉扯到最大,給您最絲滑的閱讀體驗! 2500年的冬天,溫度似乎比去年更低一些。
冬天愈冷,夏天愈熱,這是近百年來的大趨勢了,不過倒也還沒到相鄰兩年有明顯差異的地步。
所以這應該是托馬斯的錯覺,是心理作用。
他快步穿過空曠的操場,刷卡進入奇斯卡大學的校實驗室,恰恰好卡點到——果然他的師弟師妹們都請假了。
他多少有點後悔,早知道他也不來了,這種天氣睡覺最香。
“早上好,皮克西西教授,”他一邊脫外套,一邊和自己的導師打招呼,“希望今天實驗順利,讓我的論文可以早日收尾。”
這時他摸着自己冰冷的袖子,才發現今天這格外的冷并不是錯覺。
是他袖子這塊兒的制熱器壞了。
“啊,是的,希望如此。”皮克西西先生盯住自己的反應釜,頭也不擡地回應。
這是皮克西西先生的常态,真忙起來他甚至連飯也不吃——不僅是正常的飯,就算是給他準備了太空部隊吃的膏管餐,他也懶得擠兩口。
托馬斯用力揉着自己凍僵的胳膊。這條胳膊已經完全沒有知覺了,他真心希望狀況沒有糟糕到需要去醫院。
這時,皮克西西先生的實驗似乎恰好告一段落,他松開氣閥,摘下防護鏡,擦了把汗——尤其是好好擦了擦耳朵之間的縫隙。
再一回頭,看見托馬斯。
皮克西西霎時驚喜,就好像剛知道托馬斯進來似的:“托馬斯,太好了,我正有事要找你說呢!”
托馬斯一僵——不會吧不會吧,不會是又有什麽額外工作吧?
Advertisement
皮克西西一貫是那副笑眯眯的表情:“托馬斯,以你的能力,我相信你今年一定可以如期畢業。所以如果你工作沒定的話,考不考慮賞光來我的研究所?”
托馬斯愣在原地,他胳膊一下就不冷了,甚至還有點熱了。
因為皮克西西先生的研究所還有另一個名字——“國際聯邦化學研究所”。
這是2500年,“土地荒漠化”、“淡水資源缺乏”、“植被減少”這些問題更加突出,“生态環境惡化”與地球上的每個人息息相關。
不過,這也都是喊了上百年的口號了。
喊得人都麻了。
科技确實也在不斷發展。“海水淡化”可解燃眉之急,但是如果淡水資源再進一步減少就難辦了;“防沙牆”能抵擋一部分風沙,但居住區還在縮小之中;衣服夾層裏夏天制冷、冬天制熱,但機器難免有失靈的時候。誰能想到都26世紀了還能有凍死的人呢。
尋找宜居星球成了一個永恒不變的話題,但是其實仔細想想——要是真有那麽合适的宜居星球,又哪那麽巧就輪到我們地球人開開心心搬過去呢?人家自己就沒人住嗎?
“國際宇宙調查團”一批一批地派專家去探索宇宙,終于在約莫一百年前,有了突破性的成就。
那一天,我們的調查員遇見了不屬于地球的飛行器。
由于是第一次見,互相之間都比較緊張,直接就開始交火。
于是地球史課本中就有了“第一次星際大戰”。
但是那時,雙方都沒有專業的太空部隊,所以戰争規模其實不大。而且在戰亂的過程中,雙方也在加強了解,這麽一了解就發現了一件尴尬的事——大家科技文明發展的水平和速度,其實都差不多。
甚至長得也差不多——都是頭部、軀幹、四肢,眼睛、鼻子、耳朵、嘴。
最大的區別是,似乎因為他們那個星系的恒星輻射光和太陽光成分有本質區別,所以他們膚色偏綠。
而由于彼此之間都沒有壓制性優勢,于是開戰1年零7個月以後,雙方停戰議和。
地球人給他們的星球按音譯取的名字是“達魯星”,所以按理應該叫他們“達魯人”。
但是日常生活中,常有人用“青蛙人”來代稱他們。這帶有貶義。
在東半球,有時會戲稱其為“打鹵人”,這就不是西半球可以理解的了。
地球人和達魯人之間有沒有生殖隔離,這不得而知。因為雙方之間的交流目前僅限于高層對話,還沒有展開民間交往,甚至沒有開始商品交易。
這意味着如果你不隸屬于太空部隊,也不屬于星際高層,那麽其實這些外星人的突然出現,對你的生活影響不大。
倒是“新人類”的出現,比較令人不适。
“新人類”是比較好聽的說法,也是現在為了維護穩定而規定的官方名詞。在傳統史書中,他們被稱作“變異人”。
這就得追溯到更早以前,比“達魯人”出現還早得多。
由于廢水排放、海洋污染、輻射擴撒,不僅帶來了一系列的疾病,而且還出現了一批“變異嬰兒”。
他們有些自出生起便失去行為能力,有些則可以正常地學習生活,有着正常的大腦,甚至有的智商還比普通人高一些。
但是歸根到底,他們和正常人不太一樣——有着比如八臂、六耳等奇異特征。
還有些比較讓人不能接受的變異方向,此處不一一列舉。
總之,其中部分輕微變異的嬰兒長大後,如正常人一般娶妻生子,産生的後代便是如今的“新人類”。
他們難免是受歧視的弱勢群體,但同時他們也是可憐的受害者。
于是各方輿論又各有不一——
有人認為應當打破歧視,讓新人類不再受人白眼。
有人認為是新人類的祖先用最惡劣的方式破壞環境,使那裏成為變異區,而且從未道歉,所以他們不應受到同情。
但也有人說,那個年代國家觀念還很鮮明,那場災難其實是一國殃及周邊各國,所以新人類中還是有很多是純粹的受害者。
至于新人類本身,一些人為了過上正常的生活,通過手術等手段截去了自己不正常的部分;一些人用衣服或者頭發掩蓋了自己的變異器官;還有些人頭鐵地不去隐瞞,認為自己從未做過錯事,便無需在意別人的眼光。
當然還有些新人類相對幸運,他們的變異部分在內髒等器官中,所以表面看起來與常人一般無二。
但是不論是通過僞裝還是手術,都無法改變基因,于是又出現了一系列新人類“騙婚”案件——受害者明明與看起來正常人的結婚,但胎兒卻明顯是“新人類”。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新人類”的身份證件上會有特殊标注,婚前體檢也會有專門項目。
有人認為這種做法加劇了對“新人類”的歧視,但也有人認為這恰恰是為了“新人類”更好地被人接納,只有“新人類”相關犯罪減少,才能更好地融入人類群體。
總之就是各說各的理。
但反正不管怎麽說,架不住“新人類”已經越來越多。雖然還是少數群體,但是走路時迎面碰上一位不是什麽稀罕事,到公司報到第一天發現領導一邊倆耳朵也不是什麽稀罕事,正常有禮貌的人也沒工夫多看。
就像皮克西西先生,他的耳朵是蝴蝶翅膀狀的,尖尖的主耳下有一個小小的副耳,倆耳朵中間很容易藏污納垢,所以他平時很注意這個區域的清潔。
托馬斯看時間長了,還覺得挺可愛的。
那麽皮克西西先生為什麽不留個長發,把耳朵遮住呢?
因為他是個光頭。
或許這就是聰明絕頂吧,他也不過就區區50歲出頭而已——不過其實他的頭發在30歲那年就掉得一根不剩了。
好在他也不在意這些細節,他已經把自己的人生完全獻給了科學研究。
他有着異于常人的高智商以及後天的勤奮,“鐖元素”的發現和對于病毒殺滅的研究讓他成為了當之無愧的業界領袖、國聯化研所的所長。
皮克西西先生其實就是一個受人尊敬的“新人類”的典範。
至少化學專業的學生考試前,是必定要拜拜他的雕像的,畢竟教科書上有他名兒。
托馬斯也是千萬人中擠破頭,才成為了皮克西西先生的弟子。
他倒也沒有什麽拯救地球的宏願,就是單純很喜歡化學——既然化學可以創造世界上沒有的東西,那麽稱化學家一句“造物主”不過分。
近百年來環境惡化,化學背的鍋不算少,但但凡受些教育的都明白這世界不能沒有化學研究——尤其是達魯人出現以後,科研簡直成了競争,誰都怕達魯人的科技水平超過地球,于是各方向科學家的地位進一步上升。
托馬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了世界頂尖的奇斯卡大學,拜入皮克西西先生門下。于是比起旁人,托馬斯對這位大名鼎鼎的化學家就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除了世人皆知的極致的嚴謹認真以外,他還是一個無可挑剔的導師。
他一向幽默又溫和,總是笑眯眯的一副沒什麽煩心事的樣子,還很關心學生們的科研進度。
幹化學科研這行的往往壓力很大,因為不易出成果,而且還死活找不出失敗的原因。每當托馬斯他們自我懷疑、泫然欲泣的時候,皮克西西總是以一副十分歡快的形象出現在他們眼前,詢問他們是否需要幫助。
每當這時,托馬斯他們就稍稍好受一些,從焦頭爛額的實驗中獲得片刻剝離——哪怕問題并沒有解決,但至少天還沒塌。
所以有時托馬斯覺得,一個導師最重要的特質,或許并不是嚴格、仔細、溫柔或是博學,而是快樂。
皮克西西手下的弟子們都知道導師會在畢業季直接挑人進研究所,也都十分希望自己是那個幸運兒。
最終是托馬斯被這份幸運大獎砸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