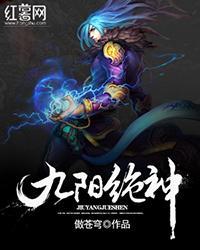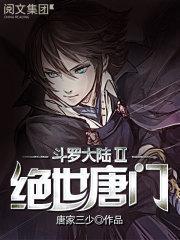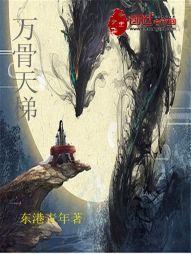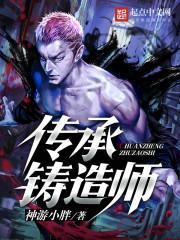第22章 用度
“我查閱賬目,發現這些年來,宮中用度,着實驚人。不當使錢的地方,想方設法找到使錢的名義。能用萬錢解決的問題,必定報個十萬二十萬,絕不往少處想。這麽多年來,不知虛耗了多少錢帛。”
崇宜迩緩緩說起了她擔任尚宮以來的所見所聞,“主上信任宜迩,讓宜迩擔任尚宮,宜迩不敢負重托。所以,今日向主上請命,請主上允許宜迩革除宮中之弊。”
宮中的奢侈,神熇是知道的,如今換了一位尚宮,正好整頓整頓,于是就道:“這件事,請師姐多費心。”
私下的時候,神熇還是喜歡喚崇宜迩一聲“師姐”,有些稱呼一旦開始使用,就很難做出改變。
每一次改變稱呼,都意味着各自心态的變化。神熇在這方面,足夠敏銳。
不過,崇宜迩的建議只是得到了神熇的支持,要想真正實施,還得說服那些女官,尤其是以唐顯如為首的女官。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得燒得旺旺的,否則,後邊就沒火了。崇宜迩深知此理,她亦需表現出新尚宮的魄力。
“崇尚宮不過是看了些賬本,就要因此變革制度,未免太草率了。”楊幸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她當然代表唐顯如的意思。
“變革制度?我可沒這個意思。”崇宜迩若有似無地看了唐顯如一眼,緩緩道:“主上深知民間疾苦,不樂以奢侈之道治國,而崇尚節儉,當然應從昭明神宮做起。我等身為女官,為主上分憂,有何不可?”
楊幸冷笑道:“我等愚昧,不如崇尚宮體解上意,只是敢問崇尚宮,若要做些節儉的樣子,當從那一處下手?”
崇宜迩道:“主上每日之膳,窮盡珍馐,一餐可供千人飽食。諸位的膳食,也都是按着官品供給,用的是宮中之物,不比公侯之家差。依我看,當從減膳開始。”
楊幸道:“我等女官,飽食足矣,不敢有二話。只是,主上乃天下之主,舉國家之力以供奉之神明,怎麽能跟我們這些人一樣?”
楊幸離開座位,站在大殿中央,面向崇宜迩,接着道:“聖母遺訓,神尊威儀,不可減損。崇尚宮欲減主上之膳,就是損害神尊威儀,其罪可誅!”
她說着,忽然疾言厲色,把“聖母遺訓”都搬了出來。遺訓這種東西,這些年也有濫用的意思。
先代諸神說過的話,都可稱為“遺訓”,今人引來壯膽,卻往往忽略遺訓與遺訓之間相互矛盾的地方,乃至于自取其辱。
“聖母在位三十年,著布衣,居草屋,食野菜,與百姓同苦樂,何嘗失了神尊威儀?”崇宜迩目視楊幸,朗聲道:“楊幸,你不學無術,曲解聖母遺訓,又不能明白主上苦心,你該當何罪?”
Advertisement
這一番責備,把楊幸說得花容失色。她看着崇宜迩,嘴巴動了動,說不出話來。
“崇尚宮教訓的是,楊司膳,你還不向崇尚宮請罪?”
唐顯如開口了,楊幸這才回過神來,極不情願地向崇宜迩賠罪,崇宜迩卻道:“楊司膳于我,本無私怨,今日為公事起争執,自然不該往心裏去。只是,楊司膳妄用遺訓,終究不大妥當。”
楊幸聽得前邊的話,以為崇宜迩要作出一副大人大量的姿态,誰知還有後話。她也就黑着臉,慢慢地退回到座位上。
“崇尚宮所言甚是,至于減膳這些事,也請崇尚宮一并處置。我等神宮女官,謹奉崇尚宮之令。”
唐顯如這麽說了,就說明她不會在表面上做反對的事,但暗地裏如何,誰又知道呢?崇宜迩躊躇滿志,壓制住了一衆女官,卻不曾想,會是一個想不到的人壞了事。
這個人就是高君岄。
高君岄侍奉在神熇左右,崇宜迩大力提倡節儉宮中用度,表面上已經起了作用,神熇為此欣喜不已。
“你怎麽了?”
對于身邊之人的情緒變化,神熇還是很敏感,她還作出了自己的猜測,“唐顯如為難你了?”
唐顯如跟高君岄看不對眼,這是宮裏公開的秘密,神熇當然知道,所以也就很直接地問了出來。
神熇并不喜歡唐顯如這個尚宮,所以,當然不能讓身邊的人受唐顯如的欺負。
“奴婢看着主上節衣縮食,不勝感慨。只是,主上已如此,百姓仍有餓死在街道上的……”
高君岄說着說着,欲言又止,竟抽泣起來。
“你說什麽?”
随後,高君岄将神熇引到北苑,二人著便裝,悄悄從一扇小門出去,轉了個彎,就看見成群成群的百姓躺在街道上,有老有小,都是衣衫褴褛,多半面帶病容。
“主上節儉,宮裏連殘羹剩飯也沒有了嗎?”
一個老人這樣大呼起來,随即有人附和,罵聲不絕耳。
神熇側耳一聽,大半是罵崇宜迩的。
回到宮裏,神熇就問高君岄是怎麽回事。
“每日,宮中的殘羹剩飯都會運到外邊去。稍好些,就被那些有門路的人賤賣了。那些次等的,就丢給城裏的乞丐。久而久之,就在北苑外邊聚集了上萬人。”
“上萬人?”這個數字,神熇很驚訝,“這些人從那冒出來的?”
高君岄解釋道:“都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不願自賣為奴,又沒法謀生,只能靠着宮裏的殘羹剩飯活下去。其中也有好吃懶做的,但大半都是良善百姓。”
“這種事,多久了?沒人管嗎?”
“奴婢尚未入宮,就聽說過了。之前也有大臣上書,是百姓在北苑之外乞食,有傷國家體面,要衛将軍和神都尹妥善應對的。然而,百姓散了又聚,始終不肯離去。他們又不是畜生一般的奴婢,神都尹也沒辦法。世間一長,大家也就視而不見了。”
神熇面色凝重,若有所思。
高君岄知道自己已經說中了要害,接着道:“崇尚宮所為,當然是好事。只是,崇尚宮生來富貴,未必知民間疾苦,只怕不知道還有這種事。”
忽然,高君岄撲通跪下,叩頭道:“奴婢受主上大恩,有些話,不敢不說。”
她擡起頭,淚眼婆娑,“這上萬百姓,都是主上的子民,一旦餓死在宮門之外,讓世人如何看待主上?後世又該如何看待今日?”
這話已經說到神熇心裏去了,這世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希望留下美名的,何況是神尊?還有,讓上萬的百姓活活餓死在宮門外邊,這哪裏是盛世?這簡直就是亂世。
崇宜迩想要做的事,夭折了。
與崇宜迩要革除神宮弊政的舉措相比,出兵讨伐北狄也不容易。
“北狄,百年宿敵,如今,正應趁其內亂,一舉破之,可得數十年太平!”
宣本頤相貌英武,神情凜然,在大殿上振臂高呼,穆剡的氣勢也被比下去了。雖然如此,反對的人還是不少。
“主上新繼位,北郡之亂才平定,正宜無為而治,以示太平。出兵,不合時宜。再說了,北狄雖然屢屢寇邊,不過掠奪財帛,未曾深入國家腹地,不過肘腋之患,奈何虛耗國庫,驅甲士赴死?”
這是穆剡一派提出的主張,與宣本頤針鋒相對。
穆剡一夥的話,總是戳神熇心頭,她也習慣了,源弘謇的表現才令她驚訝。
源弘謇是贊成出兵的,他說了一通大道理後,又當面指責反對出兵之人:“勝則開疆拓土,敗則窮兵黩武,衮衮諸公,誤國家大事!”
罵完之後,源弘謇又質問道:“諸位腳下的土地,不是先輩一寸一寸打下來的,難道還是仇敵送的?”
這質問提及往事,激起了神熇的雄心壯志。
出兵讨伐北狄的事,到底是定了下來。
神熇回到宮中,處理政務也覺得鬥志昂揚。當晚,她在寝宮讀書,正是悠閑之際,刺客卻殺了進來。
毫無征兆,簡單粗暴。
成時郁保護着神熇,一直退到安全的地方。因為那次雲臺的事,神熇身邊的衛士增加了一倍,随時聽候宣召的衛士也增加了一倍。所以,一有動靜,就有上百人圍過來。
在混亂中,神熇似乎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當她退到安全之地時,想起了那個人的名字——韋鳶。
韋鳶确實是來了,她作出這樣的決定,有玉石俱焚的意思。真正到了那個時候,她和手下人已經被衛士團團圍住,再也見不着神熇的影子了。
什麽“玉石俱焚”,要死的人只有她這樣的刺客而已。韋鳶不甘心,穆輯那小子只答應送人進來,對接應的事一個字也沒提。在這樣的情況下,韋鳶就是不甘心,又能怎麽樣呢?
韋鳶玩起了困獸之鬥,她這一鬥,居然出了牢籠。
“什麽人?”源時慶發現牆那邊閃過一個身影,就追了過去。
那個身影倒下了,源時慶靠近的時候,嗅到了濃濃的血腥味。
随從舉起火把,照亮了那張美麗的臉,雖然帶着血污,源時慶還是能認得出來。
是韋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