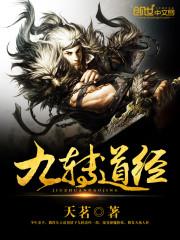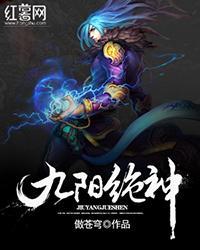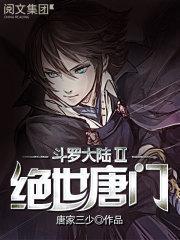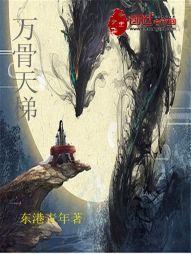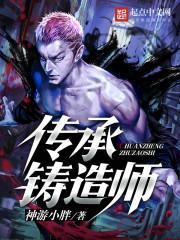第87章 (8)
兒……”何老爺滿臉疑惑,“她不是去做什麽大祭司……”
“什麽大祭司啊,我說你不懂吧你還不信,”金桂狠狠地推他,“那大祭司吧,人家是個大官,一般人做不了的——咱閨女那就叫祭司,那是要到廟裏當姑子去呀——你快勸勸她去吧啊你啊……”
“你婦道人家懂什麽?”何老爺滿臉不以為然,“人家術士的祭司那就是個官兒:琴兒不是說了嘛,一般人還當不了呢。那地方叫廟,其實它就是個衙門——咱閨女是去研究學問的,你看這逢年過節不都能回家,跟姑子哪搭得上半文錢關系。再說,那天道君老爺還講呢,說是這回什麽祭忠魂的裏面就有那麽個祭司,好像是個姓蕭的,說是去年咱江都最大的一個官兒,除了皇上誰都管不了那種:你看這人都死了禮儀還可風光呢,咱全城老百姓都得給披麻戴孝——哎琴兒?”
何琴一身缟素地自內室出門,眼神空洞而哀傷,她長跪在廳前向父母辭行:金桂一下子就哭得呼天搶地,而何老爺不由皺起了眉頭——
“琴兒你怎麽穿這麽一身?跟個小寡婦似的,”他說,“國喪歸國喪麽,又不是什麽五服至親,穿成這樣做什麽?”
“回爹爹的話,女兒是為蕭先生服孝,”何琴說得有些麻木,“古人言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女兒身受蕭先生衣缽,就自當依至親之禮相待。”
“哦……”何老爺還有些沒轉過彎來,“你穿成這樣子去做官,衙門裏管不管呀——嗯?明天才國喪呢不是,聽爹的話,第一次去衙門,穿得像模像樣的。”
“回爹爹的話,女兒為蕭先生服孝,乃是衣缽弟子分內之事,”何琴語調平靜地說,“請爹爹不必擔憂,術士習俗這般,共事同侪,俱是能夠理解的。”
“哦這樣啊,那你就去吧,”何老爺一聽如此語調就變得歡快起來,“在衙門裏好好做事,給咱家老祖宗争口氣哈——唉,你說你哥他怎麽就沒你這麽出息呢——這女兒麽,終歸是別人家的人啦……”
他唠叨着就稀裏糊塗地放她走了,而金桂又開始呼天搶地。“哎呀呀,我上輩子究竟是造了什麽孽啊,”她就越哭越傷心,“姓蕭的我上輩子是欠了你什麽呀這——我好好一個妹子被你拐得魂兒都沒了,現在又害我家閨女到廟裏給你守活寡——當家的我這上輩子是造了什麽孽啊我這……”
“哎等等,”何老爺好像想起了什麽,“你說哪個姓蕭的?不會就是咱都得給服喪的那個什麽大祭司吧?”
“我哪知道啊,”金桂委委屈屈地說,“我說那小子你肯定有印象的,我剛過門那年芷蕭還跟他鬧私奔來着。住長幹裏、頭發髒兮兮,又幹又瘦,一天到晚穿件黑衣服……”
“是不是個子高高的,頭發剪得半長不短,一天到晚苦着張臉像別人欠了他的銀子——”
“是啊,你想起來了吧?”
“啊是他呀!”何老爺憤憤地一拍大腿——“這不就是那個大祭司嗎——哎我說金桂咱當初可真傻呀。若是那時候就讓芷蕭跟了他,光看那撫恤家眷的銀子——喂呀,好歹咱現在,也不至于過成這樣啊……”
【全本終】
Advertisement
2012年4月25日初稿于南京
7月26日二稿于煙臺
9月12日定稿
☆、後記 我眼中的世界
《天牢》寫完了,上下兩卷六十多萬字,寫得自己險些要瘋掉。說實話動筆寫《天牢》某種程度上是出于想要挑戰的心理,一方面規模宏大、時間長人物多,前後伏筆線索無一不需要時刻注意,另一方面主角不太對胃口——熟悉我的讀者會發現我擅長寫奇葩和變态,花漸落鐘離如意甚至本文中的路修遠姬無悔楚素商之流——像阿殘這樣的英雄芷蕭這樣的姑娘,一個是癡心到死不回頭的書呆子而且專長還是藥劑,平日愛好看天書,讷于表達——而且我第一次以正常男人當主角有點吃不消啊吃不消;另一個普通優秀女青年的代表,雖然法力高強一身正氣卻偶爾會撒小嬌吃小醋,會為愛情私奔也會理智地選擇自己的最終道路,尤其是,還是個超有母愛的好媽媽(相對比的是曼吟,人家寧可被絞心咒也不要小孩子,詳見第三十章《預言》),所以在創作過程中經常會有想死的感覺,好像如果沒有曼吟楚素商這群奇葩這故事我壓根寫不下去了。不過客觀點看,也許這樣的角色在多數讀者的眼中會更可愛,并且出于創作廣度考慮世界更多是由普通人組成的。我寫《天牢》是在說我眼中的世界,從而把普通人當主角也不過必然趨勢。
這是一個架空的年代,或者說,是我架構的一個我以為理想的年代:列國林立并不重要,魔教橫行也只是外在因素,我所謂的理想,其實是一個文化氛圍。在前言裏我曾說,不太古代也不太現代,就當它近代好了——一方面我的術士們有一種很西方化的思維模式,自由、民主,講求科學(如果是純粹的中國古代不會出現藥劑這類學科還要實驗考據的情況),生活向前看,皇帝名存實亡——至于國人被這種風氣耳濡目染因而入鄉随俗,既堅持老一套另又要向大人們妥協以圖安生,這才是中國人的特性。而另一方面,江都的生活習慣很傳統,尚士風、穿漢服(盡管不蓄須發),以風雅為美,寫不好字會被人笑話,清曲和古琴是最受人尊敬的藝術,尤其是,文言不曾被廢除,盡管大家平日裏都講白話,正規的學問考據和書信來往則俱用文言——這種生活方式可能當代中國人已經無法想象了,我也只是想想而已。另外大環境沒有外部幹擾,說來無非是江河流域的這片土地,列國林立比較好管也比較好寫,并且喜歡窩裏鬥也是中國人一大特征,盡管十國友好來往互不侵犯,諸君且試看小小一個術士學堂兩個道就能鬧成這樣。有裏面不打外面,難道這就是所謂“攘外必先安內”?
我一直不願回避這個事實,便是直到現在,盡管國人的思想日趨開放、民智已大規模開啓,可所謂“劣根性”在國人身上仍随處可見。看熱鬧的打醬油的,混一天算一天的,見不得別人超過自己的(蕭殘深受其害),還有抄襲山寨(要不是因為這人物太典型我才懶得折騰原著裏的洛哈特),成家要孩子至今被多數人自覺不自覺地視為義務,還有考試……所以《天牢》裏的世界符合我的理想卻并不完美,魔教橫行不過外因。這些不完美是去不掉的,正如每個人物都有他致命的軟肋。蕭殘看似正邪不分實際意志堅定、芷蕭雖然堅持正義其實內心搖擺。書呆子蕭殘和沒頭腦慕容楓其實哪個也不壞,游戲人生的姬天欽和糾纏不清的楚寒秋本質都很美好;東君和曼吟不同程度地控制(或說玩弄)着他人的命運,而姬天璇和仇戮卻有自己最真實的一面——誰也不是壞人,正如誰也不是好人。我們生活的就是這樣一個世界,所以從一開始我就說,這故事雖來自《哈利波特》,卻完全不是童話;我佩服羅琳,只她終究是個寫童話的。
所以我說這故事年齡太小的讀者可能看不了:她們可能會更願意相信芷蕭和蕭殘能堅定不渝地走到最後或者慕容安國本來有一個溫馨和美的家庭,她們不會懂芷蕭做出最後決定的社會含義,也不會明白姬天欽楚寒秋攪基背後的深層次悲哀。如果你相信王子與公主、相信正義的力量,那麽天牢裏的主要人物個個都是渣。但其實,人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我們只是看不到深藏的一面罷了。
不僅看不到別人,更看不到自己:曼吟看透了深藏不露的蕭殘卻不曾發現自己一直樂于導演所有人的悲劇,楚寒秋看透了那麽複雜的曼吟到最後卻連自己喜歡誰都不知道。我們像花盆邊上的螞蟻,一圈一圈地轉,看到別人的後腿卻看不到自己的,不論多辛苦到頭來都走不出去。生活就是那個花盆,是一張網,是傳說中由無常守衛的天牢:天牢對應天上的星,星星亮了,我們就逃不掉。一代一代、一圈一圈,無悔的出生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像是在宣揚宿命論,但試想,行動可以改變未來,性格決定行動,而性格是天生的;環境就更不用說了,那也是個客觀的東西。我們無從選擇,即便反抗,到頭來還是成也于斯敗也于斯——姬天欽這樣、蕭殘這樣,而何琴,其實也是這樣。
人總是要死的。我們活在天牢裏,誰也擺脫不掉被無常吻一下的命運,即使仇戮這般窮極心思求長生不死最終不過灰飛煙滅。讀《哈利波特》不會有人悲憫(注意不是喜歡)伏地魔,但我悲憫仇戮——如果你也悲憫仇戮,套用《金瓶梅》的話,你有一顆菩薩的心。好吧。但是即便如此,即便明知如此,我們依然在與命運不屈頑抗。我們采用不同的方式,有的正派有的走了歪路,前者變成英雄後者變成反派,而走中間路子的人,像蕭殘,他依然是英雄——卑微地活着,為了一個最終目的忍受一切冷眼與誤會,這種人雖不似義勇獻身的真誠可愛,卻委實可敬,而人類的偉大之處,也正在于此。
人類便是這樣一種既卑微又偉大的生物,在卑微裏追尋偉大,這是人類的悲劇,也正是人類的價值。給《天牢》寫了一個大煞風景的結尾:何老爺和金桂的最後一場完全破壞掉了先前淡淡惆悵的氛圍。我執意保留,因為除了我們的價值,我還需要讀者看到我們的荒謬——把先前那個卑微與偉大的理論倒過來,我們自以為很偉大,其實我們又很卑微:直到某個際遇突然發生我們才發現一直在反對的事情其實大有好處,只是悔之晚矣;反過來,是不是我們一直在不懈追求的東西到手之後,我們才發現其實也沒什麽,一切,不過如此。
2012年7月30日寫于家中
☆、後記二 從花漸落到路曼吟
《天牢》上下兩卷共有三個重要的女性,郁芷蕭,何林鐘,路曼吟。
面對命運無情套上的枷鎖,普通青年抗争一氣最終向它妥協,文藝青年負隅頑抗垂死掙紮,而鉛筆青年拒絕這個枷鎖,并親手設計另外一個将自己套在裏面。
——芷蕭是第一種人,何琴是第二種人,曼吟是第三種人。
先說芷蕭,這個名字聽起來已經覺得有些遙遠了。芷蕭是個符合社會标準的好女孩,聰明漂亮正直賢惠,而且富于正義感,又能堅持自己的想法。只是最後她妥協了,而且漸漸适應這種妥協,我想這是一般女孩子的命運。所以我說我悲憫芷蕭,并不是悲憫她的死亡,而是她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在社會和現實的強壓下,最終不得不選擇放棄。
而何琴選擇抗争,走進祭司經院,将一生獻給學問:她用這樣的方式抵抗社會壓力,并在神聖宗教的保護下為心中的美好堅守一生。只是我不知道,我現在完全不能判定,何琴在很多年後會不會後悔。這是我的疑惑,我無法解決——也許很多年後她會發現自己是多麽年少無知,曾經堅持的信仰有多麽可笑:其實安國很好,羅睿他們甚至別的人都很好,為什麽自己會執意将大好青春交付給一個從不曾在心裏在乎過自己老男人呢?也或者,她不會後悔,就像她的蕭先生一樣不會後悔。我以為之于何琴,蕭先生更像是一種信念,她追随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理想。她為這種理想枯守一生,而問題依然在于,她會後悔嗎?
我不知道。
如果說蕭颙光是一種理想,芷蕭最終不得不放棄他、何琴選擇追随只是不知未來怎樣,曼吟就是在理想中生活的典範。她在理想中生也在理想中死,但這一切,包括理想本身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正如蕭颙光早期經常在無意間走上曼吟安排好的路。
芷蕭是社會想要我成為的我、何琴是現在的我,曼吟是理想中的我。
何琴的生活狀态本是我不喜歡的,就像我不喜歡芷蕭的生活狀态。安排何琴愛上蕭殘本出于造化弄人的考慮,因為天牢所要表達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一切命運的殊途同歸。然而寫到後面,我只感覺何琴越來越像自己,越來越像一個為自己所厭棄的自己。從小把成績一類的東西看作身外之物,好心态向來是我引以為豪的本錢——這是我不喜歡何琴的一點重要因素:她太重視自己取得的成績以至于不分晝夜埋首書山,生活幾乎像蕭殘一樣無趣,不僅不若曼吟彈琴做戲描畫賦詩自在逍遙,甚至連像芷蕭那樣談個戀愛她都做不到。然而我們在某些經歷上又存在着類似:這是一個叫潘瑤的姑娘,一個由于何琴偏向虎山行的選擇而變得至關重要的“敵人”。那姑娘在玄武道本就相當有資歷,她瞧不起何琴因為她是國人出身。然而何琴依舊選擇走進蕭門,可以說是因為對蕭先生的愛,但更多的,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言,蕭先生對她更像是一個理想:她只是想要他一個贊許,她只是想離自己的理想更近一些。為此她不怕坐冷板凳不怕吃一切苦不怕別人的冷眼不怕周圍一切不信任不認可,頂着同門全是玄武道的壓力跟定蕭殘永不回頭。即使蕭門的血統觀念很重,她堅信只要自己足夠優秀蕭先生就一定能看得起她,只要自己足夠努力理想就一定可以實現——況且蕭先生本身也是個混血。然而蕭先生不過一介書生,即使看清潘瑤的本質也無力一票否決,況且之于何琴,她完全不清楚蕭先生的态度。從這個角度說,何琴的結局完滿了,因為蕭先生最終授她以他的衣缽。我以為這是個溫馨的結局,包括她走進祭司經院皓首窮經了此一生,不管她會不會後悔,她如今的理想實現了,并且沒說未來怎樣,這是我大多數主角完全享受不到的待遇。大抵人最終不敢面對自己,就算是我這種越在意某角色就越要弄死她的瘋子,看到一個自己并不見得喜歡,卻與自己親身經歷如出一轍的人物,也還是會忍不住,送給她一個,還不錯的結局。
我沒寫潘瑤推給何琴一切雜務、沒寫何琴在某些方面忍氣吞聲,沒寫兩人看似君子之交實際針鋒相對——因為劇情沒理由繼續複雜下去了,我也不打算這麽寫,更不想讓這出意在說命運的故事變得仿佛特有所指。所以從一開始潘瑤就被設定成一個對何琴懷有敵意且沒什麽底蘊的家夥:讓她完全不是何琴的對手也許會好些罷,因若潘瑤也太優秀了,《天牢》的下卷就終将變成兩個女子為理想和前途你死我活的血戰,而我沒有資格談論這件事。
與之相對的是曼吟,她是我在《天牢》中最喜歡的角色。曼吟死了,就像花漸落最終走向死亡,一個哭着一個笑着,結局不過殊途同歸。何琴的性格不像我,像我的是漸落、是曼吟——毀滅性格像自己的角色而存留經歷像自己的并給她不錯的結局,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心态?
從花漸落到路曼吟,這種發展似乎更能說明我人生觀的一種變化。此處不談鐘離如意:她雖也是個真性情的女孩,但她太幼稚——《與子同袍》是初中時代的構思了,盡管編劇技巧比《花漸落》成熟,在角色設定方面我還是盡可能保留着童年僅存的一點感念。從而,若說方才對芷蕭、林鐘,曼吟的比較算作是一種橫向比較,以下分析便是縱向對比。
這三個角色是花漸落,藍田玉,和曼吟。
有讀者對我說,她到現在最喜歡的文仍然是《花漸落》,并且全不像我自己感覺的那樣以為此文文筆幼稚,情節拙劣。漸落是個以舞臺為生命的人,她為夢而生為夢而死,平生所待只一知音:知音絕則弦絕,華麗地綻放而凄豔地終了,知其不可而為之,并且為此一拼到底永不回頭。那是年少時的我,第一回遭受某種意義上的挫折的我:盡管那劇本現在看來真是爛得出奇,那種初出茅廬的少年躊躇滿志、只想要得到一個華麗收場的情形還歷歷在目。手中的劇本不曾得到賞識、曾經很了解自己的朋友形同陌路,那樣的凄惶、那樣的無助,就感覺全天下沒有一個人能真正理解我,而我寧可死,也絕不甘入流俗。在這樣的心境裏寫出《花漸落》,一個清高而傲岸的女子,才華橫溢但不近人情,喜歡上一個人卻驕傲着不肯說,熱愛自由以至于寧死不屈,到最後不知道喜歡的究竟是戲還是戲中人,直到曲終人散,凄美地死去——我想那姑娘對此共鳴也是年齡使然: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思想即使再成熟,對她談命運也太過遙遠,但夢想與抉擇離她很近,這讓她更容易思索也更容易感同身受——當然,在我看來,她的知識與見地已經超出現在的很多大學生了。
藍田玉也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而且出現在故事中時她只不過比同齡人多些常識,多些倔強。相比花漸落她要平凡很多,同此一心的卻是她極度缺乏的也無非是理解。對藍田玉的性格剖析在《忘情的那個角落》後記中已敘述得極為詳盡,但這裏需要說的是她的幾次選擇:第一次是分文理,第二次是讀大學——第一次她可以留在理科班以保證留在芳身邊的,但她沒有這麽做,寧可明知忍受痛楚;第二次她可以選擇留在家鄉的,但她依舊沒有。夢想與愛情不可兼得,藍田玉兩者都想要卻最終不能放棄夢想——這才是藍田玉的本質,寧可情感上受着煎熬也不能放棄自己想要做的;而至于情感,序文中提到兩人的感情已淡如秋水,一起逛街,聊些瑣碎的家常而不再談論詩歌談論文壇巨擘談論美。相比花漸落,藍田玉懂得了妥協,懂得了怎樣在維持自己的同時關愛別人。所以我說藍田玉的故事雖排在花漸落之前,但由于動筆較晚,她實際上比花漸落成熟。
然而之所以把花漸落排在後面,我的考慮是人在成長之後開始遭受挫折。藍田玉選擇了理想,于是她走向一座新的城市開始以為理想中的生活。然而現實并不像她想的那樣,自己的才華并不曾被認可,像芳那樣的知音再也找不到,好容易有個了解自己的男孩子卻再不能像谷梁佚文甚至賀泉那樣做最鐵的朋友——她不屈、她頑抗,這就是花漸落,抗争到死。這是典型的文藝青年的做法,何琴也是這般——所以說來道去我還是逃不脫這個框框(天牢?),盡管由于近來僞文藝者見得太多,我總有感覺說我文藝某種程度上是在罵我。
所以回到曼吟,常開玩笑地說鉛筆是一種境界。曼吟是個完全生活在理想中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喜歡的事。她是個天才,也是個有想法有魄力的女孩子——如果人能随意做一切想做的事,各種應付也能信手拈來,她實在是太幸福了。然而所謂高處不勝寒,過于優秀導致多數人不敢接近她,于是她會和蕭殘成為朋友。其實曼吟所需要的也無非是理解,楚寒秋将她剖析透徹,她便願意和他做夫妻——實際上,這場婚姻,明眼人都能看出,完全是曼吟同學鬧着玩的。她喜歡楚寒秋,但明顯不是姬天欽那種喜歡:她對楚寒秋對蕭殘都一樣,一個朋友,他能幸福我就高興。大家不要因為曼吟臨死前說那番話就認定曼吟真正愛的是蕭殘——她誰也不愛,正如姬天欽所說她有她自己就夠了——盡管曼吟不是正常人,她這樣的奇葩眼光更獨特:好容易找到個看上眼的,誰會輕易就拱手讓人了。所以正如楚寒秋所言,她成全蕭殘和芷蕭自己偷着哭只是因為她想把情節安排成這樣,哭過之後戲就算演完,她該怎樣還會怎樣。花漸落分不清戲和生活,曼吟卻清楚地知道生活不過逢場作戲:她是個跳脫于生活之外的人,生活的苦對她都不算什麽,她只要把戲演好就夠。此種人生态度對她而言是天然的,直到被楚寒秋剖析過她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是這樣在生活。對此她慨然接受批評,但事過之後依舊我行我素,即使在蛇君廟前也不例外。這場死亡同樣是她導演的戲,演出成功,她邊哭邊笑邊将自己毀滅。她曾說如果她做蛇君死士們會過得更好,這話不是亂來的:她和蛇君,某種程度甚至包括東君,他們都喜歡做這個世界的掌控者。只不過蛇君所為涉及別人,曼吟只是自娛自樂,另外,曼吟還是希望大家都能過好,所以她的行為多數是無害的。
不論芷蕭還是花漸落何琴還是藍田玉,不論妥協還是抗争還是一半妥協一半反抗,她們都被周圍的外物所左右。只有曼吟在左右外物,也左右她的肉身,左右周圍的一切。她的行為通常表現得反常甚至二貨(進一步的神人是她二十多年後的師妹桂望舒),死到臨頭了還有心誇別人綠帽好看——這就是鉛筆青年的境界,通常人,做不到。
曼吟基本超然了,但她依然活在自己走不脫的圈裏。她擺脫了外界畫的圈卻又給自己畫了一個,之後像其他人一樣傻乎乎地生活在裏面,讓自己笑就笑、讓自己哭就哭——讓自己死就死。重新畫個圈把自己套進去,即使是曼吟這樣的天才也逃不出,這就是鉛筆青年的悲劇。
所以寫《天牢》我就是想寫全人類的悲劇。這其實是個大問題,以本人無名小卒做此大工程似乎有些蚍蜉撼樹的味道。但說上面一大篇着實講我只是想做一個自我總結:四年下來,寫過四個冗長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在剖析我眼中的人生——人在成長、在被社會打磨,變得理性的同時發現與生俱來的靈感已被消耗殆盡。從英雄悲劇走向庸庸碌碌的普通人,從懷抱夢想的演員到游戲人生的琴師,從為理想獻身到在無盡的現實裏消磨,也許是我堕落了,也許是我成熟了。把這一系列毫不相幹的小說歸為一個系列,取名叫“歲月的足跡”,我想說這就是我自己的一部成長史,确切地講,是對世界,對生活看法變化的過程。
2012年9月8日0時整
完稿于南京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