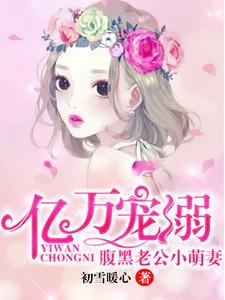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9章 【9】好天氣
【9】好天氣
通往舅舅家的那段泥巴路,直到關歆初三那年,才給鋪上水泥石板。
那條道路狹窄,是條單車道,只能供一輛車在路上單向行駛,每每錯車,都需小心翼翼,十分麻煩。
剩最後百十來米遠處,迎面來了輛三輪車,關歆只好提前停車,将車向右邊移了移,半邊車身壓到一旁的泥土地上去。
開三輪的是個小婦人,三十多歲的年紀,穿着件湖藍色針織短袖。衣裳被洗得有些縮水了,後腰下擺處的一截皮肉沒遮住,領口也失了原本的彈性,耷拉亂翻着。
她身後貨物堆得滿滿當當,打着結的塑料袋,被風吹得呼呼作響。
“金春婆!”
正要錯車而過時,她突然熄了油門,和後座的外婆打起了招呼。
關歆瞅她眼生,但聽到外婆叫她 hui 子,對她一下子就熟悉了起來。雖然這個“hui”是哪個字,關歆都對不上號,但她對她印象深刻。
hui 子和丈夫原先一直在武漢一家木材加工廠工作。2019 年的上半年,丈夫做工時,右手給絞了進去,落下殘疾,兩人便回了南縣。
“你家男人現在好吧?”閑聊兩句後,外婆關心道。
“好!好着呢!”
hui 子臉上沒有關歆刻板印象裏該有的凄苦,她臉上漾着的笑,顏色勝過她身上那件湖藍色上衣。
前後又來了車,hui 子從身後随手抓了包東西往關歆他們車裏塞,說:“他現在左手用得比之前右手還順,這豆絲都是他做的,根本用不上我幫忙。你們嘗嘗他手藝!”
說完就轟着油門走了,她緊着時間送貨。
關歆也繼續向前開,她們到舅舅家時,他們剛結束午休,都坐在院子裏曬太陽。
剛下車,舅媽就不停抱怨說關歆她們不提前通知,沒做準備。
舅舅從裏屋拖來幾把椅子,讓她們坐,忙完就去雞場逮雞。
關枝華坐在舅媽身旁,聊剛碰見 hui 子的事。
舅媽端了盤瓜子遞給她們,自己也抓上一把,邊嗑邊說:“武漢疫情後,hui 子就緩過來了。禍兮福所倚,人活着就行。”
關枝華點點頭,也應是。
一旁的外公外婆沒參與,外婆拿了把剪子,正在幫外公修剪頭發。
外婆北人南相,臉上幹淨白皙,沒有壽斑。握着剪子的那雙手,卻長得粗壯,指關節是不相符的粗大,手掌更是粗糙,爬滿硬繭。
這時日照厲害,關枝華她們閑聊聲音窸窣,外婆剪子又落的極慢,兩相交映,形成很好的白噪音。關歆放平身下躺椅,迷迷糊糊,打起了瞌睡。
這個瞌睡一打就是一個多鐘頭,關歆醒來時,日頭已經落了一半。
關枝華和舅媽這時已在忙活晚飯,外公的頭發也修剪完畢,換他握着那把剪子幫外婆修剪手指甲。
修剪完最後的小拇指,外公撲撲外婆膝頭落上的碎指甲殼,輕聲邀請她:“去河邊走走?”
外婆點點頭,收好剪子同他一起走。
關歆也湊熱鬧,跟在一旁。
“金春回來啦!”
三人剛走到村口,外婆就被李家婆婆叫住了,直呼讓她幫忙看看家裏新制的醬,讓她把把關。
外婆只好跟了去,她讓關歆和外公先走,等會再趕去尋他倆。
關歆和外公繼續朝堤壩那邊走着,步子放的更慢了些。但沒走多會兒,外公還是停了下來,他轉過身朝來的方向說:“等會兒她吧。”
斜陽正打在他身上,拉得他身影很長。
關歆望着外公的側臉,黃昏裏他的一雙眼更顯濁黃。
她終還是沒忍住,她還是問出了口:“外公,您怨嗎?”
外公眼眸低垂,眼皮滾動,久久未作答。
又等了等,終于等到他張口,叫的卻是:“驚春!驚春!驚春!”
外公右耳聽不見,聲量不能控制,總是忽高忽低。
他招着手,呼喚的是外婆的名字。
外婆名字是“驚春”,她父親取的。
因為生在立春時令,父姓為“莫”,便取名為“莫驚春”。
郢城南縣人前後鼻韻母不分,所以莫驚春做了大半輩子的“莫金春”。
關枝華也生在春天,外公取的則是弘一法師“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裏的“華枝”二字。只是調了個順序,為和舅舅的“之遙”相和諧,喚起來更相配。
外公和外婆本是大學同學。只不過外婆念到大三時,因家裏父親的關系,她被校方強制退了學。
外公再尋到她時,她正坐在破角胡同裏,糊着紙燈籠。
她兩手紅腫,不知是被那燈籠紅紙染的色,還是給這三九天凍的。
反正只見她雙手瑟縮地往身後藏,不願讓昔日同窗見這窘狀。
外公并未多言,慌亂地找出兩冊書,塞到她懷裏,說:“你前些日子說想看的…你拿去看…”
未等外婆作出反應,外公就已轉身跑了。
自那次後,外公間隔幾日就會跑那兒一趟,挂着收書的名號,卻總是又硬借出一兩冊。
來去匆匆,不作停留。
只是一日,兩人換書時,指尖相擦,多停了幾秒。
兩人皆紅了臉,外公轉身欲走時,外婆叫住了他。
第一次喊住了他,磕巴兩句後,還是只問了問閱書時的困惑。
外公自那日起,便會多留一會兒,坐在門檻處,給外婆答疑解惑。
又一日,兩人聊得忘切,天光漸暗,才察覺到時間已晚。
外公合上書冊,遞還給她。
兩相交錯,又碰到了一起。
只是這次,外公沒再一觸即走,他反手緊緊握住了她。
兩顆年輕的心髒洶湧亂跳,聲響吵擾到了屋檐上的麻雀,它們四散飛去,就留他倆盈盈相望。
或許就是那晚,倆人定下了約定,留洋回國之時,關黎晖迎娶莫驚春。
兩人婚後随外公的工作調遷,南下到了武漢,也是那個年末,有了關歆舅舅關之遙。
只是沒想到,大學老師的兒子,直到十歲,才得以入學。
好在關之遙聰穎,當時五年制的小學,他兩年學完,趕着同齡人的腳步,一起升上初中。
他書讀得很好,但他并不喜歡讀書。
因為他見過學問做得極好的人,境遇遠不如田地裏最窮苦的莊稼漢。
連帶自己,也遠比不上最窮苦的莊稼漢的兒子。
都說小兒三歲前是沒記憶的,但關之遙兩歲時候的記憶卻歷久彌新。以至于到了他三十多歲,又見到那個和記憶裏相似的銅頭皮帶時,還是不禁打起了寒顫,盡管那個皮帶主人是個比他瘦弱許多的花甲老漢。
兩歲的關之遙無法理解,那些常來家裏聽唱片、和父親讨論叔本華的學生,為什麽會手拿棍棒打父親?那條銅頭皮帶好厲害,父親的腦袋瞬間就給砸開了瓜,父親的右耳也能給打聾。
他書念得極好,但他厭惡上學。
他厭惡自己的飯盒總被摻進沙土,卻不能反抗。盡管八十年代初風氣已比過去好多了,但對于他們這樣的人,大家還是有看法,如果運動又來,第一個就會把他們家打倒。
他忍啊忍、忍啊忍,心裏的憤恨滾成了大火球,終于爆發在一個下午。
他鼻青臉腫,嘴角挂着血,回家說:“我要出去做事。”
那個時候,關枝華還在念小學,但她十分理解他,因為她身受同感。
當關之遙沖這個世界亮起拳頭,這個世界突然就變得春風化雨了。
關枝華再得知關之遙的消息時,同村人都是豔羨。
關之遙具體在做什麽,關枝華不清楚。她只記得他帶她在校外吃的那碗加滿菜碼的熱湯面,和買給她的那雙白色雨靴。
她是全校第二個穿上白雨靴的人,第一個是面粉廠財務科科長的女兒。
關枝華讀到高中辍的學,女孩心思更敏感些,等到她可以專心念書時,數理化早讓她一頭蒙了。
她支了個租書攤,但門可羅雀,生意遠不如拐角處的那家。
她進書時讨教,批發她書的老板笑而不語,拉她進了裏屋,遞了本書給她。
是本錢鐘書的《圍城》,她書攤擺的就有。沒等她言語,老板點了點封面,讓她翻開仔細看。
她才翻一頁就扔還了回去,那些赤裸的文字羞紅了她的臉,包在書皮下的竟是這些東西。
她做不來這種生意,書攤很快轉了出去。那時候關之遙常跑廣州,不知道幹什麽,總是提個箱子來來回回,帶不少新奇的玩意回來。她在裏面翻到齊秦的卡帶,一個人聽到半夜。
她沒過多久就做起了盜版卡帶生意,唱片攤就擺在師專校門口,來往的都是時髦的年輕人。
也就是在這兒,一個戴着塊梅花表的學生,走到了她攤前。
這個學生後來幫她背過貨,陪她在橋洞裏躲過雨,也幫她打點過關系,讓哥哥沒被頂罪戴上黑社會頭目的帽子。
這個學生對她說過“我愛你”“嫁給我”,最後也是他說的“對不起”。
上大學,關歆一次登知網,突發奇想地在作者欄敲下外公的名字,檢索出四條結果。
那是關歆第一次對外公外婆的一生,進行長時間的思考。她在想如果沒有那些事,他們的生活會是怎樣?
舅舅應該就不會在那高牆裏蹲上兩年,母親也不會因此對那個人漸生情愫。
他們原本的道路是那麽的坦闊,卻離奇地囿于這羊腸小路裏。
這些年,關歆踏着祖輩們的足跡,一路小心翼翼,遵循世俗對成功的定義,刻苦學習,努力工作,就怕行差踏錯半步。
可如今,自己卻成了華服上的虱子,被他們一抖,就給抛了去。
她望着外公,打着腹稿,斟酌用詞,最後還是只問出了“您怨嗎”三個字,連個“恨”字都不敢提。
外公沒有回答她,他喚着外婆的名字,讓“莫金春”又做回莫驚春。
他們執着彼此的手,伴步走在河堤邊,讓晚霞落下來,慢慢融進了光中。
*
關歆沒能在南縣多待,關枝華忘記關閉社區團購的接單,她次日早上就得趕回去。
清晨六七點,透着一層薄霧,還未大亮。
關歆壓着四十碼不到的速度,跟在一輛液化車後面,慢悠悠過橋。
一下橋,就到了江家那間鮮制熟食廠,關歆朝那兒瞟了一眼。
正是上貨的時間,幾個工人在給冷鏈車上貨,預備分送至各個分店。
關歆剛要收回目光,瞥眼就瞧見個熟悉的身影,她踩下剎車,把車停到路邊,繼續透過後視鏡觀察。
江铖不似其他工人穿着統一的工裝。他套着件坎肩背心,寬大版型,水洗做舊的炭灰色,是他高中時就常穿的款。
關歆觑着眼,想看清他手腕,看是否有那标配的兩根運動護腕。
窄窄的兩條,矽膠材質,他總戴黑白兩色。
關歆覺得那就是個裝飾,類似于女生的手鏈,并沒有運動保護作用。但她還是給他買過一根,被他訛的,所以故意挑了個騷包的熒光粉。他倒不介意,一直戴着打籃球,沒見取下來過。
江铖剛上完一箱貨,站在冷鏈車一旁,身子被車門擋了大半,只能隐約瞅見他垂着的手腕。
關歆揿下車窗,正欲探出頭,手機這時響了一聲。
打開一看,是條短信,發件人是外公,寫的是“人生忽如寄,莫辜負茶、湯和好天氣。”
關黎晖明白關歆的問話,并不是一時興起,她大概是遇上了些事兒。他起先嘗試寫些什麽送與她,但越寫越長,越寫越瑣碎,最後一股腦兒都揉成了團。他不想被過度解讀,最後便挑了這句話,以短信形式,輕拿輕放,算是回了她昨天的問話。
“…好天氣。”
關歆喃喃,嘴裏重複,籲出口氣後,伏到方向盤上,前額磕着舵盤,反複琢磨這句話。
一個用力,撞響了喇叭,發出刺耳的鳴笛聲。
長鳴聲引人注目,包括後視鏡裏的那個人,也被吸引注意,看了過來。
他腳下踯躅,不知是否就要踏步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