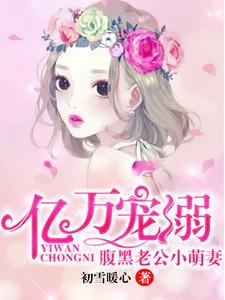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66章 :為公(上)
第六十五章:為公(上)
安珺從小就喜歡搞各種發明創造,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科研工作者,盡己所能的為祖國做出貢獻。
在從蒼梧中學畢業之後,他并未參與到真理主義運動的浩蕩浪潮之中,而是徑直來到了首都恒榮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博聞大學,在機械工程專業就讀。
他的同學,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甚至還有國外的理工科人才。
安珺一向對政治淡漠冷感,甚至可以說是毫不關心,在他的思想裏,似乎只有國籍的概念,而沒有關于階級和黨派的認知
他認為自己效忠的是作為祖國的陵山國,他的所做所為,都只是為了助力自己的祖國走向繁榮富強。
他不願摻和進“真理派”和“權威派”的争鬥之中,甚至将兩派相争視作一種不可理喻的行為。
“都是一個國家的人,他們在争個什麽勁呢”
在安珺看來,無論最終取得勝利的是“真理派”還是“權威派”,都和他本人沒有任何關系,他只要好好上自己的學,畢業之後好好搞科研,盡可能多的給國家做貢獻罷了.
“我不管臺上站着的是李昭旭還是蔣經緯,我只想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我是一個陵山國人,僅此而已。”
後來,在陵山國中央政府內部出現了“守正派”和“改良派”的分歧之後,安珺也依然表現地漠不關心,他不願意“站隊”,他想一輩子保持中立。
只是一心渴望着“保持中立”的安珺終究還是在不久後的将來被裹挾進了這場黑暗的內部鬥争之中,徹底淪為了連啓平等人栽贓陷害對方的工具,作為一個導火索般的犧牲品被迫害至死。
江衡救不了他,張尚文也留不住他,連李昭旭都沒能做的了什麽。
他不願意“站隊”,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也會強迫性地将他塞到某一隊某一派之中,充當自我粉飾的有力武器。
這是獨屬于某一段時代的悲劇,投射着那一個悲劇的時代。
在陵山國建國後的第一個三年中,一切都像“藍圖”所規劃的那樣,穩中求進,健康積極地向前發展着
陵山國的大多數日用品,桌椅板凳鍋碗飄盆衣服鞋子之類,都不需要再從外國進口了。
陵山國生産出的輕工業産品也不再是粗制濫造進和效率低下的代名詞,這在從前那個幾乎一切都要依靠手工生産的年代簡直是不敢設想的。
更加令人振奮的是,陵山國的鋼鐵産量較三年前有了飛躍性的增長,雖然質量依舊比不上以工業發達著稱的永緒國,卻已經是一個極其難能可貴的進步了
“我們陵山國地大物博,礦産資源豐富,卻沒有先進的工業技術,只能以低廉的價格出口原材料,再用高昂的價格把成品買回來,這樣下去,就是金山銀山也不夠我們揮霍浪費的,
況且,他們現在願意賺我們的錢,把我們自己造不出來的東西高價賣給我們,以後呢萬一我們和他們的合作關系破裂了呢萬一兩個國家之間打起仗來了呢
我們是愛好和平的,其他國家怎麽樣我們也不能斷定,國際關系總是複雜多變的,誰也不能永遠靠的住。
所以說,把技術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裏,實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我們現在的首要任務。”
李昭旭在三年前發表的這段重要講話,已經如同陽光雨露一般滋潤着陵山人民的心靈,各行各業的人,尤其是科研工作組的成員們,都充滿了頑強拼撞,自強不息的幹勁。
到了1876年,國家直屬的科研中心已經将規模擴大了三倍有餘,各領域“人才”增加了二百多名。
他們不再像先前那樣,一大堆人解決一大堆問題,分工不明确,也無法保證創新效率最大化。
現在,這二百多人按照各自的專業才能被分為了四個科研小組,分別是“入微””求是”“務實“和“衛國”
“入微”,顧名思義,就是研究一些構造精密的物件,需要科研工作者們精益求精,不容忽視半分,
“求是”則主攻生物方面,負責研制治療各種頑固疾病,尤其是嚴重傳染病的藥物,
“務實”主要針對于人民群衆的日常生活,研究一些具有科技色彩的,便民利民的設施以及百姓平日需要的各種東西,
“衛國”負責研究各式各樣的先進武器,增強國家的軍事實力,以備不時之需。
“我們不會主動拿起武器,但是,一旦有誰妄想着侵擾我們,我們将會義不容辭的予以反擊。”
在1877年,以安珺擔任組長的“入微”科研組研制出了陵山國第一塊自主生産的機械手表一—他為自己的科研成果命名為“安康”
“這手表看上去是個小物件,裏面卻也蘊藏着大學問。”在“入微”科研組的“慶功大會”上,李昭旭親臨現場,給予勤懇工作着的科研工作者們表彰與勉勵。
”幾千個細小的零件,每一分每一毫都必須嚴絲合縫,聯接緊密,它才能正常的運行,你們也是一樣,只有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大家互相配合,彼此幫助,共同努力,國家的科研事業才能有大進步。”
在成功突破技術難關之後,陵山國各大工廠開始批量生産安康牌手表,徹底打破了永緒國“銳澤”和“福道”兩大手表品牌壟斷市場的屈辱歷史,開創了一個以獨立自主為主旋律的新時代。
“從前,永緒國人每賣給我們一只手表,他們就要從中撈取三百元到五百元的利潤,他們使勁地擡高價格,就是欺負我們自己造不出來,我們能讓他們欺負一輩子嗎堅決不可能。”
安珺的态度仍然是那樣的堅毅而決絕,就像他當年在蒼梧中學的時候,極力渴望着發明出陵山國人自己的音樂盒那樣。
他總是迎風而生,逆流而上,不畏艱險,越挫越勇
他是一個有骨氣,有原則的人,正是這些本來崇高而美好的品質最終将他葬送在過分漫長的茫茫黑夜之中。
這三年的文化建設也是相當的成功,身為國家的宣傳部長,江衡很稱職地履行着自己作為“門面”的職責。
一方面,她多次在外進行公開演講,演講內容有時是江衡個人的見解,有時則是轉述李昭旭在某次會議上的核心精神。
由于每日的工作實在是過于繁重,李昭旭很少出現在公衆視野裏。
不過,在民衆心裏,江衡站在臺上演講和李昭旭站在那裏的效果差不多,她完全可以充當對方的“代言人”
江衡是一個極其獨立而要強的人,她和李昭旭之間的愛情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他們在婚姻關系中完全處于彼此尊重,互相愛護的平等狀态,從沒有誰必須聽從誰,誰一定遷就誰的規矩.
因此,在幾百萬的陵山百姓中,從沒有人把江衡認作李昭旭的附屬物,更多是把她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去看待。
她的名望和地位主要來自于自己宣傳部長的職務,而不是領袖夫人的身份。
在成功從昏聩中覺醒的民衆裏,江衡簡直就是新時代獨立女性的典範,
她才華橫溢、能力超群,還擁有着堅強不屈的意志和崇高偉大的理想信念,簡直可以被稱之為一個“完人”
那些極其富有感染力與煽動性的演講語言讓江衡俨然成為了一臺時刻播放主旋律的留聲機,人民敬重她、景仰她,崇拜她,願意在她指引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前進。
另一方面,江衡又極其重視真理主義思想在教育領域的融合與滲透。
她參與編籌了陵山民主共和國建國以來的第一批政史教材,從小學到高中,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徹底打破了蔣經緯執政時期政史讀本歪曲歷史,颠
倒是非的畸形風氣。
“要讓孩子們從小學習正确的思想,培養正确的價值觀。”
政史教材上,李昭旭等真理主義者們英勇鬥争的事跡與舍生忘死的精神被展現地淋漓盡致,“權威派”反動分子們卑惡醜惡的嘴臉也被批判性地展示出來。
“把這些負面的東西給孩子們看,恐怕不太好吧”許英才曾提出過這樣的異議,他終究是一個保守的人,總習慣于拿着所謂的“客觀規律”說事,不太願意接受那些固有認知之外的事物.
“其實,這些看似負面的東西反倒是不可或缺的,沒有對比,空談偉大只會顯得空虛而蒼白,我們不僅僅要了解自身的進步科學,也要知曉對方的反動落後,只有知道了他們有多麽的不好,才更能體現出我們有多麽好,所謂的制度自信,就是這麽來的。”
江衡在陵山國中的名望很高,她卻從來不會感到驕傲自滿,固步自封,也不會得隴望蜀、渴求更多,她既不是劉空山那樣喜歡出風頭,刷存在感的浮躁分子,也不是連啓平那樣不知飽足的野心家.
她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是落迫還是得志,都能夠永遠堅守着自己的初心,她一心只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為國為民奉獻終生
“我從不會妄想着淩駕于人民之上,為自己謀求特權,這是一種相當卑劣無恥的行為,我本來就是從一個普通人一步步成長起來的,我從人民群衆中走出來,必然要回到人民群衆當中去。
為了我的祖國,為了陵山國的人民,我甘願付出一切。“
和江衡相比,張尚文的境遇則顯得稍稍冷清了些,身為國家的□□長,他并沒有太多抛頭露面的機會,更多只是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和面前的鋼筆和稿紙“作鬥争”。
張尚文是陵山國文化領域的“标杆”,不但要“搞文化”,也要好,地“管文化”,為全國的文化創作者們做好模範榜樣。
他自己會創作一些散文、詩歌、短篇小說——大多都是與主旋律環環相扣的,刊登在陵山國的官方雜志《真理之聲》上面,其主旨與中心思想也主要是從不同視角歌頌李昭旭等真理主義者,弘揚作為社會主流思想的真理主義。
同樣的,張尚文也在自己擔任主編的《文藝創作》中發表了一些對于文化、藝術等領域從業人員的要求,以培養他們健康的職業道德準則。
“文藝創作,應當貼合時代背景,立足人民群衆,滿足百姓對于精神食糧的需求與向往,不能搞那些假大空的東西。
“文藝作品中,當然可以出現壞人壞事,小偷流氓、反動分子都可以作為創作對象甚至是主角,前提是作者描寫這些負面事件的目的是批判某種不良風氣,揭露某種黑暗現象,以貶低假惡醜來側面弘揚真善美,這樣的作品也是正能量的。”
“文藝創作可以通俗,貼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絕不能低俗、庸俗,為了博眼球而搞那些上不了臺面的東西,搞色情、暴力、淫/穢,這些都是不符合時代主流的。”
“針對‘愛情”這個問題,文藝界總存在一些兩極分化的觀點,有些人以為愛情是極其崇高的,為了表達愛情可以采用各種各樣誇張過分的手法,甚至使用一些色情的手段都是無傷大雅的,它們都是在為崇高的愛情做陪襯,能上得了高臺面;
另一些人則相當排斥愛情,認為文藝作品中一旦出現愛情元素就是靡靡之音,就要走色情路線,變得低俗化。
這兩種觀點,都犯了片面化的錯誤。
愛情自然可以成為文藝作品中的主要元素,它并不等同于色情,等同于那些低俗庸俗的東西,愛情确實是一種崇高的情感。
只是,在文藝作品中,對于愛情的描繪和敘述應當适度得當,不能無限制地肆意表達,并且愛情存在于作品中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弘揚真善美,傳播正确的愛情觀。
那些濫用愛情,放蕩欲望的作品自然得不到公衆的認可,稱不上是優秀的文藝作品。”
“門面”和“标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陵山國上下一片政通人和,文化發展欣欣向榮,大量正能量的文藝作品湧入陵山人民的視野,給予人們豐富的精神財富。
在那些最受人民群衆歡迎的文藝工作者中,有一名叫作夏銘鐘的小說家,他使用筆名“橙園”發表作品,寫作風格以想象豐富和寓大于小著稱。
在他的作品中,古代人和現代人可以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不同時代的先賢哲人們可以聚在一塊讨論社會民生。
橙園曾在《文藝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盛世相逢》的短篇小說。
故事中,平貞時代的開國君主于汶楷來到了現代,和李昭旭進行了親切的會晤,兩人批判着舊時代的黑暗,頗有相見恨晚之感
最後,這兩名敢于打破舊規則的偉人,共同喊出了那句著名的:“王侯将相寧有種乎!”
這篇文章受到了人民群衆的廣泛認可,就連李昭旭本人看了都對其贊嘆有加,
”如此巧妙的構思,如此獨特的想象,如此健康的價值觀,橙園先生真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
彼時的陵山國,尚且是一塊肥沃而充滿希望的土壤,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迎着溫暖的東風與燦爛的驕陽,在春天裏肆意生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