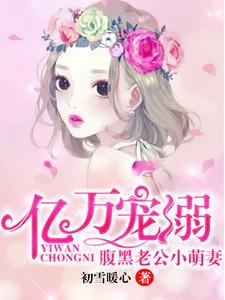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38章 ☆、秋千蕩漾,甜蜜漣漪
方萍自己一個人去看了蔡河江的比賽,回來後叽叽喳喳說個不停。
“哇,姐,你知道嗎?那比賽真的是全程心髒砰砰砰,好刺激啊。”
方染給方萍買了一杯可樂,兩個人在師範學院的塑膠跑道上,邊喝邊說。
“蔡河江那小子真的好帥,我沒想到射擊也能這麽酷。”
“蔡河江那小子運氣真的很好,我還以為至少得高考後,通過體育特長生的途經考進師大呢,結果初中沒讀完就被省體校選中,就來了省城。”
方萍還在吱吱喳喳說着,方染卻已經看不下去了。
“萍,如果難受,就說出來吧。不用憋在心裏。”方染說。
“我們已經完全走上了兩條不同的人生路。一個是流水線上的打工妹,一個是朝着摘金奪銀的夢想沖刺的潛在運動員。昨天,他送我回來的時候,下了公交車後,我跟他,往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各自頭也不回地走了,既然永不相交,那麽,也不必回首。”
方萍喝了一口奶茶,又說,姐,這奶茶味道不錯,以後如果我出師了,賺了很多很多錢,就在家鄉開一間奶茶店。
方染知道,方萍這一趟來省城,是為了埋葬那些青澀的夢想,還有愛情的。
這個妹妹,早在作了辍學的決定後,就學會了以嶄新的心态擁抱自己的人生,她說過,已經發生的事情,再糾結也沒用,只能努力沿着生活的逆流向上攀援,才能扼住命運的咽喉,當人生的主宰。
所以,方染還是不如方萍啊,只會一個人苦苦掙紮在過去的悔恨裏,無法自拔。
時間匆匆,轉眼,高一下就接近尾聲,文理分科之前,培明開了學生大會,專門請了一個在教師這個專業崗位耕耘了四十多年的退休老教授,給他們上一堂講座,題目叫,你為什麽讀書?
那老教授很風趣,一上來就問,同學們,你們為什麽讀書啊?
然後就有幾個人,怯生生地舉起手來,說為了高考。老教授搖了搖頭,你們這些人,太功利。
底下就嘩地一下哄笑開了。老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突然又問了,你們這些小娃子,有誰家父母是農民的?
Advertisement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紛紛搖頭。這時候,有個人,高高舉起了手,大家轉頭一看,竟然是,方染。
曾經,方染并不喜歡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農民,那是一種潛意識裏的抗拒,可是今天,在這個200多人的大會場裏,鬼使神差地,她舉起了手。
老教授又問方染:好孩子,你父母是農民,那有沒有告訴過你,為什麽,勒緊褲腰帶,也要讓你讀書啊?
方染又搖了搖頭,其實她心裏有個答案,為了光宗耀祖,但她不好意思講。
老教授又說,其實不讀書,大概也是可以生活一輩子的,祖祖輩輩的農民就是這樣生活的,知道了節氣的轉換,知道種什麽作物,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就算農耕時代已經過去,工業時代到來了,但流水線上的工人也只需要日複一日進行些重複性勞動,不讀書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為什麽要讀書呢?因為天地之大,海洋之闊,思想之巍巍傲視,生活之豐富多彩,沒有讀過書,是體會不到的……
在我看來,讀書的全部用處就在這裏了。
所以,将讀書跟個人前途、跟價值變現、跟社會發展、跟未來生活、跟群體命運捆綁在一起,将讀書直接等同于高考,就太功利了。
聽到這裏,可能有同學們就會問了,那讀書不是為了高考,我還沒日沒夜地拼命讀書幹什麽?
問這個問題之前,請同學們先問一問自己,“将來,我想做什麽?”還有,“目前,我能做什麽?”,然後你就會發現,我們拼了命去讀書,其實是為了以後的生活,能有更多選擇權,去做想做的事,而不是為生存所迫,去做能做的事。
所以,在文理分科之前,請大家将兩個問題好好想一想。
此後很多年,那個老教授的話,一直銘刻在方染腦子裏。起初,她琢磨得不是很明白,什麽叫想做的事,什麽又叫能做的事。
直到2008年,她看到龍應臺寫的一篇文章。
2008年,龍應臺在寫給她兒子安德烈的一封信裏,曾這樣寫道:
孩子,我要求你用功讀書,不是因為我要你跟別人比成績,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将來會擁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有意義、有時間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當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義,你就有成就感。當你的工作給你時間,不剝奪你的生活,你就有尊嚴。成就感和尊嚴,給你快樂。
如果我們不是在跟別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為自己找心靈安适之所在,那麽連“平庸”這個詞都不太有意義了。“平庸”是跟別人比,心靈的安适是跟自己比。千山萬水走到最後,我們最終的負責對象,還是“自己”二字。因此,你當然沒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為了符合上一代對你的想象而活。
方染真的很認真去想了老教授的兩個問題,然後又去問他了她老公程皓的意見,程皓讓她聽從心的決定,她毅然決然地選了文科。
誰叫她的記者夢在燃燒呢?
鄭興禹不出所料,進了高二三班尖子班,程冉那個吊車尾的成績,只能繼續在文科班裏混,還跟方染同桌,但像以前一樣,時刻跟鄭興禹膩在一起,就不可能了。
程皓,跟方染還時不時冷卻着,所以,方染有大把大把的時間,來為高考準備和沖刺。
進了文科班以後,方染一下子就變成培明文科班全年級第一,英語、語文、地理、數學都是方染的強項,政治、歷史靠死記硬背,方染并不喜歡這兩門課,但為了總成績,天天弄了個時間表,什麽時間段背誦,什麽時間段做題,什麽時候段聽力,都被她安排得好好的。
方染在第一名的位置保持了很久,雖然她的成績跟理科班的第一名,都要差個100多分,但她已經很滿足了。
轉眼就到了高三。
大部分人的高三,都是一樣的吧,就像後來發表在讀者雜志上的《憑什麽上北大》一文作者賀舒婷寫的一樣。
也是,從早晨六點早自學上課到晚上十點晚自習下課一動也不動坐在位置上。
也是,考完後,茫然地看着車水馬龍人來人往,恍惚想真的考完了嗎?為什麽心裏空空的沒有着落?
也是,差一點就背不下去了就要把書扔掉了,卻告訴自己,忍不住的時候,再忍一下。
也是,意志的力量,是決定成敗的力量,靠着這句話走過了高三最後的日子。
也是,在敬畏與期待中迎來又送走了一模、二模以至N模,每根神經都被冷酷無情的現實錘煉得堅不可摧。
也是,無數次的希望在無數次的失望前撞得粉身碎骨,無數次的激揚在無數次的頹喪下摔得頭破血流。
也是,難以承受那潮湧而至的恐慌和迷惘,于是逼着自己埋進去,埋進書本,埋進試卷,埋進密不透風的黑繭——為的只是有朝一日的破繭成蝶。
也是,所有的吶喊被咽下去,所有的豪情被收起來,象一頭二月黃牛,默默踏步,無聲前行。
方染的高三是在倒計時中開場的,又在撕書中結束,對于高三那一年的印象已經很模糊,最清晰的,還是一個又一個夢境。夢裏,她們從高三的班級往樓梯下走的時候,所有樓梯突然一階一階倒塌,她愣愣在高三的那個樓層,下不來。
這個噩夢跟了她很多年。
最後的最後,她也在這場意志之戰裏功敗垂成。
所以,時至今日,她依然說不出那段話,賀舒婷那篇文最後的那段話:
當你在若幹年後某個悠閑的下午,回想起自己曾經的努力和放棄,曾經的堅忍和耐力,曾經的執着和付出,曾經的汗水和淚水,那會是怎樣一種感動和慶幸,怎樣一種欣慰和尊敬——尊敬你自己。
但她希望,所有煎熬着走過黑色高三的人,都能在若幹年後,驕傲地對自己說,尊敬你自己。
作者有話要說: 這一章,大部分來自百度,寫得頭疼,好想睡覺的說。---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