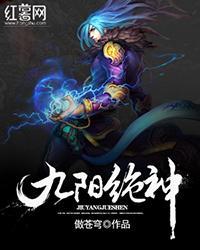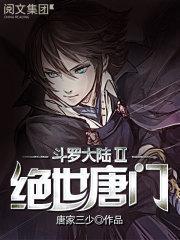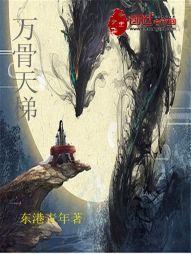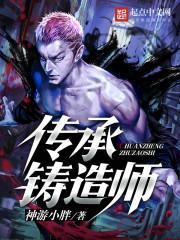第1章 ☆、那就從那天說起吧
這些都是海泠給我講的故事,海泠是我奶奶。她說現在會叫她這個名字的人幾乎都不在世了,爸爸媽媽不在場的時候,我這麽叫她也無妨。
我很喜歡海泠。爸爸媽媽總說我瞎胡鬧,只有海泠會陪我一起瞎胡鬧。
海泠說她給我講的那些故事都是真的,它們如期在她面前發生,就像春天裏從石縫中抽出的小芽。
只是這些小芽實在長得太過離奇,讓我覺得它們的可信程度并不比手游的氪金爆率更高。然而海泠非說都是真的,那就當它們是真的吧。
畢竟我跟她吹牛的時候,她也全都當真了。
海泠年輕的時候,在家鄉小鎮上做着圖書館管理員。這鎮子臨海,鎮上只有一家圖書館,圖書館裏也只有一個管理員。
圖書館是在她家祖宅上改建的——改建原因不重要,反正和不可說的那十年有關;總之海泠的爺爺,和爺爺的兄弟們費了老大的勁,總算保住了家裏那堆據說是從明代傳下來的書。
明代傳下來的,距離當時五百多年,基本等同于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的時間——裏面如果有個書蟲什麽的,可能已經成精。只是海泠沒看過那些書,一本都沒看過。她單知道有這麽一堆發黴發脆的舊紙囤在閣樓上,僅此而已。
畢竟讀書人未必都有着先進的思想和觀念,至少她的爺爺不是——藏書閣的鑰匙,傳男不傳女。
然後海泠的爺爺去世了,爺爺的兄弟姐妹也一個個不在了;還剩下她老年癡呆的奶奶,躺在姑姑家的床上,每天早上醒來,腦中的記憶都像洗過一樣幹淨。
然後圖書館蓋起來了,舊書都收進閣樓,新書被擺上架子,三層小樓差個管書的。左左右右的親戚都不想幹這活——政策剛剛放寬,鎮上有點想法的青年壯年都趕着下海發財撈金子,誰還想在老屋子裏守着這堆發黴的書?
海泠說那我來吧,反正我也沒別的事好做。
海泠小學才上到一半的時候,媽媽就成了相框裏的一張照片,現在爸爸也加入下海撈金的大軍,從這個臨海小城去了另一個臨海小城——被某個老人畫過圈的那個。他這一走之後,除了彙款單,很少再有別的音信。
海泠每天早晚出門回家,玄關都只擺着她一個人的鞋子。
那一年,海泠18歲零6個月,她的世界只有縣城那麽大。關于未來,她的想法十分簡單:順其自然。
換句話說,沒有想法。
Advertisement
她并不是很想留在家鄉,也并不是很想像爸爸那樣出去;反正,在打定确實的主意之前,守好這個圖書館,以及三樓那一屋子書,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海泠接過了圖書館的大門鑰匙,每周二至周日,早八點至晚五點,坐在木質發黑的櫃臺後面,有時看書,有時看天。
我說那多無聊啊,沒別的事做嗎?
海泠說也不是整天都坐着沒事幹,開館前和閉館後還要擦桌拖地,整理書架的。
好吧。
高中畢業生留在家鄉建設家鄉,這在當時是值得上報宣傳的事。海泠說,她還接受過縣城的記者的采訪,婦女節一次,青年節又一次。
我見過其中一篇稿子,在爺爺的剪報本裏——确切地說是其中一篇稿子的配圖:文字全被剪了,只剩下黑白相機拍攝的年輕管理員的照片,小小一塊,還沒豆腐幹大。
老實講,以當時的紙質和印刷技術,根本看不清五官,發黃的舊報紙上只能看見海泠的眼睛,又圓又亮,像兩粒黑豆豆——但這一小塊報紙被整齊地裁下,細心地熨平、塑封,夾在剪報本的最前面。
海泠說這張報紙出版的時候,爺爺還在大學裏念書,這一頁是他後來去找來的,跑了好多舊書店和圖書館,還去了報社,差點就要去造紙廠翻垃圾了。
瞧瞧這炫耀的嘴臉。
我看過海泠的老照片,也是黑白的,四周邊框上剪着一圈細致的花紋,還用金色的筆寫着某年某月某日,攝于某地。
畫面最中間的姑娘,十八九歲,臉蛋圓圓,倚着欄杆轉身望向鏡頭,唇角含笑,黑眼睛亮得像打濕的星星;她碎花襯衫的領口上系着一束柔軟的蝴蝶結,齊耳的發尾被風吹起,仿佛在水裏招搖的海葵。
雖然海泠沒說,但我從她照片上的眼神判斷,這一定是爺爺拍的。
我也看過爺爺年輕時候的照片,二十來歲,頭發一絲不亂,襯衣像紙一樣挺括;他坐在桌邊,手裏握着支鋼筆,目光深沉地對着一本攤開的書,看起來像個做大學問的學究。
海泠說他才不學究,這都是擺拍,假正經。
雖然我沒見過爺爺本人,但我覺得,對着家裏那兩個大書房,以及鏡框裏那份年代悠久,蓋滿紅戳的學位證書,海泠的這句話根本毫無說服力。
我說,那你們是怎麽認識的?
海泠停了一停。
“我是從‘開始’開始講,還是從‘認識’開始講?”她看着我的眼睛說。
我說,從認識開始,開門見山,直切主題,最好十句話講完,狗糧吃多了撐。
然而海泠并沒有采納我的意見,她本來也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見。她擡頭望向天花板,望了好一會兒,然後視線像陽光裏的灰塵一樣緩緩落下。
視線沉入地面的時候,海泠籲了口氣,仿佛從一團亂糟糟的毛線裏找到了線頭。
“那就從那天說起吧。”
我以為會是發生在小鎮圖書館的爺爺奶奶羅曼史,然而并不是。
從這裏開始,海泠的故事朝離奇的方向一路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