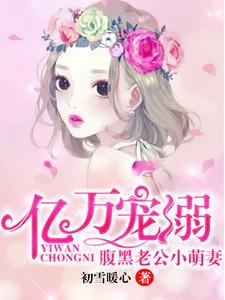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7章
雨下了一整夜,清晨,淩珊推開公寓的窗子,看着已經放晴了的天,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
向樓下望去,早晨的布達佩斯街道……依舊很安靜。
還是有點不能适應啊,想想看真有點懷念中國街道那種熱鬧的氛圍,現在這種安靜總讓她覺得有些不安、不真實……是她太閑了嗎?
明天她就要到那所小學開始正式任教了,要備的課她也已經準備上好多遍了。
看向立在牆角的那把黑色雨傘,淩珊立刻從昨天穿着的牛仔褲的口袋裏取出了那張便簽紙。
捧着谷歌地圖,搜索了一下那個男生寫給她的地址。
離她住的地方很近啊,就隔着一條街,走路十分鐘就能到。而且……他媽媽開的居然是一家中餐館!
想起他說過自己小時候在中國住了三年,看來他們一家子都挺有中國情緣的。
……
想着太早的話餐館大概還沒有開始營業,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淩珊才按着導航來來到了那家中餐館。
餐館規模并不是很大,挺普通的,和那條街上其他的店看起來沒什麽區別。
走進一看,店內的裝潢很有中國風情,尤其是牆上挂着的那幾個醒目的大號中國結。當然,對她而言是沒什麽新鮮的,但對老外們來說應該挺新奇的吧。就像在國內的人去了西餐廳、咖啡館、西式甜品店什麽的,總愛拍幾張照發朋友圈,自我感覺挺優雅、有品位、有情調的。
好吧,她大學的時候也沒少幹過這種事。
但是現在反過來,站在一個西方國家的中餐館,換個角度來思考……突然覺得以前幹那種事挺傻帽的,呵呵。
不一會兒,走來的一位年輕女服務員便走了過來,招呼她坐下。
一知半解地聽着這位服務員姑娘對她說的匈牙利語,當姑娘好奇地問她是中國人嗎,她回答了句“是”的時候,姑娘明顯眼睛亮了一下,笑得很甜。
Advertisement
這時,淩珊環顧四周,發現店裏其他桌坐的都是西方人,就她一個中國人。
也對,中國人在國外如果想吃中餐的話,一般都會找中國人開的中餐館,味道正宗。而外國人開的中餐館,就和在國內中國人開的西餐廳一樣,為了配合本國人的口味而做有一些改變。
以及……中華料理實在是太博大精深了,一般老外真心做不來。
當菜單被遞到自己手裏時,雖然想着自己只是為了還傘才來到這裏,但既然已經到吃午飯的時間了,淩珊決定幹脆就在這裏吃了吧。
好多天沒吃中國菜了,她的舌頭和胃還真的挺想大中華美食的,雖然估計這裏做的不正宗。
看了看菜單,發現每道菜都是匈牙利語、漢語、英語三語标明,以方便客人閱讀。匈牙利語的她是看不大懂,但是這些菜名英語翻譯的……好多都是字面直譯啊,簡單、粗暴、讓人想笑。
擡手掩唇遮住了嘴角的笑意,笑不露齒、笑不露齒,公共場合她要維護中國人的形象啊。
“這道菜,再加一份米飯。”淩珊向服務員姑娘指了指菜單上的那份地三鮮。
點完餐後,等菜期間,淩珊也悄悄地打量着四周。
大概因為這家餐館裏坐着的都是西方人的緣故,所以同那些正宗的中餐館裏的氛圍不同,很安靜,依舊遵守着他們西方人的用餐禮儀……啊,啊,吃中餐就是要熱熱鬧鬧的才有氣氛啊!
再看向角落裏的那桌,坐着的一男一女半天用不好筷子,不一會兒就從手中掉落,把二人給急得不輕。
淩珊偷笑着随手拿起桌上的餐具盒裏放着的筷子,靈巧地把玩了一下。
不少西方人都很驚奇東亞人是如何做到用兩根棍子就能吃飯的,她一直将其得意的歸結為……誰讓我們心靈手巧~
菜上來後,原本并不抱着多大的期望,結果嘗了一口……竟然挺正宗的!難道這家中餐館雖然是匈牙利人開的,但廚師是中國人?
剛準備再夾一筷子時,卻聽到了隔壁桌爆發出了争執聲。
只見桌旁一個戴着眼鏡的客人很憤怒地說着什麽,一旁站着剛剛的那位服務員姑娘和一位看上去有五十來歲的中年婦女。
服務員姑娘一臉焦急,而那位褐發、身材有些發福且衣着樸素的中年婦女則是面色平靜、耐心地應對着那位客人的指責。
淩珊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去。
那個客人應該不是匈牙利人,操着一口說出上來帶着哪國口音的英語,淩珊仔細一聽……頓時又無語又想笑。
原來那個客人憤怒是因為……他點了一道魚香茄子,然而菜裏只有茄子沒有魚,讓他覺得這是一種欺詐消費者的行為。
那位中年婦人一遍遍地解釋着這道菜真的就是這樣,但那位客人就是不依不饒,不停地指着菜單上那道菜的英文标識。
淩珊記得之前她看菜譜時有被“魚香茄子”的英文翻譯給嗆到,“魚香茄子”比較正宗的翻譯應該是“Yu-Shiang Eggplant”,然而那份菜譜上簡單粗暴地直譯成了“Fish and Eggplant”——“魚和茄子”。
嘆了口氣,雖然別的客人和店家間的糾紛跟她沒什麽關系,但這種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問題,她一個中國人還是發聲比較好。
“不好意思,先生,我想要說一句……魚香茄子這道菜,它真的沒有魚。”淩珊站起身來,用英語對着那邊說道,為了證明自己話的真實性,又特意補充:“我是中國人,那道菜我從小就吃。”
突然插入的話,瞬間讓整個餐館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淩珊的身上。
這種全場矚目的感覺,讓心理素質向來不咋地的淩珊一瞬間有點小緊張,盡管她說的是大實話。
“中國人?那麽,這道菜裏如果沒有魚的話,為什麽要叫魚和茄子?”皺了皺眉頭,那位不知來自哪國的客人依舊表情相當不滿。
“我剛剛也有看那份菜單,所以,首先,我必須要說的是,那份菜單上的英文翻譯有不少錯誤,比如這道菜,應該是‘Yu-Shiang Eggplant’而不是‘Fish and Eggplant’。但我想這家店也并非是想要欺騙客人才如此翻譯,因為這道菜的中文名字裏也的确帶有‘魚’……”
淩珊的解釋還沒完,那位客人的表情便由不滿轉為了不解,滿滿疑惑地打斷了她的話:
“既然你說這道菜裏沒有魚,那為什麽你們中國人還要在給這道菜起的名字裏加上‘魚’?”
“因為這道菜的背後有一個故事。這是來自中國四川的一道菜,四川,你知道嗎?就是……大熊貓的老家。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四川有一戶人家非常喜歡吃魚,他們家在做魚的時候也會準備多種調味料來使魚的味道更棒。有一天晚上,這家的女人為了不浪費上次燒魚時留下的調味料,便把調味料和在菜裏一起炒了。她以為這樣做出來的菜會不好吃,擔心丈夫會不高興。結果丈夫回家吃了那道菜後,卻贊不絕口,覺得非常美味。然後,這種做菜方法就慢慢流傳下來了。在中國四川的菜系裏,除了魚香茄子外,還有魚香肉絲、魚香三絲、魚香豬肝,這類菜的絕妙之處就在于用燒魚的調味料來炒,因此名字裏才帶有‘魚’。”
一口氣把魚香茄子的來歷用英語說了出來,淩珊瞬間有一種想要淚流滿面的成就感……尼瑪啊,大學英語六級口試的時候她都沒把英語說得這麽溜過!
以及,還好作為一屆吃貨的她大學選修課選過“中華飲食文化”這門課,不然被老外給問住了那就尴尬了,還怎麽展示自己的逼格啊。
而整個餐館的客人全都目光炯炯地看着淩珊,認真聽完後,一個個地露出了“原來如此”的表情,還挺誇張的。
其中一個年輕的男士甚至感性地表達着自己的看法:“哦,浪漫的故事,體貼的丈夫,我喜歡,我也要嘗一下那道菜。”
淩珊感覺自己的思路有點跟不上趟……這個故事浪漫在哪裏了?以及,兄弟,你的重點抓錯了吧?
不過,她這也算是無意間在這家餐館裏宣傳了一下中華美食文化。
昨天講成語,今天講飲食……為什麽她突然有一種古代傳教士的感覺?
……
待到這場風波平靜後,淩珊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繼續慢條斯理地吃着自己的飯。
待到快要吃完,想着要不要見一下店主好把她兒子昨天借她的那把傘還回去時,桌子上突然多了一小碟菜。
身為專業吃貨的淩珊一眼就認出了,居然是東北很有名的鍋包肉!
擡起頭,只見是剛剛那位身材稍微有些發福的中年婦女放到她的桌上的。
剛想開口說自己沒有點這道菜時,卻見這位匈牙利婦人溫和地張口用中文對她說道:
“這道菜是我請你的,謝謝你幫我解圍,也因為你的講解,剛剛有好幾桌客人都表示要嘗嘗魚香茄子那道菜。”
淩珊愣了一下後,頓時便明白了。
這位阿姨應該就是這家店的店主了。
……和昨天那男生一個腔調的東北話。
“謝謝,那個……您是這家店的店主吧?”雖然猜到了對方的身份,但淩珊還是禮貌地先詢問一下。
“哦?你怎麽知道我是店主的?”婦人那雙琥珀色的雙眸明顯一亮,說話間又指了指餐桌對面的座椅:“介意我坐這兒嗎?”
“當然不。”淩珊連連擺手,同時也注意壓低了聲音,畢竟西方人在用餐時交談都是非常小聲的:“我猜您就是店主,是因為您和您的兒子的中國話都說的相當好。”
……其實她更想說你們娘倆那東北話一聽就是一個旮旯裏出來的。
說完後,又趕忙把之前被她立在牆邊的雨傘拿起,遞給了婦人。
“其實我今天來這兒主要是為了還這把傘的,昨天我在漁人堡參觀的時候遇到了大雨,您的兒子把傘借給了我。他給了我這裏的地址,說是我把傘還到您這兒就行。”
“伊諾克昨天去了漁人堡嗎……”接過傘後,婦人若有所思地喃喃了句,随即意識到對面還坐着淩珊,笑着說道:“還沒有做自我介紹,我叫摩爾納.凱蒂,是這家店的店主。伊諾克是我兒子的名字,摩爾納.伊諾克。”
因為歷史上與東方人的淵源,匈牙利人的名字也是姓氏在前,名字在後,這在歐洲是獨樹一幟的。
淩珊在培訓的時候有學習過這點,所以也禮貌地回複:“你好,摩爾納太太,我叫淩珊。非常感謝伊諾克昨天幫我,他不僅借了傘給我,而且還幫忙阻止了小偷偷我的包。”
摩爾納太太倒是眨了眨眼,眼中劃過了一絲的調皮:“在浪漫的多瑙河畔與一位美麗的東方姑娘邂逅并向她伸出援手,這是他的幸運。”
被這麽一調侃,淩珊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拿起水杯喝口水來掩飾自己的尴尬。
心中禁不住感嘆了一下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這位阿姨心态可真年輕……反正她老媽是絕對不會說出這種話的。
“淩——珊——”摩爾納太太又試着念了念淩珊名字的發音,念得有些繞口:“不好意思,我的中文沒有我兒子說得好,是這麽念的嗎?”
“嗯,差不多。沒關系,您叫我Ling就好。”
剛剛那幾句話後,淩珊便聽出來了,摩爾納太太的中文确實沒有她的兒子伊諾克說得好,發音要更加生硬一些。雖然伊諾克東北腔十足,但“陰、陽、上、去”這漢語的四聲發得還是比較标準的。要知道,外國人學習漢語的一個大難點就是漢語的聲調。
而似乎是找到了可以和自己暢談的中國人,摩爾納太太也聊起了她的中國情緣:
“我丈夫還在世的時候,做過中匈貿易的生意,所以我們一家當時在中國的沈陽住了三年。剛到沈陽的時候伊諾克才三歲,離開的時候也就六歲多一點。那個年紀的孩子,正是學語言學得最快的時候,所以我們全家就屬他漢語說得最好。他六歲回匈牙利的時候,反而匈牙利語不怎麽會說了,當時讓他小學的老師很苦惱呢。”
專業學過語言學方面課程的淩珊對此表示很贊同,那個年紀的确是掌握語言的一個高峰期。
“我這家餐館其他的菜我不敢說,但東北菜應該還是很正宗的,畢竟可是有我把關的。”摩爾納太太自信地說着。
淩珊指了指她快要吃完的那道地三鮮,然後笑着豎起了大拇指。
難怪她剛剛覺得這道地三鮮做得相當不錯,想來送她的這個鍋包肉應該也很正宗了。
當然,她沒好意思說的是,之前她看了那位戴眼鏡的客人點的魚香茄子,只一眼,她就覺得那道川菜做得絕對不地道。
……誰家魚香茄子放芝士啊。
“Ling,不知我這樣說是否有冒犯到你?如果可以的話,能幫我看一下我這家店菜單上翻譯的錯誤嗎?你剛剛說菜單上許多翻譯錯誤,可以幫我糾正一下嗎?”摩爾納太太真誠地詢問。
淩珊一瞬間有些為難,不是她不願意發揚中華民族助人為樂的優良傳統,而是……有好多菜她也不知道正宗的翻譯應該是什麽。
估計她剛剛展示的那一下逼格,把在場所有人都給唬住了,以為她是個中外文化交流通,其實她也就是個半吊子。
“其實,有許多菜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麽翻譯”淩珊直接實話實說,但随即話鋒一轉:“不過如果可以的話,給我一份菜譜,我可以帶回去研究一下怎樣翻譯比較标準,過幾天還給您。”
“哦,真的嗎,非常感謝你。”摩爾納太太欣喜地說道,“那麽,下次來時,我請你吃正宗的匈牙利菜,熱心的中國姑娘。”
淩珊原本下意識地要按照中國式思維謙辭推讓一下,比如說些“哎呀,別這麽客氣,不是什麽大事。”“沒關系,不用這麽麻煩啦”之類的。
但想到這裏不是中國,說話做事還是入鄉随俗比較好,所以也就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對方的好意:“好的,非常期待正宗的匈牙利美食。”
答應對方這個翻譯菜譜的請求,一方面是因為這本就與她目前的職業有關,正好借此機會學習一下。
另一方面,她承認,她是有點小私心的。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她孤身一人在布達佩斯,多認識一點人總是好的。她畢竟要在這裏生活上差不多一年,在這座城市建立點關系網是必要的。
她對摩爾納太太和伊諾克這對兒母子印象相當不錯,這樣一來二去應該也能與他們熟絡一點。
當然,想要獲得別人的善意,自己也要有所付出,所以她也會和他們真心相交的。
作者有話要說: 淩珊的逼格值與好運值……已經耗盡了,接下來她就該面對獨自身在異國的一件件苦逼事了,沒有誰的路會是一帆風順的。
PS.對于魚香茄子的來歷我也是查的,應該會有不同的版本,這裏選取的是流傳比較廣的一種。
歡迎大家加我的現言文讀者群:580097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