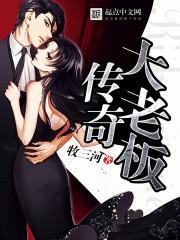第13章 七月流火(三)
三、
顧岳和往常一樣雞鳴即起,借着朦胧星光,迅速穿衣洗漱,隔壁房裏李長庚也起來了,兩人一道跑至演武場,不多時人已到得差不多了,顧岳略一計數,大概有成年男丁五十餘人,半大少年三十餘人,又有二十來個年紀不一的男童,只不見女子身影。李長庚小聲向他解釋道,女眷早上忙于家務,所以習武操練大多是見縫插針,不限時不限地,連帶着各家女童也都在自家房前屋後由長輩女眷順手教導。
顧岳不免覺得,這樣一來,各家女眷用功不夠,功底肯定不足;可是昨晚看她們輕輕松松游刃有餘地将十幾個幼童抛來擲去,下盤穩當,眼力準确,反應敏捷,臂力足夠,功底都很紮實,這又讓他很是不解,難道說李家橋的女眷習武另有訣竅?這也不太可能吧?
而此時鐘聲響起,操練時辰已到,演武場立時靜寂下來。
今日領隊操練的是李長庚的父親李水厚,站在演武場上方一尺來高、條石為基的土臺上,待到鐘聲停歇,便起頭一句:“天地有正氣――”一邊高聲吟誦,一邊拉開了明山拳的架式。底下近百人,也在高聲誦念的同時沉身下腰,起手回腕,蓄力出拳,一字一頓,“氣”字吐出,正好将沖山式完全施展開來。
《正氣歌》共計六十句,明山拳也正好六十式,一句一式,句意與拳勢恰恰相配,巧合得讓顧岳一直都在猜測到底是明山和尚傳下的拳法原本就暗合《正氣歌》的詩意、還是那位神通廣大的張天師特意為配合明山拳選了這首《正氣歌》傳給顧家。
不過,能夠将這六十句配着拳式一路走完的,不過十來人,其餘人或是氣短氣促、呼吸不暢,或是詩句不熟、丢三拉四,又或者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兼顧,陸續都停下了吟誦,收斂精神專心打拳。
李長庚在第四十五句時停了下來,已經是年輕人裏非常拔尖的了。
所以堅持到最後的顧岳,十分醒目,不時有人以眼角餘光向這邊打量。
操練完畢,東方已是晨光初現,衆人都急急趕回家去拿農具準備收割,即便對顧岳很感興趣的人,也沒這個閑暇來試探了。
李長庚帶着顧岳回自己家拿了鐮刀和扁擔,到村口與其他人彙合。
收割季今日便要開始,全村男丁,除了家中的确有事和負責警衛防匪的十三人,其餘人都要先去顧韶韓的田裏割禾,即便如此,因着田地不少、搶收如搶火,顧韶韓還是得從外村另請十個幫工,要趕在這短短三四天裏收割、脫粒、晾曬、去秕、歸倉、垛草,以免耽誤後頭的人家收割,又或是遇上夏日暴雨壞了收成。
到得田邊,顧岳毫不意外地看到,數十人早有默契一般,一伍一什地分成了小隊,各有年長者為伍長什長,按着顧韶韓劃定的分界,各據一片稻田,悶頭開割。
顧岳自然與李長庚分在一伍。伍長是李長庚的一位堂祖父李高升,另外兩人則是顧岳的族叔顧學韓與族兄顧望岳。
李高升打量着顧岳:“學生伢沒幹過農活吧?讓長庚多教教。鐮刀也是刀,李家橋的男伢兒,哪有玩不了刀子的?”
李長庚笑着答應,帶着顧岳走到田埂邊那一壟,免得礙着另外三人,先割了幾把示範給顧岳看,然後才直起身,摸摸頭,想着應該怎麽解釋給顧岳聽,只是這樣喝水吃飯一樣簡單自然的事情,太熟悉太習以為常的動作,一時之間還真不知道怎麽去教人,想一想才道:“要不你先試着割幾把我看看?”
顧岳掂了掂手中的鐮刀,四下裏看了一回,轉頭問李長庚:“斜刀?腕力?”
李長庚又試了一把,恍然明了:“對,對,是斜刀,是腕力。橫刀容易被稻杆挂住,用臂力又太費勁了。嘿,你讀書多,還真是不一樣。來吧,咱們得盡快趕上前頭的人,不能落太遠。”
他們這一伍的另外三人,已經割到前頭好一段了。
顧岳與李長庚并肩排開,彎腰割禾。
李長庚手掌寬大,一把攏過來的稻杆比尋常人要多個兩三成,又是手長腳長,一彎腰便比其他人多罩住兩三行稻谷,是以同樣五步一垛,李長庚順手在身側堆出來的稻谷垛,很顯然也要比其他的稻谷垛更高大一些,他的周圍,清出來的空地也明顯更寬大一些,不多時便将顧岳抛到了後面好一段。
顧岳悶着頭揮鐮割禾,開始時的動作自然還有些不太熟練,畢竟鐮刀對于他來說太過輕飄,一時之間不太好把握,過得片刻,才慢慢體會到掌中木柄的細微顫動與彎如新月的刀鋒斜斜劃過稻杆時的流動,動作雖然不曾加快多少,但已流暢許多,少了最開始的那份生硬。
稻田裏的水早兩日便放得差不多了,泥土半幹不濕,赤腳踩在上面,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泥土中的草莖。今年的年成不錯,稻谷生長得密不透風,晨風從頭頂掠過,絲絲涼意也随之掠過,朝陽初升,不知不覺間,顧岳已經大汗淋漓,金黃的禾葉時時從手背、手臂、小腿乃至臉頰邊劃過,留下的劃痕被汗水刺激得隐隐生痛。而因為長時間地以同一個姿勢彎腰勞作,顧岳感到自己的動作已經不像剛開始時那樣靈活了。
顧岳咬牙堅持着不去四面張望,他只需要知道自己還沒有趕上李長庚就行了。
李長庚一壟割到頭,反身又從那頭往這頭割,交錯之時,也只默然而過。
顧岳是悶頭苦幹,李長庚是打定主意要早早割完自己半邊,好去給顧岳幫忙,自然不可分心去打招呼。
日頭漸高,村中各家女眷送早飯出來,李長庚招呼顧岳上田埂來,一道到江邊去洗手洗臉,江邊有十幾株大柳樹,正好在樹蔭下休息吃飯。顧韶韓只包他請的外村幫工的飯,其餘人都是自家送飯,家境好壞,飯碗上大致可以看得出來,不過大多還是按緊了紮紮實實地裝了一大海碗白米飯,再壓上幾塊鹹肉臘魚,加點腐乳,澆點鮮紅的剁辣椒――這是農忙時節,不吃飽吃好一點兒,哪有力氣幹活?
因着顧岳遠來是客,大姑姑還特意在他碗底卧了一個荷包蛋。
翻出來時,顧岳有些窘迫地看看李長庚,想要分半個給他,又覺得這樣做似乎更不合适,李長庚完全不覺得這有什麽不對,大姑姑更是一巴掌拍在顧岳頭上:“快吃,我還等着洗碗去!”
休息了片刻,趁着太陽還不算高,大家還得抓緊了再幹個把時辰。不過這一輪,每伍都要輪流分出兩個人來打稻。顧岳這一伍的打稻桶,早上出來時,便由伍長李家叔爺扛了過來,此時正擺在收割過的田地中央。上寬下窄的杉木桶,開口這面,長約六尺,寬約三尺,高只二尺許,三面均內豎篾席,以免摔打稻谷時谷粒飛濺出去;打谷這一面的木板,往往要額外加固一層,并且不可過于光滑,以便于脫粒。
李長庚和顧岳排第一輪,兩人先将附近的谷堆都抱到打稻機兩側來堆好了以便于随手取用,打稻倒無什麽特別的訣竅,不過是動手不動肩、高揚重打、每摔打一次都要記得輕輕抖動稻束好讓谷粒更快脫落而已。至于如何才是用力得當,既不至于浪費力氣,又能夠盡快将稻穗上的谷粒摔打出來,看看旁人如何做,自己再做幾次,自然明了。
李長庚一邊給顧岳示範,一邊不無自豪地說:“打谷費的是牛力,別村的男丁,一個時辰最多只能打一分田的谷子,咱們村好些人都可以打到一分半,手腳最快的差不多可以打兩分田,所以咱們村的谷子,每年都收得最快。”
脫落在打稻桶裏的谷粒,積到半桶,李長庚與顧岳便擡着木桶将谷粒傾倒在籮筐裏,裝滿谷粒的
籮筐則整整齊齊地擺放在田埂邊。
暑日漸漸當空,汗下如雨,飛揚的稻芒和着汗水一道刺人肌膚。
陸續有人收工,各挑着一擔谷粒,晃晃悠悠地回村去。
顧岳有些緊張,自己這個生手,是不是拖了後腿?他們這一伍,似乎落在後面?不過也不好四處張望,仍是埋頭專心打稻。
好在等到他們收工時,稻田裏還餘下兩三個伍不曾完工,他們這一伍并沒有落到最後面,這讓顧岳多少松了口氣。
鐮刀都收在打稻桶裏,用稻杆蓋一蓋以免被曬得太燙了。李高升拍拍顧岳肩膀:“不錯不錯,學生伢很吃得苦。沒挑過重擔吧?先挑個八分滿,免得撞翻了反倒麻煩。”
李高升和另兩人挑着籮筐先走一步,李長庚将顧岳那一擔裏的谷粒勻一些到別的筐裏去,顧岳想要阻止,李長庚道:“高升叔爺說的有道理,你以前沒挑過重擔,這可不是力氣大下盤穩就行了。咱們村的籮筐又比別的村大,他們一擔一百三十斤,咱們村裏一擔夠裝一百六十斤。還是先別滿挑的好。”
扁擔一上肩,顧岳就知道李長庚的話是什麽意思了。平日裏不論父親的要求還是講武堂的訓練,講究的都是立如松,行如風,坐如鐘,腰直背挺,眼明手快,如刀在鞘,如弓欲張;然而重擔在肩時,挑擔人卻得像那根顫悠悠的老竹扁擔一般,彎而不折,韌而有力,腳下步履配合着籮筐起伏搖擺的節奏,慢慢加快,卻又不能快到失去控制。
顧岳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呼吸與步伐,不斷調節快慢輕重,注意扁擔在肩頭的位置,帶好套住籮筐的繩索,穩住下盤,以免被晃動的籮筐帶偏,耳邊不時飄過其他人的說笑之聲。李長庚在他前頭,邊走邊說:“聽說騎馬的講究也差不多是這麽回事,騎的人得控緊了缰繩,還得合着馬的步子去。”
顧岳“唔”了一聲。
滇馬瘦小卻能負重,善走山地,當地人多用來馱貨,不怎麽騎乘,顧岳也只騎過幾回,不過現在回想起來,似乎也的确如此,當騎者随着馬行的步子,或左或右,或起或伏,在鞍上輕輕搖晃身體,讓自己與馬兒成為一個整體時,不論騎者還是馬兒,都要輕松許多。
進了村子,将籮筐裏的谷粒倒在演武場上,再用木耙耙平攤開,在烈日下曝曬。
李長庚将籮筐疊放在演武場側邊的木棚子裏,顧岳注意到,木棚裏頭的橫欄上,每隔一段便挂着一個木牌,上面标着各伍伍長的名字,各伍的農具,包括今日挑谷的籮筐和扁擔,都放在這個木牌下頭。
顧岳不免好奇:“咱們村裏的人都能識字?”
李長庚:“比別村的人應該多一些吧,至少都認得自己的名字,家裏能吃飽飯的,也多少上過幾年學,柏樹灣小學堂不收咱們村學生的學費的,只收書本費。”
顧岳略一想便明白了,柏樹灣小學堂的校産,其實大半是何思慎的家産,不覺感慨地道:“何姑父毀家興學,真是造福一方。”
李長庚點頭:“是啊是啊,所以六丙瞎子才說,姨父将來肯定是要進縣志的。哦,六丙瞎子也姓何,聽說原來不是瞎子,因為算命太準了,老天爺看不過去,弄瞎了他一只半眼睛,現在只留下半只眼,三步之外就看不清人了,話也不敢明說了。姨父将來要進縣志的話,還是他瞎眼之前說的。”
李長庚話語之間很是得意,連帶得顧岳也隐隐生出幾分與有榮焉的自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