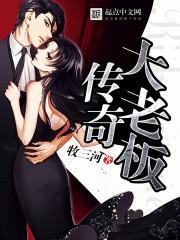第23章 鼓盆而歌(一)
天剛蒙蒙亮,顧岳已經起來了,洗漱之後,仔仔細細地打上了綁腿。昨晚從衡州回來時,大姑姑告訴他,今天得去山裏祭掃祖墳,來回五六十裏的山路,因此出發前一定要好生準備一番。
匆匆吃過早飯,帶好幹糧清水,還有必不可少的槍枝子彈以及傷藥蛇藥,背了鬥笠,大姑姑又找了一柄短刀讓顧岳插在背包側邊,這才送他和大姑父一起出門。清明節、中元節和臘月二十八的三次祭掃,各家的男丁常是輪流進山,大姑姑家這一次便輪到了大姑父。顧岳沒滿十八歲,原本是不需要進山的,但是今天還要将戰死異鄉的顧品韓的靈牌下葬,顧岳的母親當年病逝後葬于昆明,她的靈牌也得一道下葬,是以顧岳今日必得背着靈牌一起進山。
今天進山的男丁,總計四十八人,由顧韶韓帶隊,分出四什之外,又另分出前哨與後衛兩個小隊,每隊各四人,每隊帶兩條看家狗。衆人輪流充任前哨後衛,整個隊伍滾動前行,戒備森嚴,正是行伍本色。
中途停下來休息時,顧岳和大姑父這一什裏還有另外一個初次入山的李姓少年,名叫李長壽,算起來是大姑父沒出五服的堂侄,不解地問大姑父:“守業叔,張鬥魁剛剛被招安,大明山上一時半會出不了大夥土匪,就算有些小夥毛匪,也斷斷不敢來招惹咱們這一大幫壯丁,怎麽大家還這樣緊張?”
顧岳心中也有這樣的疑問。行軍理應戒備,但張鬥魁剛被招安的這會兒,大明山上應該暫時沒人敢來招惹他們這一大隊人馬,為何還是如臨大敵一般?
大姑父不以為然地搖頭:“長腳鄭七剛剛被打跨的那年中元節,很多人就是你這麽想的,結果進山時被一夥只有七個人的毛匪偷襲,綁走兩個後衛,勒索了一大筆贖金,還害得咱們李家橋被周圍十裏八鄉笑了半年,就算後來打掉了那夥毛匪,也不是什麽光彩事。”
他們這一什的什長,是割禾時顧岳他們那一伍的伍長、大姑父的堂叔李高升,剛剛巡查回來,坐下喝水,聽了大姑父的回答,已經猜到李長壽先前的疑問是什麽,在一旁補充道:“咱們這般警覺小心,不只是防範毛匪,也是為了防範野獸。這大明山上,曾經出過紅毛野熊。老人們都說,入山之人,最怕的是一熊二豬三老虎,更何況是紅毛野熊?那是連老虎見了也要逃跑的狠家夥。”
顧岳訝異:“紅毛野熊?”
李高升:“是啊,老輩人說,那是從神農山跑出來的人熊,力氣比熊還大,又有人的聰明勁兒,難惹得很。聽說明山和尚當年被一隊清兵追捕,一直追到山裏頭沒路的地方了,眼看着逃不過去,虧得遇上一頭紅毛野熊,那頭紅毛野熊被清兵當成獵物捉拿,發起火來,幾下子就收拾了整隊清兵,吓得清兵後來不敢再入山了。”
另一人眉飛色舞地湊過來道:“都說明山和尚是有神仙保佑,那頭紅毛野熊就是山神差來救他急難的!”
顧岳上過地理課,稍一回想,便想到李高升說的“神農山”,應該就是鄂西北的神農架,據說是神農氏嘗百草、教民稼穑之地,故以此得名,山勢高峻,綿延數百裏,草木豐盛,禽獸繁多,人煙稀少,歷代多有種種神仙志怪傳說,顧岳上中學時,一位曾經去過此地的先生,最愛在課餘時候同他們講這些志異趣聞,其中即有狀如巨熊的紅毛野人之說。神農架往南即是跨長江兩岸的巫山,據說某些地方,水道狹窄,山頂猿猴,可以借助藤蔓在兩岸山峰之間來往。巫山再往南便是縱貫整個湘西、直至湘南的雪峰山,大明山其實是雪峰山支脈。
這樣說起來,當地傳說,大明山上的紅毛野熊是從神農山過來的,倒也有幾分依據。
顧岳這麽一解釋,大家都覺得,這紅毛野熊的傳聞,更真實可信了幾分。
聽着幾位年長的叔伯你一言我一語地說着那紅毛野熊的可怕,什麽生撕野豬活剝老虎都不在話下,還有孤身進山的村民被擄走後生死不知,李長壽有些戰戰兢兢地問道:“這麽說起來,紅毛野熊對咱們李家橋還有些恩義來着,那個,咱們要是碰上了怎麽辦?”
開槍獵殺好像不太對,不開槍的話,又有些心裏打顫。
李高升一本正經地答道:“放一百個心,真到了那個時候,就把你丢給那頭野熊,它收了祭品
就會放我們大隊人馬走。”
其他人不免相視哄笑。
說起來,進山這麽多次,他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紅毛野熊,那些傳聞,說得活靈活現,認真追究起來,卻誰也說不清楚究竟是否真人實事。入山之時,如此謹慎小心,也不過是有備無患罷了,最主要的,其實還是防範出沒無常的山匪。
不過李家橋一帶,哪家小伢沒有被紅毛野熊的傳聞吓唬過?今日再吓一次,也不算什麽。
顧岳此時已經明白李高升是在吓唬他們這兩個初次入山的新丁。李長壽似乎有些膽小,這一路上,稍有風吹草動,便警覺地轉頭四處張望,先前更是被紅毛野熊吓得臉色發白,這會兒聽明白李高升的吓唬,精神才松下來,很不好意思地摸着頭笑笑,捧起竹筒喝水,想将自己的尴尬
掩蓋過去。
顧岳忍不住悄聲問大姑父:“長壽怎麽會這樣膽小?”
他看李長壽,身手還是挺矯健的,料來也是常年跟着大家一起習武練拳,應該是膽壯氣足才對。
大姑父嘆了口氣:“寡母獨子,看得太緊了些,這也難免。不過,”他正色向顧岳道:“膽小
也有膽小的好處,危險來臨,最先察覺到的,往往便是這一類人。”
顧岳恍然。他記得有坐船出海的同窗說,大海之上,船只将要傾覆之際,首先逃跑的老鼠,都說是膽小如鼠,偏偏這些東西最能見機先逃。
當然,顧岳不能将這舊聞直接說出來,以免顯得像在拿老鼠諷刺李長壽。
其他幾人仍舊樂呵呵地拿紅毛野熊的種種傳聞在逗李長壽。被吓多了,李長壽顯然大有長進,捧着竹筒笑眯眯地一邊聽一邊點頭附和。顧岳聽得有趣,不覺說道:“雲南那邊深山裏面,據說有一種猛獸名叫山魈,長得有些像猿猴,但是模樣比猿猴可怕多了,當地人都叫它鬼面狒狒,傳說曾有人看到這鬼面狒狒生食人腦,也不知這傳聞是從哪兒來的,我小時候住在外祖父家裏時,經常聽到老人們拿這鬼面狒狒吓唬各家孩童不許私自上山。”
大家不免驚訝啧嘆了一番,又有人道,八裏橋鎮子西頭有一個大池塘,據說裏頭有鬼蜘蛛,陽氣弱的小伢,一靠近水邊就會被拖進去淹死,所以八裏橋鎮上的小伢都被反複提醒,絕對不許私自下塘洗澡。
正說到熱鬧處,前頭敲梆子了,李高升立刻站起身來,喝令大家趕緊收拾集合。
繞過兩道山梁,偶然回望時,卻見後方遠遠的山坡上,不少人影正在林間晃動。大姑父望了一眼,向顧岳道:“那個山頭是杉山鋪的墳山。每次祭掃,杉山鋪總是跟在我們後頭進山,再等着我們一道出山。”
大樹底下好乘涼。顧岳立刻明白了杉山鋪人的想法。
大姑父言語之間很有幾分自豪:“沒我們村在前頭開路,周圍幾個村子的人都不敢進山。”
近午時分,一行人在竹林深處的墓地前停了下來。各家尋各家的祖墳,顧韶韓帶着他們這一房的男丁在自己祖父母的墓側挖了坑,讓顧岳将他父母的牌位放進去埋起來,那邊已經有人從山上尋了塊條石過來,顧岳按着顧韶韓的指點,用紅漆在石上寫了“先考顧品韓之墓”、“先慈顧龍氏之墓”以及“子顧仰岳立”三行字,便将這塊簡陋的墓碑樹了起來。
放眼望去,有些墓碑更為簡陋,不過一塊木牌而已,風吹雨打,字跡早已模糊不清。
像父親這樣戰死他鄉、屍骨無還的墓主,恐怕為數不少吧。顧岳心中這樣想着,同時心情卻又平靜得很。
上香燒紙、敬酒供飯之後,還要将墳頭被雨水沖掉的泥土再培厚一些,将沿途撿的石片緊緊拍入墓周泥土中,壓緊墳土,以免雨水沖涮太過。
做好這一切,何思慎從另一邊繞了過來,與顧韶韓說了幾句話,便招手叫顧岳和他們一道去祭明山和尚。
往山坡上走不多遠,出了竹林,一片向陽的大石崖下,有個一人多高的石洞,洞口上方用紅漆寫了“明山洞”三個大字,何思慎感慨地道:“這個山洞,就是當年明山和尚隐居之地,所以後人名之為‘明山洞’。”
顧岳注視着洞口那三個大字,不解地道:“那個‘明’字,是寫錯了嗎?”
本應是“日”旁,卻寫成了“目”旁。
何思慎搖頭:“不是寫錯,是有意如此。”
顧岳略一思索,有些明白了:“是因為前清時的文字獄?”
何思慎微笑:“可不正是如此?你這次去長沙,可惜來去匆匆,不然倒好往岳麓書院去看看。那裏頭的門匾楹聯上的‘明’字,也都是這個寫法。”他嘆了口氣,“這也是無可奈何之計。”
洞裏空間頗大,靠洞口處用石塊壘了個竈,石竈上方的石壁熏得半黑。石竈裏側的洞壁上,淺淺刻着一幅看不清面目的僧人像,僧人像前一尊粗糙的石香爐,香灰半滿。
顧韶韓是這一次的領隊,所以也由他領頭上香。大家輪流敬香,依次退出。
顧岳排在最後頭,目光止不住地在洞內掃了好幾個來回。這山洞裏進斜伸出一個小岔口,堪堪可以避一避洞口的冬日寒風,想來便是明山和尚的床榻所在之處,不過即便曾經擺過木床竹
榻,一兩百年下來,也已蕩然無存。迎着洞口的明亮處,與僧人像對面,倚着石壁用石塊和石板壘了一個小桌一張方凳,想來是明山和尚日常讀書寫字之用。
淡淡香霧之中,似乎依稀可以想見,明山和尚是如何在這簡陋的山洞之中自炊自食、讀書打坐,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任憑風吹雨打,堅剛不可奪其志。
默默祭完,出了明山洞,顧岳不覺長長籲了一口氣。
何思慎感慨地道:“明山和尚是咱們李家橋的祖師爺,所以每次上墳時咱們都要來祭一祭。就算是大明山上的盜匪,經過此處時也會來上一炷香,不說求明山和尚保佑,至少別得罪了他。這明山洞裏,一兩百年來香火不絕,也算是‘何陋之有’了。”
顧岳認真地點頭:“的确如此。”
何思慎看看顧岳的神情,轉而失笑。
少年人見先賢而心向往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站在明山洞外,放眼望去,隔了山谷,對面的山勢,明顯變得高峻陡峭許多,而且一峰更比一峰高,連綿不絕地延伸向視線不能及的遠方。
何思慎道:“過了這道山谷,對面那片高山,才是真正的大明山。歷朝歷代,張鬥魁那等占山為王的巨盜,占的就是那片山,所以官軍才沒法剿得幹淨。”
顧岳打量着那片山崗,難免在心中暗自估量,若是他領軍來剿匪,這等險要地勢應當如何入手。何思慎又道:“以前八橋鎮這邊有句話,說的是:過了五道嶺,才算大明山。不過現在都不講究這些了,頭道嶺那兒就都叫做大明山了。”
顧岳回頭看看明山洞:“是因為明山和尚住在五道嶺這邊的緣故嗎?”
何思慎微笑:“大概是吧。據說明山和尚到這兒時,年紀已經很老了,上不了五道嶺,只在前頭四道嶺這邊走動。不過八橋鎮這邊的人為了不暴露明山和尚的行蹤,提起來就說和尚在大明山上。一來二去,大家也就這麽将頭道嶺這邊都混着叫成大明山了。”
顧岳輕輕吐了口氣。
斯人已逝,唯留這一個簡陋不過的石洞,但是百年之後,提及其人其事,仍是讓人心生敬意。
人生至此,也算是不虛此行。
何思慎看看顧岳的神情,約略猜得到他此刻的所思所想,暗自失笑之餘,未免又有些感慨。
少年心性,終究是少年心性。
祭了明山和尚,時已正午,大家拿出帶來的飯團鹹菜清水,坐在涼風習習的竹林中吃午飯。有手快眼尖的,捉了好幾串竹鼠,還有運氣好的逮了兩只野兔,用随身帶的短刀飛快地扒皮剖腹,切成細條,抹了鹽和辣醬,穿在竹枝上,生了火烤得焦香,大家每人分了一兩串,祭過祖先的米酒也被端了過來,沒那麽多杯子,輪流就着碗喝,間或還有人劃個酒令猜個拳,也沒人覺得不應該不妥當。
這樣輕快的氣氛,一掃方才的肅穆乃至于沉重。
顧岳稍稍有些不太适應。不過,又奇異地覺得,似乎這樣輕松愉快祭掃先人,也沒什麽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