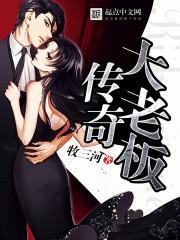第25章 鼓盆而歌(三)
戲臺在八橋鎮南岳大帝廟的正殿前頭。顧岳一行人趕到時,戲臺前面,已經擠滿了人。張鬥魁那個駐防連都在兩側的半邊樓上看戲,張鬥魁自己和莫師爺則同八橋鎮這一帶的頭臉人物坐在戲臺正前方,除了莫師爺仍是折扇不離手,其他人都是一把大蒲扇不停地搖,趕走身邊腳下亂轉的蚊子。何思慎自然也在其中,隔了人群看見顧岳,好一會才認出他來,看他臉上抹了兩道泥印,不免失笑,便向他招招手。
顧岳擠過人群,向張鬥魁等人問好之後,走到何思慎身邊。
何思慎笑道:“你這是要學骠騎将軍,‘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顧岳低頭默認。
何思慎笑着搖搖頭,卻也知道,至少今晚,是難以改變顧岳的決心的,便不再提此事,示意顧岳從桌子底下拖了一條板凳出來,在自己身邊坐下,又丢了一把大蒲扇給他。
李長庚等人向顧岳揮揮手,然後很快被人群淹沒了。
何思慎等人,正在聊今年的收成、糧食稅、田畝稅、團防捐、人頭稅等等,顧岳覺得自己不過是暫住,過不多久便要走的,也不太關心,随意掃了一眼戲臺上,正戲還沒開始,一個老頭正在拉二胡,時停時續,配合着另一個閉着眼睛清唱的中年人,中年人的胸前斜挂着一根足有兩尺多長的無節竹筒,每唱一兩句,便拍擊幾聲,聽那空空之聲,竹筒兩頭是蒙着皮膜之類。顧岳仔細聽了一會,唱的似乎是《明英烈》裏藍玉北征那一回。
莫師爺搖着折扇偏過身子笑眯眯地道:“顧兄弟,這漁鼓戲還是頭一回聽吧?”
顧岳點頭。
莫師爺道:“臺上那位也姓何,本名麽,莫某一時半會還真想不起來了,聽說年輕時在南岳做過道士,所以都叫他何道士,道沒學成,卻學了一肚子戲回來,操起漁鼓不上幾年,就成了咱們這方圓百裏地最紅的戲先生了。今兒個要唱大戲,不然還輕易請不動何道士。”
一說姓何,顧岳下意識地看了看何思慎,不過很快反應過來,他雖然一直讀的新學堂,多少還是知道,說書先生唱戲先生這樣人物,向來被認為操的是賤業,不登大雅之堂,甚至于是下九流,有些根底的人家或宗族,若出了這樣的子弟,都是要逐出家門、開出族譜的。
顧岳意識到自己一聽說那唱戲道士姓何,就去看何思慎,倒是很有些不妥了。
他難免有些窘迫地笑笑,想解釋一下,一時間又找不到解釋之詞。何思慎正半閉着眼聽得專心,手中蒲扇還應着音律一點一點,倒不在意,說道:“何道士的确是李家橋人,不過他那邊和我這一房離得遠,倒是跟算命的何六丙算是同一房傳下來、沒出五服的堂兄弟。”
莫師爺滿臉興味地打聽:“聽說六丙瞎子那一房,都有些神神叨叨的,讀書是都讀了,就是進學的幾乎沒有?”
何思慎有些感慨:“他們那一房,聰明人盡有,就是這聰明都沒用到正道上。”
何六丙算命的靈驗,在十裏八鄉是出了名的,更難得的是,哪怕只剩半只眼了,也善看天氣,只這一點,周圍農家就沒有不敬着他的;這何道士去唱漁鼓戲,說起來是操賤業了,但是讀過書的聰明人唱起戲來就是不同一般,尤其善唱三國、說岳、明英烈這樣的大戲,尋常人家還真請不動他。
顧岳留神聽了一會,果然這何道士唱的這一段藍玉北征,脈絡分明,詞句流利,雖是簡潔易懂的白話,偏偏又帶了幾分文人氣,讓不能讀書識字的村民聽了便心生敬畏,也讓臺前這些自認為頗有身份的聽衆覺得聽這等文雅戲臉上有光。
不過,顧岳忽而發覺,他幾乎聽不出來何道士是在哪幾處停頓換氣,只覺那歌詞唱腔,如山路高低起伏、連綿不斷。
一段唱完,何道士下去休息時,顧岳轉過頭來,低聲問道:“姑父,這何道士真是氣息悠長,練過好些年內功吧?”
何思慎點頭:“何道士那一枝,說起來都有些天份,拳腳上差些,這內功倒是都練得不錯。何道士練的是這一口氣息,何六丙練的是耳力。”
莫師爺趕緊湊過來問道:“聽說六丙瞎子那耳力,聽得到兩裏路外的說話聲,有這回事不?”
何思慎失笑:“又不是順風耳,哪有這麽誇張?不過是比平常人耳力強幾分罷了。”
顧岳忽然想到,夏收那會兒,李長庚常常一臉自豪地向他誇耀,李家橋的男丁因為常年習武,
手腳利索力氣大,幹起農活來如何如何強過周邊那些村子。
何道士和六柄瞎子這一房,常年習武,學以致用,果然也都是各自行當裏的出色人物……
這麽一想,怎麽總覺得有幾分詭異呢?
此時戲臺上一陣忙亂之後,擺了個香案,案上一個香爐,南岳大帝廟的廟祝穿了正經道袍,舉着三枝香,向着正殿方向拜了一拜,插入爐中,拖長了腔調高聲吟唱了一段半文半白的祝禱詞,不過其間夾雜了不少拗口的古詞,顧岳聽得半懂不懂,大致知道是祭先人祭神靈求祖宗神靈保佑風調雨順。
好不容易等着那廟祝唱完,不少年輕人都在臺下籲了口氣,顧岳也不自覺地吐了口氣,莫師爺與何思慎相視而笑。也難為這些少年人,要捺着性子聽這麽長一段多半聽不懂的祝禱詞了。
香案搬了下去,樂師在簾子後面就座,一陣鑼鼓敲過,換成了梆子,戲臺左邊,何道士換了身僧袍,頭上戴了頂僧帽遮住頭發假充光頭,拄着根竹杖權當禪杖,一搖三晃地走了出來,繞着戲臺,一路走一路唱,顧岳聽了幾句就明白過來,何道士演的是明山和尚,所以一路唱的是國破家亡的凄涼、不肯屈膝事敵的剛直、跋涉千裏的孤獨,還有初到大明山時淳樸鄉民的好客。
這出戲大概是演的年頭久了,八橋鎮幾乎人人都聽過好些遍,因此臺下不少人時不時跟着哼一兩句。
只是這臺下的嗡嗡之聲,也不能蓋過何道士的聲音去,依舊是字字清晰、如在耳邊。
莫師爺難免感慨了一句:“盛名之下,果然無虛士!”
顧岳覺得這出戲似乎和先前的漁鼓戲沒什麽大差別,不過就是換了身衣服、在臺上多走了幾步、加了樂師配合而已。不過剛剛這樣一想,戲臺左邊,忽地跑出兩名小兵,手執木刀,假作追殺明山和尚,三人在臺上追逃,時疾時徐,忽左忽右,盤旋繞走,臺下衆人,明知不過演戲,也看得極是緊張,惟恐那何道士假扮的明山和尚被兵士追上。
眼看越追越近,戲臺右邊,忽地一聲虎嘯。
旁邊立刻有人興奮地低聲叫道:“來了,來了!”
從簾子後面躍出的那只老虎,一撲丈餘,大有猛虎下山之勢,臺下哄然叫好,叫好聲中,兩名兵士慌忙閃開,明山和尚趁機躲到了老虎身後,只見那老虎伏地蹲了一蹲,擰轉腰身,縱身又是一撲,将一名躲閃不及的兵士撲倒在地,掄起前爪往他臉上一按,那兵士立刻配合作癱死狀。臺下哄笑起來。
另一名兵士曳刀而逃,自然也被老虎撲殺。
然後那頭猛虎懶洋洋地掉過頭來,向着明山和尚吼了幾聲,明山和尚合掌為敬,靜待猛虎走近,與它一道下臺離去。簾後鑼鼓聲又一次響起,樂師齊聲唱了幾句,臺下衆人也跟着亂哄哄地唱,因着太過喧鬧,顧岳只大略聽到“伏虎”、“護法”、“明山和尚”幾個字眼。
這一出《明山和尚遇虎記》極短,卻是正戲之前的加官戲,接下來才是中元節的正戲《目連救母》。目連需得連闖十八層地獄,才能将其母的受罰鬼魂救出來。這出戲各地的中元節都會演,顧岳在昆明時自然也看過好幾回,不過似乎今晚這一出目連戲很是不同,說是目連戲,不如說是武戲更合适些,十八層地獄的鬼卒鬼将,正好對應十八般兵器,演目連的武生,每闖一層地獄,便換一樣兵器,竟好似十八般兵器樣樣皆通。
每換一樣兵器,戲臺下便是一片叫好聲。此時目連手中執的是□□,槍一入手,便抖出數朵槍花來,顧岳忍不住也跟着叫了一聲“好”。
對面的四個鬼卒這一回扮成了長臂短腿黑面鬼的模樣,因為腿短跑不快,只争相将早就擺在戲臺角落裏的那兩大摞去了套索的籮筐當成石塊扔向目連,扔過來的籮筐,或是底朝天,或是面朝天,又或是側翻滾落,不論姿勢如何,目連只将手腕略略一抖,槍尖斜挑,在籮筐底面、側面又或是內面輕輕一墊一頂,籮筐便被□□挑飛,穩穩落到自己這邊戲臺的角落裏,那邊扔這邊挑,籮筐一個接一個地摞起來,臺下立刻又是一片哄然叫好。
一共十八個籮筐,那扮目連的武生,無一失手。一節戲罷,目邊下臺去了,四名鬼卒卻沒有即刻退下,将那兩摞籮筐一個個地舉起來,轉着圈向着戲臺下晃了幾晃,讓大家看清,每一個籮筐都完整無缺,連槍頭印子都沒有留下一個,顯見得目連手頭穩得很,槍上力道恰恰好。待到臺下又一連聲地喝彩,四名鬼卒才得意洋洋地搬了籮筐下臺去。
旁邊有人與有榮焉地說道:“那裏頭還有從我家借去的兩個籮筐。到底還是葛老板手頭拿得準!聽說去年中元節隔壁峰縣唱這出武目連時,足足挑破了三個籮筐!”
其他人紛紛附和,将那葛老板好生誇了一通。
顧岳聽他們說話,心念忽然一動,轉向何思慎道:“姑父,這一節戲,是不是從《小商河》演化出來的?”
楊再興在小商河馬陷泥潭,槍挑十八輛金人的滑車之後不幸戰死。《說岳》裏這一出戲,可是
讓顧岳和他的同窗們唏噓良久。
何思慎笑道:“眼光不錯。”
莫師爺在一旁嘆道:“何止這一節戲,前頭那幾節,都是從武戲裏化出來的吧?”
顧岳略一回想,果然如此,譬如目連闖第三層地獄時,和那守獄鬼将單打獨鬥,三鞭換兩锏,便是《說唐》裏頭秦叔寶戰尉遲恭那一出。其他幾節,也莫不如此。
難怪得與他在昆明看過的目連戲大不相同。
此時臺上略作收拾,接着先前那一節,重又開演。這一回換的兵器,卻是一枝方天畫戟,與目連對戰的是三名鬼将。顧岳脫口而出:“三英戰呂布!”
可不正是三英戰呂布?
八橋鎮周邊村子的人,看這出武目連戲已有多年,熟悉得很,倒不像顧岳和莫師爺這樣有心去仔細分辨其中究竟用了哪十八出武戲,但每一精彩處,仍是叫好鼓掌不絕。
這一出武目連戲看完,興奮過後,戲臺下幾乎所有人都有些疲憊,不過猶自交頭接耳意猶未盡地評說着方才那十八層地獄的武戲如何如何。
戲臺上忙亂着搬道具,臺下也開始忙亂,人群湧動,李長庚費力地擠過來向顧岳招手示意,人聲嘈雜,顧岳一時沒聽清李長庚說的話,何思慎用蒲扇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底下連着幾出都是文戲,年輕人沒這個耐心看,都往鎮子上玩去了,不用跟着我們,去吧去吧!哦,家裏有新亡人就一定記得放白河燈!”
顧岳“哦”了一聲,心想自己應該給父親放一盞白河燈,至于亡故了數年的母親,呆會問問李長庚就知道應該放什麽燈了。
顧岳跟着李長庚出來時,已然發覺,不斷有年輕人像他們一樣擠出人群,三三五五往鎮子裏頭走。
站在廟門外,居高臨下,可以望見八橋鎮街上的點點燈光,還有清江河裏陸續放出的河燈,便如兩條火蛇般蜿蜒伸展開去,映得十五夜的圓月似乎都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