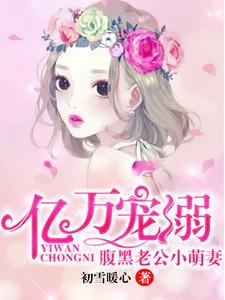第16章
回到船上已是下午,湖面上起了風。三人上船,來到僻靜之處,韓宣手扶欄杆,眺望天邊湖水。大象迫不及待剛要詢問,卻被張靜姝攔住。過了片刻,只聽韓宣吟道:
“季子平安否?
便歸來,平生萬事,哪堪回首?
行路悠悠誰慰藉?
母老家貧子幼。
記不起,從前杯酒。
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
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
只絕塞,苦寒難受。
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腳終相救。
置此劄,君懷袖。”
他吟完轉過身來,微微一笑:“這首《金縷曲》的詞,不知道你們聽過沒有?”
大象一腦子漿糊:“你這說的都什麽亂七八糟的,能不能好好說話?又骨頭又肉的,做菜呢?”
韓宣沒理他,又瞧瞧張靜姝,張靜姝也搖搖頭:“沒聽過。。。。。。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幾家能夠。。。。。。這詞寫的好凄涼啊,是誰寫的?”
“清朝有個人叫納蘭性德,你們知道吧?”
“嗯,知道,”張靜姝點頭道:“就是寫“人生若只如初見”那個人吧。聽說是個有名的才子,這是他的詞麽?”
韓宣搖頭:“納蘭性德文采風流,才華橫溢,寫詞上的造詣更是千古獨步,被稱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那是很了不起的。不過這首詞卻不是他寫的,寫這詞的人叫做顧貞觀。”
“顧貞觀?”張靜姝皺眉:“那是誰啊?
“他是——”韓宣剛要解說,大象聽得不耐煩:
“你能不能把話說清楚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他們到底是幹什麽的,扯這些沒用的幹啥啊?”
“象哥,”韓宣把手一攤,無奈道:“這些事都是有聯系的,我總得從頭說起啊,要不然你們也不會明白的。”
“那你趕緊的,別說廢話!”大象瞪了他一眼。韓宣嘆了口氣:
“那——好吧,這事還要從你們滿人身上說起。”
“啥?和我有啥關系?”
韓宣道:“當年李自成進北京,崇祯帝殉國,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滿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一匡天下。雖然軍事上順風順水,但其他方面的根基并不十分牢固,總是害怕有朝一日被趕回關外。為了防止漢族知識分子煽風點火,鼓動漢人造反,便大興文字獄,羅織各種罪名,想要以此鉗制漢人的思想,進而鞏固自己的統治——”
他略微思索了下,接着道:
“在順治朝的時候,江南有個有名的才子叫做吳兆骞————”
“吳兆骞?”張靜姝皺眉。
“嗯,”韓宣點點頭,“這吳兆骞是蘇州人,據說自幼聰穎異常,才氣非凡,不到十歲便能吟詩作賦,素有神童之稱。長大後更是被稱為“江左三鳳凰”,文采冠絕一時,出名的很,家境也不錯。反正總而言之吧,按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人生贏家,前途無量。家裏人也都對他翹首以待,盼他能有一番作為,哪知世事無常,這人後來卻出了事。”
“出了事?難道他也惹上了文字獄?”張靜姝問道。
“沒錯,”韓宣道:“吳兆骞二十六歲那年參加鄉試,中了舉人。這本是件令人高興的事,飛黃騰達,光宗耀祖,便從此始。誰知後來卻被仇家誣陷,說他是作弊,朝廷下了旨讓他進京複試。據說複試的時候,身邊武士持刀環立,眈眈相向,可能這吳兆骞心理素質不怎麽樣,膽戰心驚之下,竟然沒有把卷子寫完,這下可就把罪名坐實了,朝廷震怒,将他抄了家,人也發配到了寧古塔。”
“寧古塔?”
“就是現在黑龍省寧安市附近,入關前清軍在那駐過軍。”韓宣解釋道。張靜姝點點頭,韓宣接着道:
“你們想,這吳兆骞本是南方人,自幼生長江南水鄉。如今稀裏糊塗蒙受不白之冤,竟然被發配到這千裏之外的苦寒之地,那時候又沒有暖氣,東北這邊冬天如何,咱們都知道,他一個南方人到了這裏,遭受的苦楚那就不用提了。況且他本是受人陷害,大家心知肚明,自然紛紛替他鳴不平,這其中就有一個叫做顧貞觀的人——“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寫詞的人麽?”張靜姝問道。
“沒錯,”韓宣道:“這人自幼與吳兆骞交好,關系莫逆。當初吳兆骞被發配的時候,顧貞觀就曾立下誓言,說此生定要救他回來。可是雖說當時為吳兆骞呼冤的人不少,但在朝廷高壓之下,大家自身都是難保,又有誰能為他強出頭呢?這顧貞觀來來往往,四處奔走二十餘年,仍是無法救朋友回來。這一年他寓居京師,正趕上下雪,觸景生情,想起遠在關外的好友,心中十分難受,便寫下這首詞寄給吳兆骞。我剛才念的是上一首,還有下首。吳兆骞在家裏衆兄弟之中排行最小,因此也叫吳季子,所以開頭才會有“季子平安否,”的問話,那是以詞帶信的意思了。”
“原來如此,”張靜姝道:“那後來吳兆骞被救回來了麽?”
“後來這首詞被納蘭性德看見,他很感動顧貞觀對朋友的這份情誼,便代為幫忙。納蘭性德的父親是康熙朝著名的權臣納蘭明珠,勢力不小,幫着上下疏通,最後終于将吳兆骞救了回來。不過可惜的是,這人或許在東北待的時間太長了,二十多歲便到這裏,在松花江邊住了二十三年,早就習慣了這邊的氣候,回家以後竟然水土不服,沒幾年就病死了,這可真算是造化弄人了。”
韓宣搖頭嘆息。張靜姝笑道:
“我倒覺得咱們這邊挺好的,不像南方夏天那麽熱。”
大象在旁一直插不上嘴,見他說完,終于不耐煩道:“你講這一溜十三招,都是沒用的屁話。你倒說說,這些人跟那石頭上的詩有什麽關系?”
“當然有關系。”韓宣瞅了瞅他:“因為這詩也是寫給吳兆骞的。”
“也是寫給他的?”張靜姝奇道。
“正是,”韓宣道:“這詩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大詩人吳偉業,又號吳梅村,就是寫《圓圓曲》那個,你們看過《鹿鼎記》吧?”
“看過,”張靜姝道,“沖冠一怒為紅顏,我記得這句。”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恸哭六軍俱缟素,沖冠一怒為紅顏。這位吳偉業先生當年與吳兆骞也是相識,吳兆骞發配的時候,他曾去送別,專門為其做了一首長詩,感嘆他的命途多舛,詩名就叫做《悲歌贈吳季子》。裏面開頭幾句便是“人生千裏與萬裏,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那石頭上少寫了一句,可能是刻字的人忘了。這裏面前兩句是取自江淹《別賦》裏“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的意思。這詩我小時候讀過,印象很深,不過後面的句子都忘了,反正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牢騷話,什麽“生男聰明慎莫喜”之類的,那也無關緊要。咱們只需知道前幾句就夠了。”
“夠什麽?”大象愣道:“你還是沒說明白,這幾句詩能看出什麽啊?”
“你們想啊,”韓宣神秘的一笑,拿起照片晃了晃:“他們既然在石頭上面刻下這幾句詩,當然不會是文盲,肯定是讀過書的人。而且,之所以刻這幾句詩,那定是因為自己的處境身世和這詩有共鳴,否則的話,幹脆刻“到此一游”,或是別的什麽名言警句罷了,又何必刻這麽幾句?根本說不通嘛。那麽好,問題來了,到底什麽人會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像吳兆骞一樣不情願的被大老遠發配到東北來?并且剛才聽那個李師傅說,那女孩口音像是南方人,你們再想想這照片上的時間————”
“照片上的時間?南方人?”張靜姝微一思索,忽然眼睛一亮,恍然道:“啊!你是說他們是————”
“沒錯!”韓宣目光炯炯:
“他們是知青!至少刻字的那個人肯定是知青!”
“知青?”大象皺眉看看韓宣,“你能肯定?”
“當然能!”韓宣斬釘截鐵的道:“不管怎麽說,我敢肯定那照片上的女孩肯定是南方來的知青,那年頭出差辦事都要單位開的介紹信,要不是知青,誰能從南到北跑這麽遠還能生活?”
“怪不得咱們在鎮上都問不到他們呢。”張靜姝道。
“是啊,”韓宣嘆了口氣:“既然是知青就應該住在下面的農村,或者農場什麽的。他們就算來過鎮上,次數一定也不會很多,所以鎮上這些人說沒見過他們,那是再正常不過了。咱們早就應該去下面的農村問問,不過這麽多年過去了,這裏的農村早非當年模樣,能不能打聽出來,那也實在難說的很——”
“沒關系,”張靜姝寬慰道:“吳所長不是說了,只要知道這些人的身份,他那邊就好辦多了,咱們回去告訴他這些人的身份,我看他多半能查得出來。”
“嗯,現在也只能如此了,咱們這就回派出所找他。”
韓宣說着,将照片放進懷裏。剛一擡頭,只覺得眼前一花,好像有什麽人的衣角在船尾拐角處一閃而逝。他心中一驚,來不及思索,三步兩步竄了過去。大象和張靜姝吓了一跳,連忙也跟了過去。只見韓宣站在船尾,四處張望,甲板上卻是一個人影也沒有。大象問:
“你幹什麽?”
“你們剛才往這邊看了麽?看見什麽東西沒有?”韓宣問道。兩人都搖了搖頭,張靜姝道:
“沒有啊,怎麽?你看見什麽了?”
“好像有個人!一直在這盯着咱們,我一轉頭的功夫就沒了。”韓宣皺眉道。
“會不會是你看錯了?”張靜姝問。
“嗯——”韓宣沉吟片刻:“走,咱們去船艙裏看看。”。
船艙不算寬敞,裏面稀稀拉拉坐着十來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普通游客,也看不出什麽可疑的人。韓宣環顧四周,見最後一排椅子上坐着一位白須飄飄的老大爺,他這位置視野極好,船艙裏的情況一目了然。韓宣快步來到他身邊,問道:
“大爺,您剛才看見有什麽人進來了麽?”
“啥!——你說啥——?”老大爺放下拐杖擡頭看着他,一臉驚愕。韓宣加大了聲音:
“大爺!我問您剛才看見有人進來過麽?”
“啥!——你說啥——?”
“剛才有沒有人進來過!!!”韓宣扯嗓子大聲喊道,由于聲音太大,整個船艙的人一起回頭,莫名其妙的看向三人。三人一陣尴尬,張靜姝臉一紅,拉了拉韓宣衣服。那老大爺仍是大聲問道:
“啥!你說————”
“行了!您老歇着吧。”韓宣氣急,轉身拂袖而去。身後卻傳來老大爺爽朗的聲音。
“沒人進來過。”
韓宣心裏一陣苦笑,和二人回到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