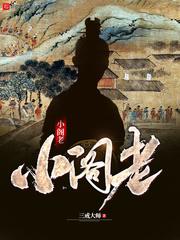第19章 (4)
着遠方駛往東北方向的三艘海船,船頭飄揚的仍是日出滄海的大旗。雲夢一直沒有改換旗號。
兩支船隊背道而馳,漸漸已望不見蹤影,只餘下萬頃碧波在強烈的陽光下洶湧起伏。
外傳 小夜
〖一日,帝問曰:“襄陽圍已三年,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誣以他事,賜死。
——《續資治通鑒》〗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史書中沒有記載宮女的名字,有誰知她心中所藏的秘密?
【一、】
海棠,其花甚豐,其葉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綽約如處子。
小夜家的庭院裏便有一株海棠,今年春天它又開花了,嬌豔的花兒在春陽中盈盈欲語。每次看見它時,小夜心中都有一陣陣的感動。仿佛總在向柔風傾訴着什麽的海棠,令她神往又黯然心傷。無名的憂郁與惆悵不知從何處而來,常常在最不提防的時刻攥住她的心。
家中永遠是那樣黯淡,擁擠,嘈雜不安。唯有這海棠,是恬靜又明麗的,無言地撫慰着孤獨的小夜。
左鄰右舍是同樣灰暗的人家,同樣灰暗的生活。唯有李家子弟策馬而過的身影,如海棠明媚小夜的庭院一樣,令小巷煥然生輝。
上一任池州知府,卸任回京之後,曾不無訝異地對京中同僚說道:“池州李家,一門三尚書,四代六将軍,文采武功之盛,已是世之罕有;更奇的是,他家子弟,仿佛生有異禀,龍吟方澤,鳳躍雲津,無一不是人中俊傑!”
新任池州知府,也不止一次在信中對朋友感嘆:“池州山水之靈氣,盡鐘于李家子弟了!”
但對于小巷的居民,他們是這樣特立獨行以至于高不可攀。他們的喜怒哀樂,舉止言談,像一個個深不可測的謎,讓小夜盡在心中作無數次的猜測,不知道他們為什麽這樣高興或者憤怒。她熟知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和排行,熟知他們的相貌和聲音,甚至熟知他們的嗜好,卻始終沒能弄明白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對于她,他們是陌生的種族,高高在上的神祗,讓她如癡如狂地迷醉,卻無法理解。她只用固執的、專注的目光,追随着顯然是他們之中的核心的六郎李應玄。
其時李家年長的三位子弟都已出仕,在留在池州老家的八位兄弟中,李應玄并不是最年長的一個,但他卻在無形之中左右着所有兄弟的動向。小夜初次意識到這一點,是在她十三歲那年的浴佛節上。
那時她還只是一個小姑娘,因為長年伏在繡架上,枯瘦得如不見陽光的小草,就像小巷中無數孩子一樣。四月初八浴佛節,全城的人都去城東靈應寺禮佛,這也是小巷中的孩子們少數幾個可以放下繡活輕松游玩的一天。
這一年的浴佛節,一直為池州人所津津樂道。并不是因為熱鬧,每年的浴佛節都有它的熱鬧。池州人記得這一個,完全是因為李應玄。
那年春天池州新調來一支駐軍,卻是從淮北大宋國土之外招納來的歸義軍,原屬楊妙真的舊部。楊妙真排行第三,人稱“三娘子”,割據山東臨濟一帶多年,一杆梨花槍號稱是天下無敵手,部下兵強馬壯,無論是金人還是蒙古人都無奈她何。楊妙真病逝之後,部下群龍無首,立腳不住,有的被蒙古人招納了去,有的解甲歸田,但也有不少人渡河南下,投奔大宋,樞密院将這些人馬編為三支歸義軍,其中一支派駐到池州,領軍将領名為蕭五常,據說是楊妙真舊部中的第一骁将,殺敵無數,威名極盛。
蕭五常的部下向來以悍勇聞名,要論上陣殺敵,自是所向披靡;但是軍紀不佳,也是遠近有名。自從這支部隊到池州之後,池州人沒少吃苦頭,只是礙于其身份特殊,朝廷待之有如客人,池州知府也不便管得太多,對池州人的抱怨只能軟硬兼施地壓服下去。無人管束,蕭五常的歸義軍更是得意忘形,竟然在浴佛節上縱馬尋樂,有幾個最是無法無天的,更專尋了人多之處策馬馳去,看馬蹄所到之處哭鬧成一片,他們在馬上哈哈大笑。也有士兵棄馬步行,專尋年輕女子多處去挨挨擠擠,乃至于動手動腳地出言調戲。
李家的衆多女眷都信佛,浴佛節自是要去禮佛。因為随從多,行動未免緩慢一些,到靈應寺外時,已是近午時分,正是最熱鬧的時候,也是禮佛的池州人被那些恣意尋樂的士兵攪擾得沸反盈天的時候。小夜和同伴被人群擠來擠去,已經快喘不過氣來。
見到李家子弟策馬護着十幾乘轎子姍姍而來,衆人都松了一口氣,紛紛讓開道,幾位與李家說得上話的老人,帶了自家子弟迎了上去。
直到這時,小夜才能夠從人群中脫身出來,躲到一家香燭鋪的門前的楊柳樹後,擡起頭熱切地望着高踞馬上的李家子弟們,像所有的池州人一樣,對他們的到來抱着無限的希望,認為只要有李家子弟出面,一定可以制止住那些士兵的胡作非為。
最年長的四郎聽了老人們的訴說與請求,沉吟了一會,翻身下馬,到老太太轎前低聲請示。小夜離得太遠,聽不見他們的說話,但是看四郎的神色,滿懷希望的心已經沉了下去。
因為失望,人群又開始騷動起來。
六郎李應玄望着人群,臉色慢慢地漲紅,突然間抽出鞍邊箭筒裏的一枝箭,揚手擲了出去。人群中傳來一聲慘叫,一個剛剛踢倒了路旁茶水鋪的士兵大腿上中了一箭,他的同伴急忙扶住他,厲聲喝問:“誰幹的?給老子站出來!”
人群哄然大笑起來。
四郎回過頭責怪地看着李應玄。
李應玄的視線仍然停在那群士兵身上,鎮定自如地說道:“知府大人不方便管這些事,就讓我們來管。”
四郎皺皺眉,想說什麽又忍住了。
事情已經發生,再責怪李應玄已無用處;而且他看得到眼前的形勢,若是責罰李應玄,只怕會激出人群不可測的反應來。
那群士兵很快發現了他們的目标。
即便是這些無法無天的士兵,也不敢貿然去挑戰李家子弟。幾個人低頭耳語了一陣,便有人鑽入人群去請援兵去了,一個顯然是為頭的士兵則高聲叫道:“有膽射我們兄弟一箭的人,夠膽就不要走,等着我們将軍來找你算帳!”
李應玄沒有回答,只是又抽出了一枝箭。
那士兵吓了一跳,知道李應玄抽出箭來絕不只是裝裝聲勢而已,但就此閉口,又心有不甘,似是太顯軟弱了。
正在左右為難之際,人群外已傳來急如驟雨的馬蹄聲。
請援兵的士兵頗為機靈,知道今次是李家子弟出頭管他們的事,尋常偏将副将應付不來,因此添油加醋地報到了蕭五常跟前。蕭五常一聽大怒,當下便策馬提槍趕了過來。
一行人怒馬如龍,還在遠處,聲勢已經逼人。
那幾個被圍在人群之中的士兵急忙迎了上去。
蕭五常年紀不過三十出頭,身高臂長,骠悍之氣見于形色,凜厲的目光所到之處,人群都不由得安靜下來,不敢與他的視線相接。只是蕭五常氣勢雖然淩人,神情之間卻帶着郁悶不平的陰沉,李應玄注意看了他一眼,才将那枝箭插回箭筒,策馬越過李家的轎子,迎上去面對着蕭五常。
人群緊張地注視着他們。
蕭五常滿臉不屑地打量着年輕的李應玄,過了一會才說道:“蕭某人帶着這些兄弟們不顧生死地斬殺蒙古人的時候,李家的公子們還都是些娃娃吧,如今竟然夠膽量夠本事來管蕭某人這些兄弟們的閑事了!”
李應玄迎着他的目光答道:“這不是閑事。”
蕭五常哈哈笑道:“就算不是閑事,只不知李家的公子們又是憑什麽來管!”
即便是樞密院,對這三支歸義軍的種種不法之事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要不是太出格,便由得他們去。好歹這三支軍隊是歷盡千辛萬苦才得以越過蒙古人的重重防線投奔了大宋,看在這一片忠心的份上,其他都可以包涵一點了。
李應玄回過頭說道:“應龍,回家取我的槍來。”
十一郎李應龍是李應玄唯一的親兄弟,卻是最好事的一個,李應玄未曾出手之前,他已經摩拳擦掌地躍躍欲試;聽得李應玄這麽一吩咐,心中大喜,應了一聲“知道了”,帶轉馬頭飛馳而去。
蕭五常略帶詫異地看看他,一揮手,部下四散開來,圈出一大塊空地。
圍觀的池州人都聽說過梨花槍天下無敵手的傳聞,雖然深信李應玄絕不會敗,到底還是心中不安,李家年長的四郎與五郎更是皺緊了眉頭。四郎俯身向轎中的李老夫人低聲說道:“祖母,您看是不是——”
李老夫人默然許久,在轎中低低地嘆息了一聲,說道:“就讓應玄去吧。這件事情,總得要有人出面來管一管。整個池州都在看着我們李家,李家不能負了這個期望。況且,就讓應玄去殺一殺那些人的威風,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四郎低聲說道:“但刀槍無情,六弟若有個失手——”
李老夫人決心已定,當下斷然答道:“應玄既然這樣做,就必有他的道理。你去告訴他,就說我說的,叫他盡管放手上陣,就算出了什麽事,有我呢!”
四郎只好領命而去。五郎對自己搖搖頭,向身邊的七郎無奈地嘆道:“六弟讓祖母給寵壞了,什麽事都由得他去。希望六弟不要真地失手傷了那位蕭将軍才好。”
無論怎麽樣不願意打這一仗,四郎和五郎都毫不擔心李應玄會敗。一旁聽到這話的池州人都松了一口氣,人群中開始小聲傳着這句話,興奮地等待着李應玄挫敗那不可一世的蕭五常。
不過小半個時辰,李應龍已取了長槍來。
李應玄接過槍,看着對面的蕭五常說道:“我就憑這杆槍來管這件事,蕭将軍意下如何?”
蕭五常大笑道:“一言為定!”
兩人各自帶馬後退到空地邊緣,對峙片刻,叱咤一聲,挺槍策馬沖向了對方。
蕭五常慣穿黑袍,胯下又是一匹通體烏黑、四蹄踏雪的戰馬,疾馳之際,便如一股黑旋風一般;李應玄穿的卻是銀白團花箭袖,胯下戰馬則雪白得無一絲雜色,策馬飛奔之時,整個人就如貼在馬背上的一陣清風似地輕靈,但長槍一出,又帶上了一往無前的逼人氣勢,合着池州人在身後助威的吶喊聲,令得蕭五常悚然動容。
蕭五常的部将原本都在為主帥吶喊助威,滿心以為李應玄絕不是自家主帥的對手;及至見到李應玄飛馬沖出的身形氣勢,都不由得有些震驚,一名偏将忍不住小聲嘀咕道:“看不出這小子還真不含糊!”
兩杆槍在錯身之際橫裏一交,蕭五常力大槍沉,将李應玄的槍壓到了下方;但是李應玄順勢将槍往下方壓得更低,令得蕭五常因用力過猛而略失重心,李應玄随即擰腰反手将長槍往回一收,槍上生出一股粘力,竟将蕭五常的槍也拖動了幾分。
蕭五常霍然收槍,震驚地道:“且慢!這是不是岳家槍法的拖槍式?你從何處學來?”
李應玄也暫且收了槍,帶住馬,肅然答道:“久聞蕭将軍識得天下槍法,果然名不虛傳。這确是岳家槍法。當年靖康之變後,國家多難,池州李家的先祖延清公以一介書生,投筆從戎,就在岳武穆帳下做了一名參将,習得這槍法;風波亭之獄後,延清公避難離職,定居池州,開了池州李家這一枝,也将這槍法傳了下來。”
四下裏一片寂靜。即使是池州的老人,也不知道李家槍法的源流;此刻衆人心中不由自主地生出深深的敬畏,以至于不敢再貿然出聲喝彩。
蕭五常只錯愕了一瞬便大笑道:“好,今日我就以楊老令公傳下的梨花槍來領教這岳家槍法,豈不是一大快事!”
話音未落,蕭五常的槍已到了李應玄的馬頭前。
李應玄連擋一十三槍,第十四槍來時,他在馬背上向後一仰,槍尖自他胸前擦過,走了個空,蕭五常疾收槍,李應玄卻已抓住這個機會,槍尾一挑,打中了蕭五常的槍身,令得蕭五常身不由己地連人帶馬向一側偏了過去,李應玄趁機搶攻,連出三槍,将蕭五常逼退數步。
初夏正午的陽光已有灼人之勢,但圍觀的人群一動也不動,沒有人想要退到陰涼之處去。
蕭五常與李應玄幾次攻守易位,卻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占到上風。蕭五常勝在槍法淩厲、變化多端;李應玄卻每每能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之下反守為攻。
蕭五常久戰不下,心中不由得焦躁起,來眼看李應玄又要搶得先機,暗自一橫心,兵行險着,詐作舉槍格擋李應玄斜斜刺來的一槍,卻忽地一側身,槍交左手,緊貼着脅下刺了出去,拼着挨李應玄一槍,也要将他挑下馬去。卻不料李應玄那一槍原是虛招,剛剛作勢遞出去,手腕一抖,槍尖挑了起來,由斜刺變成了自下而上刺向蕭五常的小腹。
蕭五常的槍尖到了李應玄的胸口時,李應玄的槍也已到了蕭五常的小腹前。圍觀的人群失聲驚呼起來。
但是兩人不約而同地停住了手,對視一眼,又同時慢慢将槍收了回來。
蕭五常沒有再出槍,反而哈哈笑道:“痛快痛快!再打下去就沒有意思了!”
李應玄微微一笑,說道:“蕭将軍,若是在半年之前,應玄恐怕還非将軍對手;但是這半年以來,将軍寶刀閑置,雄心銷磨,槍法多少都有些生疏了吧。應玄能夠與将軍相持到現在,委實有些僥幸。”
蕭五常不無詫異地望着李應玄,好一會才道:“六郎過獎了,蕭某向不服人,今日卻不能不服六郎。我在六郎這個年紀,絕沒有這樣的成就;假以時日,六郎定可遠勝過蕭某人。”
李應玄笑而不答,轉過話題說道:“今日一見,應玄才知道蕭将軍并非那種耽于安樂的人,避居江南,原非将軍本意,樞密院的确不應讓将軍閑置在池州的。将軍部下多有擾民之舉,恐怕也因為閑置無事的緣故吧。邊關多事,正是用人之際。應玄雖無官職,也當請各位叔伯盡力向樞密院進言,力争能夠早日讓蕭将軍重返戰場。馳騁邊關的蕭将軍,只怕再不是應玄能夠抵擋的了。”
蕭五常一時間說不出話來,擡頭遠望北方,臉上微微抽動着,盡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失态。
蕭五常的部将離得更近一些,也聽到了他們的對答,都沉默下來。
自那天以後,蕭五常的部下無事不出營門一步;即便出來,也不再像從前那般惹事生非。五個月後,蕭五常所部被調往襄陽。
【二、】
在浴佛節上,李應玄成了整個池州的驕傲。小巷中的孩子,僅僅因為經常能夠見到李應玄和他的兄弟們經過,也有了一種能夠對其他同伴誇耀的自豪。
小夜也是這群孩子中的一個;雖然她是這樣沉默,從不會像其他孩子那樣興奮地訴說,在她的心中,依然充滿了這種自豪。
尤其令她暗自裏驕傲與滿足的是,在小巷衆多的孩子中,李應玄唯一對她說過話。
可那是怎樣的一句話啊!
秋高草枯,李家兄弟幾乎每天都要出去騎馬打獵。李家兄弟的馬蹄聲一響起,小巷裏的孩子們便都扔下活計跑了出來。看這些天之驕子們躍馬揚鞭、談笑風生,是他們寶貴的歡娛。小夜癡癡倚門,望着李家兄弟們帶醉自夕陽中歸來,肩上栖着鷹,鞍邊挂着弓箭和獵物,秋陽亦如醉。最幼小的十一郎李應龍醉眼迷蒙地從馬上摔了下來,而且正好摔在小夜的門前,小夜猝不及防地往後一退,絆着了門檻倒栽下去。但是一條馬鞭靈蛇似地揮出卷住了她的腰,将她拉住,免了她摔在門內青石板上、頭破血流的厄運。
小夜不知道一根細細的馬鞭怎麽可能有那麽大的力量将自己拉住。李應玄已經收起馬鞭,微微一笑:“好險啦,小姑娘。”
十一郎的兄長們正在大笑,誰也沒有伸手去幫他,都帶着那種有趣好玩的笑容看着他,讓他自己爬起來,搖搖晃晃地爬上鞍去。李應玄也在笑,轉過頭來又看了小夜一眼,仿佛要确定她的确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到驚吓。小夜的臉漲得通紅,卻鼓足勇氣要好好地正視神一般的六郎。李應玄的笑容親切又溫和,春陽一般的目光仿佛包容了她的整個身心。小夜全身忽地一熱,那一剎那她忘記了自己周圍的一切,只有一種眩暈的幸福。
這一剎那的變化是如此明顯,仿佛是上蒼慈愛的手指輕撫過一株小草,讓它瞬息間幻化成一朵嬌豔欲滴的小花,以至于李應玄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當馬蹄聲遠去、暮色初起時,小夜才如夢初醒般地感到周身的涼意。
只有她還站在門邊,其他的孩子們都回去了。
——可是,她已經不再是個孩子。
後來,小夜慢慢地發現,李應玄對每一個人都是親切又溫和的,他像他信佛的母親一樣憐弱惜小,總是不自覺地從眼神舉止中流露出他的憐惜與撫慰。
知道了這一切,小夜仍固執地不願相信,那個夕陽西下的傍晚,李應玄的目光只是在施舍他的憐惜。她不能忘記那目光中隐含的不自覺的愛撫,以及掩飾不住的驚奇與錯愕。
自那以後,小夜退到了門檻的後面。她懷着那混亂、灼痛又甜美如夢的秘密,半掩在門後,渴求地望着那飛馳而過的身影。李應玄在經過時會不由自主地用目光搜尋她纖巧的身影,在迎上他的目光那一瞬間,小夜臉上煥發的光彩讓他感到一陣無名的快樂。他是照亮小夜生命的陽光。這可憐的孩子,她平時一定很不快樂吧?他想我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一點兒時間和心情來照看一個生命,就像母親照看撲火的飛蛾一樣,到天亮時,就要将那小小的飛蛾放生到外面的天地去。
日複一日,心情如此沉澱,在他不自覺間積聚。
在無數細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有着最溫馨的幸福和最深沉的悲哀。
小夜知道自己在作繭自縛。可是她怎能舍棄那一剎那令她死而無憾的幸福?他們現在每每會在心中相視一笑。李應玄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麽嗎?他滿足于那一剎那心中溫柔的快樂。這是他所未曾有過的一種快樂。而他又是這樣灑脫不拘小節,不吝于讓自己擁有這似乎不合乎常理的奇異心情。
看見小夜時,李應玄的眉揚了一揚,似乎想告訴她一些什麽事情,随即又不同尋常地向她微笑。小夜的臉漲紅了。她不知道自己的嘴邊也漾起了溫柔的微笑。這讓李應玄又怔了一怔。這一刻小夜不再像一個羞怯又勇敢的孩子,而是像——他下意識地擾亂了自己的思緒,不讓自己再想下去。他可以關照一個孤獨的、可憐的孩子,但不能關照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
當聽到李家年長的四郎、五郎和六郎赴京讀書的消息時,小夜明白了李應玄那異乎尋常的笑容和暗示。他是在向小夜告別。她暗暗地失望,同時又感到莫大的歡喜。李應玄會記得向她告別,是因為她已經在他的心上。小夜唯一的願望,也不過如此。只要李應玄總是能記得她,有時會想起她,小夜便已覺得滿足。
在等待的日子裏,小夜的針下慢慢地多了一些讓母親擔心的東西。母親默默地看着小夜長高,長大,出水的荷箭似地日日綻放出不同的美麗,眼裏清亮得如汪着水,繡出的花鳥暗藏着無限生機。她仍會為了馬蹄聲而放下針線跑出去,但已經不再那麽熱切。她将自己深深地藏在門後,悄悄地望着李家兄弟揚鞭而過。李府是一個大家族,十一個兄弟裏只有李應龍與李應玄是親兄弟,其他都是堂兄弟,因此只有李應龍最像李應玄。小夜喜歡看李應龍的背影,背影能讓她在恍惚中當成是李應玄;但這是不可替代的,她也知道這不過是自己一廂情願的幻覺,可是她只能從這幻覺中偷得一點兒快樂。
深藏門後的小夜,那亭亭的身影仍然引起了李家兄弟們的注意。他們大多還是些心志飛揚的少年,李應龍更是個大男孩子。有一天當小夜凝視着他的背影時,他忽然回過頭來對小夜咧嘴一笑,做了個大大的鬼臉。他的兄長們都哈哈大笑。小夜狠狠地一跺腳跑回自己房中,臉上紅一陣又白一陣,淚珠控制不住地滾下來。他們是這樣不屑地取笑她!
從那以後,她不再跟着弟妹們倚門而待,等着李家兄弟經過。母親暗暗地松了一口氣。她不希望女兒有非份的妄想,只希望她能像自己一樣過着雖然辛苦了些但是穩妥平安的日子。小夜異常的沉默一向讓她擔心,特別是小夜長大以後。
一連幾天,李應龍都沒有再見到那隐藏在暗中的身影,心中不由得十分歉疚。他只是為了好玩,可是沒想到會讓那個小姑娘氣得不願意再出來。他試着回想小夜的面容,可是想不起來,只覺得似乎不像這一條陰暗的巷子裏的女兒。她臉上有時會有一層明亮的光彩,使得她整個人就如一顆閃光的珍珠;這是他過去偶然間瞥到的。他開始挂念那個奇特的小姑娘。她身上有一些東西,他說不出是什麽,但是讓他好奇。這個不再出現的小姑娘,究竟是什麽模樣?
李應龍每次經過小夜家的庭院,總不由自主地要向院裏看一眼。但小夜一直不再出現。他只看到那株海棠開了又謝,謝了又開。
小夜日日坐在繡架前。無言的等待是讓她痛苦又歡樂的秘密。所有青春的熱情都繡進了那一幅幅絲帛中。她不知道自己的刺繡已成了池州府的一件奇跡。老一輩的繡匠說,葉家的那個大女兒是讓她家院裏的海棠附了身,才繡得出花鳥的魂兒來。那是他們不了解也拒絕了解的謎。他們是用手、用娴熟的技藝在刺繡,小夜用的卻是她在孤獨、沉默中凝聚起來的所有熱情與心血。弟弟從外面帶回來的一張張畫兒,成了她的摹本。她不只繡花鳥,也繡人物,繡亭臺樓閣。唯一遺憾的是,她不能繡出自己模糊的夢境。
她的技藝越來越精熟。卸任回京的池州知府将她的繡品作為禮物贈送給京中的同僚,其中有一個是池州人,李應玄的父執輩。那日他們兄弟三人剛從太學出來,拜谒這位長輩,商議今年的進士考試之事。座中客人恭維池州山靈水秀,連民間繡女都這樣心靈手巧,無怪乎李家兄弟個個都是人中龍鳳了。李應玄笑而不語。池州府的繡戶都集中在李府後面的那一條小巷中,這幅嬌豔如出浴楊妃的晨露牡丹,應當是出自那條陰暗的小巷。是那家有海棠花的庭院、那個會在看見他時整個人都光亮起來的小姑娘嗎?也許只有她才能繡出這樣有生氣、有熱情的牡丹。他不覺暗自裏有些驕傲,很奇怪地為小夜的技藝而高興。
小夜仍是日複一日地坐在繡架前。
又一個殘冬過去,春暖花開,小夜已經十七歲了。母親笑着說她該為自己繡嫁妝了。小夜低着頭一聲不響地挑選着絲線,心裏有微微的慌亂。她太專注于繡架和自己的心事,以至于完全沒有想到每個女兒都得面臨的命運。
小夜不知道如何是好。她的世界因為母親的這一句話而不複完整。
母親說這話後沒幾天,夕陽西下時,人聲馬嘶又來了,但是不同尋常的歡樂。小夜的心猛然一跳,針刺了手,血滴染紅了素絹,急忙起身時帶翻了凳子。她奔到庭院中,猛地一拉門。
院門從外面鎖住了!她忘記了這是她自己的要求。父母和弟弟出去時,總是将她和初長成的妹妹反鎖在家裏,免得歹人窺伺。
李應玄只看到門縫裏那雙含淚的、絕望又熾熱的眼睛。為什麽要上鎖?踏入小巷,他才知道自己有多渴望見到小夜臉上為他而閃耀的光輝,見到那羞怯又勇敢的微笑,感受到那道緊緊追随着他的目光。那是一種不希冀回報、無怨無悔的溫情,令他感動而想念。重門深鎖,海棠花開今在否?他渴望見到小夜無恙,仍是當年的模樣,仍然可以讓他自然而然地關懷和憐惜。
可他只能策馬而過。
小夜無力地倚在門上,任淚流滿面,無視妹妹驚恐、怪異的目光。夜色慢慢地籠下來,一陣風過,海棠花瓣落了一地。
【三、】
李應玄這次回來,是因為太師賈似道黜落了他的考卷。他的兩位兄長平和沖淡不慣于顯露鋒芒,而他在試卷中公然指責權臣誤國。諸多的內憂外患,可是“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半閑堂裏鬥蟋蟀的宰相賈似道,是太學生們幾次群起而攻之的對象。身處京都,種種消息都傳入耳中,令他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結果三兄弟中只有他落榜。
與李應玄一同被黜落的有好幾個。他們相約要投筆從戎。其時蕭五常在襄陽大帥呂文煥帳下甚得重用,因了蕭五常的推崇,呂帥對李應玄大有好感。因此他們決定去襄陽。約定各自回家準備,再到池州會合,一起動身。
血氣方剛的李家兄弟都鬧着要随李應玄一同去投軍,被李老夫人阻止了。唯一不能阻止的是李應玄。這個她最鐘愛的孫兒,向來就不是肯輕易放棄自己決定的人。何況她也想讓孫兒出去避一避。賈太師一向不會輕輕放過與他作對的人。而恐怕只有在襄陽,才能讓李應玄躲過賈太師的報複;畢竟呂文煥祖上世代為将,長江一帶的水師将領,大半都是呂家的舊部或是子弟,即便是賈太師,也不敢輕易去惹翻呂文煥。
太夫人吩咐家人為六郎置辦行裝,其中包括兩件披風。太夫人決定要繡上鷹,就像李應玄的祖父當年在淮揚軍中時穿過的戰袍一樣。
這兩件披風都交到小夜手中。只有她的繡藝能讓太夫人滿意。
李府的仆婦到小夜家中時,小夜的父親和弟弟都出去了,母親和妹妹在院中晾曬剛洗的被褥和衣服。小夜在窗前支好繡架。春陽斜斜地、柔柔地抹在繡架上。小夜聽見陌生的說話聲,擡起頭,看見院中那個仆婦。母親惶恐地在答應着什麽。小夜心中一緊。是為自己來的嗎?母親真的打算給她說個人家?
母親陪着那仆婦進來,很緊張地說道:“小夜,李府要繡兩件披風,一幅蓮花觀音。圖樣都帶來了。老夫人叫你用心繡,趕快一點,等着要呢。其他的活先放一放。”
老夫人想讓觀音陪着孫兒一起去襄陽,保佑他平安歸來。
那仆婦道:“老夫人說了,也就在這幾天要的。價錢不惜。小夜姑娘,這是訂金,絲線讓你自個兒配,要最好的。”
她一邊說一邊打開帶來的包裹。包裹裏除了繡觀音圖的素絹,兩件白綢披風,還有一件已經半舊的、絹色都有些發黃的戰袍,上面繡着飛鷹,英姿勃發如欲振翅飛去。仆婦道:“老夫人交待,照這上面繡。可千萬保管好,這是老太爺的遺物。兩天後我先來拿披風和戰袍。”
小夜低着頭一一答應。她不是第一次接李府的活計,可是這一次似乎有點不大一樣。李應玄才剛回來,就趕着要這些東西。
她低下頭看着手中的戰袍,心裏莫名的煩躁。
那天是住在東門外的舅父的生日,父親和弟弟先去置辦禮物了,本來她母女三人應當随後趕去的,李府仆婦一來,小夜只好獨自留下趕活。母親和妹妹臨走時鎖上門,囑咐她自己安頓中飯和晚飯,記着收拾晾曬的被褥和衣服。
回到繡架前,小夜心中有微微的恐慌。她還從沒有一個人呆在家裏的經歷,小小的院落,此刻大得異樣,空洞洞的。
她定定神,坐下來仔細挑選絲線,心中卻萦繞着清晨時輕輕踏過的馬蹄聲。李家兄弟們總是喜歡很早便出城。等到馬蹄聲消失,她才記起李應玄已經回來了,就在那群人之中。可是她卻沒能趕上再看他一眼。她平時都是很早便起身的,開門灑掃,剪下花枝插在窗臺上的白瓷瓶中。她原本可以趕得上李應玄的經過。可是昨夜大半夜的無眠讓她在清晨時睡着了,迷蒙中錯過了機會。而現在院門又已上鎖。明天她還有機會嗎?她多想好好地再看一眼久別的李應玄,感受到他溫和憐惜的目光與微笑。
小夜咬着線頭呆呆地出神。她近來很容易陷入這種恍惚的、怔忡不安的狀态中去。許久,她才驚醒過來,慢慢地将披風繃上繡架。
春陽和煦得叫人想就此睡去。小夜養的那只小黃貓懶洋洋地在陽光底下仰